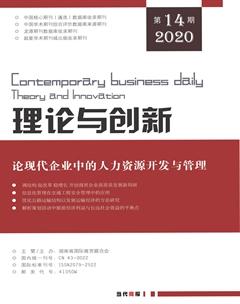古代衙門胥吏的利與弊
內鄉縣衙有一座塑像,兩個胥吏站在院中一人捋須微笑,一人撫刀而立,威風凜凜。縣衙主簿衙展室內更有詳細的圖解,里面有一句話叫“清朝與胥吏共天下”,由此可見古代胥吏的權勢。胥吏作為古代衙門機關工作人員,按道理,胥和吏本非一回事,吏是不入流的下級官員,胥則為官府里的充役之人,二者有著官民的分殊。可是自從宋代官吏分途以來,正經八本的讀書人羞于為吏,在人眼里,吏也就逐漸跟胥相混淆,被混稱胥吏。胥吏包括六房書吏和三班衙役,他們不僅不被人們視為“國家工作人員”,還被稱為“衙蠹”。幾乎所有的官場惡習,欺上瞞下,敲詐勒索,都跟胥吏有關。
但是,在封建社會,胥吏是離不了的,無論哪個朝代,胥吏都要占絕對多數,十倍,甚至數十倍、百倍于政府官員。清朝中葉以后,州縣的衙役和書吏,少則數百,多則上千。政府的運轉,實際上是胥吏在推動。
其實胥吏的危害,各個朝代都知道,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有時甚至低到了象征的地步。常識告訴我們,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是不行的,所以,象征性的工資,就等于默許他們自己想辦法。當然,凡是跟權力沾邊的所在,總能生出銀子來。既然上面不給銀子給“政策”,那么這些人撈過了頭,也就算不上是原則性問題,頂多是制度設計者的自作自受。
到此肯定有人會問,既然胥吏之害根源如此清楚,怎么就沒有人想法解決呢?換句話說,給他們足以養活家小的工資不就結了嗎?答案是,在那個時代,不可能。
在一個設官分治的農業國度里,政府的財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機構的征收能力。一般來說,征收的錢糧歸機關中的個人時,機關中人的積極性最強;征收歸機關,個人的積極性次之;征收歸國家,個人積極性最差。也就是說,交國庫的這部分,是地方政府中人最沒有熱情去征收的。如果國家統一發給所有政府機關中的人足額的工資,勢必要在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的同時,削弱機關中人征收的積極性,造成國庫收入不足。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往往要盡力縮小政府機關人員“吃財政飯”的比例,以減少國庫的壓力。也就是說,國家的財政不能變成“吃飯財政”。將“吏”排除在官員隊伍之外,壓低“胥”的社會地位,給他們一點微不足道的補貼,甚至對官員也采取低薪政策(最極端的是元朝,各級官員統統沒有工資),無非是把負擔丟給了官員和非官員的政府中人自己。
從另一個角度講,在一個同樣的農業國度里,當只有在政府里工作才是獲利最多,而且是最穩定職業的情況下,政府機關是不可能不膨脹的。如果把正式官員的員額硬性固定下來的話,那么吏和胥隊伍就要擴張。明清兩代,盡管吏的門檻一再提高,繳納銀兩逐年增加,但樂意充任者依然擠破門,有的人,寧可借貸,也要充吏。衙役也是如此,沒有人在乎其法律地位的低下,市井中人甚至城郊農民往往求一位而不得,于是正役之外有幫役,幫役之外還有白役。
在這種情況下,高薪養廉惟一的出路,就是壓縮政府機關中的人,但是壓縮只能壓縮正式的官員,那些半正式的政府機關成員吏和胥,以編外的形式膨脹,是根本擋不住的。壓縮不了人,只好中薪、甚至低薪養廉,但依舊擋不住人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例規化、封閉性的政府運作機制在清王朝實施,再加上清代地方政府設置承襲明代,分三房六班,使得地方政府的分工非常明確,然而這些條件卻造就了本身政治地位不高的胥吏有了以權謀私的條件。胥吏之害在清朝時期達到了頂峰,并且嚴重影響了清朝的的統治。
從執行層面來看,我總結的胥吏之治有以下3個危害:一是偎慵墮懶、怠惰因循。伴隨封建機構的完善,隨之而來的是行政工作的增加,胥吏隊伍擴充龐大。為了擴充隊伍,胥吏制度選拔水平的降低造成整體素質下降。胥吏工作水平不高、個人素質地下、品性懶惰,工作往往會不及時,使得工作得不到更為有效的開展。又因懶惰而造成監管不當,就無意間為不法之徒開了門。例如,被稱之為明朝的經濟命脈的后湖皇冊庫,用湖來保護庫內的皇家文件不受火光之災。但庫內胥吏對工作的怠慢,及明朝中后期胥吏工作不認真導致大量皇冊雜亂堆積、發霉發潮、鼠咬蟲害,甚至是人為盜竊。二是監守自盜,徇私舞弊。南宋時期市場上出現了書商所售之書是用官府公文、檔案的背面印制的現象。清代嘉慶年間,武清縣的魚鱗圖冊因為胥吏的破壞而毀壞殆盡,不少當地胥吏抱著偷拿來的魚鱗圖冊在集市上出賣。很多胥吏手腳不干凈,多為監守自盜。識貨一點的,將政府機密或文件作為有價值的情報出賣;愚昧的,干脆將官府東西當做二手、廢品賣掉。不少朝代反復在法律中強調禁止出賣文件、檔案,并且不斷加重處罰措施,但此類問題仍舊層出不窮。徇私舞弊,胥吏身在文書工作一線,“抱案牘而備繕寫”,卻往往會利用技術與文筆之便對官府文件進行小動作后徇私舞弊,以職務之便來謀取私心,更有甚者就會進行接下來要說的敲詐勒索。三是挾持官員,間接操縱權力。此為胥吏之害的最高形式,也是對封建王朝政權統治最壞的影響。一般情況下,胥吏在利用職務之便對律法、人事、賦稅等進行修改時就已經間接的干預了政務工作,甚至還可以憑借掌握人事而控制人權。當胥吏利用職務之便挾制官員,從而掌握處理政務的權利時,就為大問題了。明朝時,“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清朝胥吏把持政務的現象發展到頂峰,除了挾制本堂長官還會要挾下級衙署,胡作非為甚至彼此勾結。由于胥吏在此時隊伍整體素質偏低,于是造成清朝的基層統治質量的下降,再加之胥吏制度有子承父業的實習傳統,更早就了這種腐敗現象的無法無天,官府工作無法正確實施,胥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毒瘤,成為封建統治的壞根。
如果封建王朝對胥吏制度進行改革,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危害在設想中是可以緩解或弱化的:一方面能緩解胥吏職品低下,政治地位較為卑賤的局面。封建王朝后期,政府在為官者的選擇上以賢才、精英、科考成績合格者為途徑,讓官和胥吏的差距越來越大,胥吏的政治出路也非常的渺茫。照理說,科舉是每一個平民都可以應試的,但胥吏的子孫三代是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從根本上斷絕了胥吏后代參政的機會,無形中降低了胥吏的社會地位。相對來講,刑法方面:若是犯同樣的錯誤,胥吏所受刑罰則遠遠重于官員。這些造成的結果是胥吏對統治者的服從開始動搖。如果把胥吏編成正式的官員,其調動也與進士出身的官員相同(方法是擴大進士名額,然后讓進士從低級吏員做起),那顯然可以讓胥吏的仕途有盼頭,社會地位得以提高。
另一方面能緩解胥吏的收入問題。胥吏俸祿微薄,難養家庭,所以不得不另求它路以得“創收”。宋朝經歷了王安石變法,基層胥吏的收入由原來以賦稅為俸祿的形式變為由政法統一發放,在此基礎上胥吏的收入得以保障,這種做法在那個時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并不是每一個朝代都有王安石,宋朝滅亡以后,元代“重吏輕儒”,各衙門的胥吏俸祿已開始縮水。明代繼承元制,胥吏俸給賦予層級制度,級別品級越低著所收俸祿越少。清代胥吏無工食而僅有極少紙筆津貼,連衙役雖保留工食銀,同門子、皂隸、馬夫、禁卒等每人每年也只有六兩,這種情況下胥吏更得不到待見,但又必須贍養家庭,所以不得不走上歪路,走上敲詐勒索,收受賄賂。? 因此,胥吏之治在封建王朝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基層胥吏生活卻無法保障,于是胥吏管轄下的業務以其自身的價值變成為胥吏們“創收”的無奈途徑,并且隨著政府對胥吏刻薄的加深,胥吏之害在經濟上的表現更為眾多。在這種情況下,想改變胥吏制度,那在一定程度上應該也會相應提高他們的待遇,緩解胥吏的收入問題。
但就算改革胥吏制度,打開它的仕途,也不能從統治層面上、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封建社會,胥吏之害根除不了,根本原因在于古代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本身存在弊病,這是常識。通過擴大進士名額,然后讓進士從低級吏員做起來代替胥吏的做法也是不現實的,在古代并沒有那么多人讀得起書,更沒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到進士那一步。換個角度想一想,官府是權力,胥吏是執行,權力品級進階走向是前進的、上升的,胥吏職業生涯基本是靜止的。將胥吏的晉升之道與權力群體的晉升放到一起,那工作中官員的指揮和胥吏的執行如何協調?二者的利益如何分配?這是問題。如果干脆將二者合二為一,那會不會有新的群體代替“胥吏”的工作代替這個群體?這也是個問題。胥吏依附于官僚制度,官僚制度依附于皇權,而皇權的至高無上性與官權等級專制使得胥吏之害無法根除。胥吏之害通常嚴重于各個朝代的中后期,也正是封建王朝社會矛盾尖銳之時。土地制度遭到破壞,國家經濟賦稅必然遭到破壞,封建官僚腐朽落寞,往往到后期存在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的毛病,胥吏之術又有一定的家族流傳性,使得胥吏之害逐步深化。總體來看,古代胥吏制度利大于弊。
作者簡介:徐斌雷(1983.1-),女,漢族 河南內鄉人,專科,助理館員,研究方向為文物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