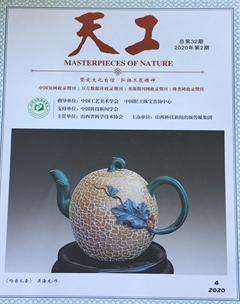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在雕塑中的運(yùn)用
[摘 要]中華民族是一個(gè)歷經(jīng)千年發(fā)展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民族,在這幾千年的文化發(fā)展過(guò)程中,勤勞而智慧的炎黃子孫將自己對(duì)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于大自然的某些事物之中,創(chuàng)造出獨(dú)具特色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題材十分豐富,表現(xiàn)形式也非常多樣,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之間的聯(lián)系進(jìn)行介紹,并結(jié)合古代與現(xiàn)代的案例,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與雕塑相結(jié)合的方式進(jìn)行概括,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運(yùn)用到雕塑中的原因進(jìn)行分析。
[關(guān)鍵詞] 傳統(tǒng);吉祥紋樣;雕塑
[中圖分類號(hào)] J306? ? ? ? ? ? [文章標(biāo)志碼] A? ? ? ? [文章編號(hào)] 2095-7556(2020)2-0064-02
本文文獻(xiàn)著錄格式:張江書(shū)芳.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在雕塑中的運(yùn)用[J].天工,2020(2):64-65.
早在古籍《莊子·人間世》便有提及“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成玄英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便是預(yù)示著好運(yùn)的到來(lái)。古人們對(duì)于天災(zāi)人禍充滿著畏懼,于是人們創(chuàng)造出與自然生物相接近的紋樣,更將希望寄托在一些帶有象征意義的紋樣上,認(rèn)為紋樣是能夠與自然、神明構(gòu)建溝通的橋梁,從而達(dá)到人們的期望。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與雕塑的結(jié)合運(yùn)用從古至今便一直存在,如石器時(shí)代彩陶上的紋樣等。中國(guó)人民經(jīng)過(guò)漫長(zhǎng)歷史歲月的不斷沉淀創(chuàng)造出形式豐富、造型優(yōu)美更具內(nèi)涵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中國(guó)文化的發(fā)展歷程,反映了不同時(shí)代中國(guó)人民的審美及其風(fēng)俗習(xí)慣,在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在雕塑中運(yùn)用的意義
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一小部分,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以一種獨(dú)有的方式傳承著,中國(guó)古代沒(méi)有像西方那么多有名的雕塑藝術(shù)家,但是在中華文化的影響下,中國(guó)雕塑有著特有的古樸風(fēng)格,也是這種特色讓考古學(xué)家在研究古代雕塑作品時(shí)不得不感嘆古人的智慧。羅丹曾說(shuō):一件雕塑唯一能夠讓你感到感動(dòng)的一定是這件雕塑作品背后的含義。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運(yùn)用在雕塑作品當(dāng)中體現(xiàn)了雕塑作品的文化性,恰恰雕塑作品也要借用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彰顯其獨(dú)特性。
城市是一個(gè)承載著大量信息的空間,并起著傳播的作用。信息的傳播一定是通過(guò)某種介質(zhì),廣告、新聞、廣播、雕塑等,以一種藝術(shù)的形式來(lái)傳遞精神與文化是雕塑作品或其他藝術(shù)形式的基本職責(zé)。城市雕塑佇立在某一特定區(qū)域起著獨(dú)特的藝術(shù)效果,具有特定的功能性以及對(duì)于地域文化的理解,在空間中起著傳播文化甚至在城市中起著精神象征的作用,成為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具有啟示的象征物體。那么,在雕塑中運(yùn)用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也是在向世人傳播中華傳統(tǒng)文化,增加民族認(rèn)同感和民族自信感。例如,韓美林放置在新疆克拉瑪依的城市雕塑《克拉瑪依之歌》就被認(rèn)為是這座城市的一個(gè)地標(biāo)建筑,《克拉瑪依之歌》以鳳凰為創(chuàng)作靈感來(lái)源,是對(duì)克拉瑪依的一種美好祝愿,希望這座城市展現(xiàn)出欣欣向榮、生氣勃勃的景象。
二、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在雕塑中的運(yùn)用
(一)平面繪畫(huà)式的運(yùn)用
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在宏觀上深深地根植于不同時(shí)期的物質(zhì)基礎(chǔ),其所展現(xiàn)的不同特點(diǎn)也可以反映時(shí)代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情況和特色,雕塑的設(shè)計(jì)澆筑了人們的情感和審美。將紋樣運(yùn)用在雕塑表面作為一種裝飾性紋樣是雕塑與吉祥紋樣相結(jié)合當(dāng)中最常見(jiàn)的一種造型藝術(shù)形式,這是將紋樣的二維繪畫(huà)藝術(shù)與雕塑的三維立體造型藝術(shù)相結(jié)合。造型藝術(shù)是一種非常直觀的、可觸可視的形式。造型藝術(shù)形式的特點(diǎn)是將動(dòng)物、植物等傾注人類的想法賦予其深刻的含義,比如龍鳳紋象征著帝王帝后,是權(quán)力與身份的代表,龜紋代表著長(zhǎng)壽。坐落于廈門(mén)中山路上的《龜之戲》是2007年由廈門(mén)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的李金仙教授創(chuàng)作的城市雕塑,它是由三個(gè)刻有龜紋、龍鳳紋、魚(yú)紋等的紅龜磨具構(gòu)成的,色彩運(yùn)用傳統(tǒng)的中國(guó)紅,造型簡(jiǎn)潔、活潑,既吸收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的樣式,又考慮了現(xiàn)代雕塑的審美與空間放置,是一件結(jié)合中國(guó)古代傳統(tǒng)吉祥紋樣與現(xiàn)代特點(diǎn)的優(yōu)秀雕塑作品。整個(gè)雕塑是時(shí)尚與古樸完美的結(jié)合,在街頭給人帶來(lái)美的享受的同時(shí)也傳播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不得不令觀者駐足留念。
(二)立體式的運(yùn)用
1.基本型改造
時(shí)代在發(fā)展,世界在進(jìn)步,但是人們對(duì)于美好東西的向往是不變的。人們對(duì)于事物的認(rèn)識(shí)、理解、情感是會(huì)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而不斷地變化,這種變化是每個(gè)時(shí)代的藝術(shù)家都在探索與追尋的東西,只有賦予時(shí)代意義與激情的雕塑作品才會(huì)被認(rèn)可。現(xiàn)代雕塑在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當(dāng)中相互影響,力求設(shè)計(jì)出既有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內(nèi)涵又有現(xiàn)代雕塑的獨(dú)特造型的藝術(shù)形式,可能這些造型與傳統(tǒng)吉祥紋樣已大不相同,但是卻有其獨(dú)特的韻味。
在現(xiàn)代雕塑設(shè)計(jì)時(shí),對(duì)于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進(jìn)行基本形式的改造是很常見(jiàn)的,古代的一些吉祥紋樣,特別是青銅器上的紋樣直接使用往往會(huì)顯得格格不入,那么這就需要我們?cè)诒A糁袊?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特點(diǎn)的情況下對(duì)其造型進(jìn)行加減法,使得紋樣更加符合雕塑的設(shè)計(jì)。例如,由韓美林先生設(shè)計(jì)的2008年北京奧運(yùn)會(huì)的吉祥物令人印象十分深刻,這五個(gè)福娃的造型一經(jīng)亮相,便引起了全國(guó)人民的極大關(guān)注,其形象就是分別來(lái)自于魚(yú)紋、蓮花紋、火紋等,既體現(xiàn)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又賦予了時(shí)代特征。
2.分解與轉(zhuǎn)化
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大多形式復(fù)雜,這就要求我們對(duì)其進(jìn)行分解轉(zhuǎn)化,雕塑家可以只從某一種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當(dāng)中選取自己最想用的那一部分來(lái)表達(dá),然后將這一部分進(jìn)行打散重新排列或是將其進(jìn)行收縮、扭曲等方式重新創(chuàng)造。例如,韓美林先生的《和平守望》,他將下面的根盤(pán)成了非常典型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中國(guó)結(jié)。又如,曾成鋼先生的作品《起舞》,這是他為銅陵市創(chuàng)作的城市雕塑,它的造型來(lái)源于銅爵,并且非常大膽地將整體抽象化但又不失銅爵的基本輪廓,他向人類傳播了中國(guó)歷史上重要的青銅文化,是一件非常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雕塑作品,同時(shí)也融合著西方的抽象,其身上的兩組銅紋飾仿佛將人們拉回了三千多年前,是一件非常經(jīng)典的現(xiàn)代與古代、傳統(tǒng)與時(shí)尚相結(jié)合的作品。
三、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對(duì)雕塑創(chuàng)作的啟發(fā)
(一)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運(yùn)用在雕塑中的情感
在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與雕塑結(jié)合的案例分析與研究中,我們看到傳統(tǒng)文化與雕塑的完美融合,紋樣的使用給現(xiàn)代雕塑增添了一抹古典之風(fēng)。韓美林先生的雕塑作品非常注重中國(guó)傳統(tǒng)紋樣和結(jié)構(gòu)的裝飾感,并將其運(yùn)用成自己獨(dú)有的藝術(shù)形式,創(chuàng)造了具有現(xiàn)代性的雕塑風(fēng)格,給人的心靈產(chǎn)生極大的震撼。韓美林先生曾說(shuō)過(guò):“一件雕塑作品要做到就算小偷走到它面前也得屏住呼吸,感覺(jué)不能再偷東西了。”
雕塑設(shè)計(jì)形式多樣,不同的設(shè)計(jì)風(fēng)格和造型反映著設(shè)計(jì)師不同的設(shè)計(jì)理念與審美風(fēng)格,但是情感是不變的。曾經(jīng)聽(tīng)過(guò)這樣一句話,每個(gè)藝術(shù)家都是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只有有情感、有寓意的作品才會(huì)有感染力,情感構(gòu)成的橋梁才能使創(chuàng)作者和觀賞者達(dá)到心靈上的共鳴,沒(méi)有故事的作品設(shè)計(jì)是蒼白的。或是抽象簡(jiǎn)約,對(duì)紋樣進(jìn)行加工提煉,不失傳統(tǒng)的韻味就像曾成鋼先生的作品一樣;或是符號(hào)拼貼,或是移植與嫁接,并且可以結(jié)合新的技術(shù)與工藝對(duì)傳統(tǒng)吉祥紋樣進(jìn)行拓展,創(chuàng)造出具有現(xiàn)代特征的作品。
(二)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在雕塑中的運(yùn)用前景
時(shí)代在不斷的發(fā)展,發(fā)展過(guò)程中很多東西會(huì)消逝同樣也會(huì)產(chǎn)生很多新的東西。傳統(tǒng)吉祥紋樣這一中華民族的瑰寶,歷經(jīng)幾千年的發(fā)展至今而未消失,而是在歷史的洗滌下不斷地產(chǎn)生新的內(nèi)容和表現(xiàn)形式,到現(xiàn)代也會(huì)產(chǎn)生適應(yīng)時(shí)代的新作品。據(jù)調(diào)查中國(guó)各地的文化古跡、文化旅游景點(diǎn)的游客數(shù)量直線上升。筆者認(rèn)為,作為雕塑專業(yè)的學(xué)生,將來(lái)的雕塑工作者,應(yīng)該在主觀上有意識(shí)地在作品中運(yùn)用傳統(tǒng)吉祥紋樣的元素,同時(shí)我們也要結(jié)合時(shí)代的特點(diǎn),進(jìn)行創(chuàng)新創(chuàng)作。我們期待在這全新的時(shí)代環(huán)境下,藝術(shù)工作者能夠創(chuàng)作出具有中華傳統(tǒng)文化特色又符合時(shí)代發(fā)展趨勢(shì)的雕塑作品。
從青銅器到韓美林的《和平守望》,我們看到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的表現(xiàn)形式一直在變化,使用的材料也在不斷變化。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我們也創(chuàng)造出多種不同于古代的材料,所以進(jìn)行雕塑創(chuàng)作的材料選擇范圍也更加廣闊。因此,在進(jìn)行雕塑創(chuàng)作時(shí),我們也要考慮紋樣和材料的結(jié)合是否巧妙。
綜述上文,我們不難看出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無(wú)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xiàn)代雕塑創(chuàng)作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要與雕塑的造型相契合,才能更好地增加作品的內(nèi)涵。雕塑的創(chuàng)造過(guò)程就是雕塑家表達(dá)內(nèi)心情感的過(guò)程,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的運(yùn)用便是一種表現(xiàn)手段。一件優(yōu)秀的雕塑作品必定是兼顧內(nèi)涵與形式的,我們?cè)趧?chuàng)作過(guò)程中要力求二者的和諧統(tǒng)一,無(wú)論是類似于古人將紋樣作為一種二維的繪畫(huà)藝術(shù)運(yùn)用在雕塑表面,或是像紋樣進(jìn)行改造,又或是將其分解轉(zhuǎn)化等形式的運(yùn)用,又或是幾者的相結(jié)合,都是我們表達(dá)內(nèi)心感受進(jìn)行雕塑創(chuàng)作方式的一種。
參考文獻(xiàn):
[1]陳慎.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初探[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xué),2009.
[2]孫澤楠,馬艷.淺析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在現(xiàn)代室內(nèi)木雕壁畫(huà)設(shè)計(jì)中的體現(xiàn)[J].大眾文藝,2017(14):76.
[3]李思皓.傳統(tǒng)吉祥紋樣在當(dāng)代風(fēng)景園林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J].美與時(shí)代(上),2015(2):65-67.
[4]趙軍霞,張瑜.基于中國(guó)傳統(tǒng)吉祥紋樣與當(dāng)代藝術(shù)設(shè)計(jì)融合研究[J].科技創(chuàng)新導(dǎo)報(bào),2014(32):218-219.
[作者單位]
福建師范大學(xué)
(編輯:劉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