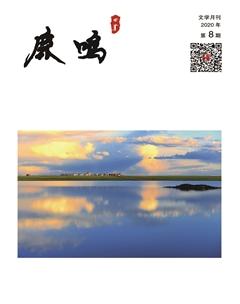四毛猴(外兩篇)
張榮
黃昏,七月的火熱漸漸退去,回到家,盛夏的炙熱與燦爛都擋在了窗外,一張冰爽的面膜貼在驕陽炙烤后微紅的臉上,打開音響,閉著眼睛躺下來。一首老歌《雁南飛》。一個年輕柔美的男聲翻唱。突然,就想起了她。
第一次在深夜里穿過鄉間小路去鄰村看露天電影,就是這個片子,《歸心似箭》。初冬,蒼茫的原野漆黑一片,漫無邊際地游蕩著料峭的冷風,村落里暗淡稀疏的燈火閃爍如散落的星辰,我穿著鄉下孩子笨乎乎的棉襖棉褲,緊緊抓著她的手,跌跌撞撞地貼在她身邊,興奮、好奇、害怕著。
電影開演了,灰烏烏的樹林,穿著破衣爛衫的人,激烈的炮火打過之后,我開始斷斷續續犯困,等到她摸著我的頭叫醒我時,電影已近尾聲。畫面上,深秋碧藍的天空里緩緩地飛過人字形的雁群,一個穿著軍裝的男子仰面望著天空,滿臉堅毅,一個梳著舊式發髻的女子滿懷期待的眼神,落木無邊。回家的路上,她問我電影好不好看,我撅著嘴埋怨她:“我都沒看見,你為什么不叫醒我?”聰明的她居然將電影插曲《雁南飛》學會了一大半,第二天帶我玩時就教我唱。她喜歡唱歌,學得快,唱得也特別好,是我童年里最好的音樂老師。她曾試過考旗里的烏蘭牧騎,因為胖而落選。后來,我上學了,我們學校沒有音樂老師,語文老師問誰會唱歌教大家唱唱,同學們的小手指一致指向我。從此,我成了班里的兼職音樂老師,我把她教給我的歌,教給全班同學,直到我離開。
我出生的時候,她12歲,記事起,她就是我的好伙伴,因為隔著幾十里的路,我們不常見面,但如果有一天回到家看見她來了,那種興奮與欣喜,什么都無法代替。姥姥生了四個女兒、一個兒子,她是最不值錢的老四,她有個不招人待見的外號叫“四毛猴”,我常常在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后,撕心裂肺地喊著這個外號罵她,她看著我氣急敗壞的樣子笑得前仰后合。她一直是胖乎乎的,一點都沒有“毛猴”的感覺,也不漂亮,大臉盤、小眼睛,但她從來都是沒心沒肺地快樂著,她不用大人的規矩要求我,任由我鬧翻天。
童年時代,我去姥姥家唯一的目的就是和她玩。住上一段時間,玩夠了,她就騎自行車送我回家。幾十里路,她頂著西北風馱著胖乎乎的我,騎得呼哧帶喘。北方冬天的鄉間小路,泛著冷硬的灰白,彎彎曲曲穿村過梁,我們一路走走停停,穿過寂寥的冬的原野、陽光和冷風。她怕我睡著,不停地和我說話。途中的某村有個稀缺的供銷社,推開油漆斑駁的木頭門,一股醋醬油與糖果交織的新鮮味道便撲面而來,每次路過都要進去,即使什么都不買,能聞一下那個味道便是快樂。供銷社的玻璃柜臺里陳列著糖果、針線,我最喜歡的一欄是小人書。那次送我,她神秘地對我說:“兩毛錢以下的小人書,挑一本,四姨給你買。”我趕緊把小臉貼在冰涼的玻璃面上挑選。指指這個指指那個,反悔了無數次后選定了封面是個漂亮女子的那一本。小人書一毛三,四姨用剩下的幾毛錢買了水果糖,那是給我和妹妹的禮物。我揣著生平第一本小人書,興奮地走出供銷社,四姨剝了兩塊糖,我倆一人一塊,清甜的橘子味霎時溫暖了漫長的路途。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給妹妹顯擺我的小人書,才發現,封面好看的小人書原來寫的是養豬的事,我立刻悔青了腸子,而四姨卻在一邊笑我這就是不識字的代價。
又一年的冬天,爸爸去城里給村里搞副業,她奉命來我家幫我媽媽料理家務,但貪玩的她一有時間就帶著我溜出去玩。冬的黃昏,清亮的空氣是透明的藍,緋紅的彩霞給地平線鑲上一道漸變色的金邊,枯樹旁逸斜出地畫在柔美的底色上,在晚歸的羊群騰起的金色塵埃里變成一幅安謐、悠然、漂亮的畫。我穿著厚厚的棉衣跟在她后面跑得滿頭大汗,小臉累得通紅,不住地咳嗽。媽在身后使勁喊我們,我們假裝聽不見,任憑衣兜里的炒大豆嘩啦嘩啦往外撒。那年,她19歲,本該是鄉下的女孩最安靜的年齡,因為這時會有眼尖的家長和熱心的媒婆留意上她們。但“四毛猴”沒有這個概念。她二姐,也就是我媽,幾乎每天晚上都恨鐵不成鋼地板著臉在煤油燈昏暗的影子里訓她,我作陪,怯怯地站在她背后生怕被連坐。訓斥的結尾永遠是:“那么大人了,一點規矩都沒有,就知道‘奔刀子,不怕人笑話?”“奔刀子”這個詞,是典型的巴盟方言,我在普通話里找不到相應的詞來代替,意思是貶義的“到處亂跑”。但是,我卻寧愿咳嗽,寧愿把炒大豆撒一地,也要跟著她“奔刀子”。那年,她的厚棉襖外面穿著一件褪了色的黑紅相間的格子外罩,上面綴著幾粒黃綠色的有機塑料紐扣,用手搓一會兒,就有淡淡的糖果的甜香,不知道城里的孩子還記不記得這個富有時代感的特殊物件,我記得。我無數次抬起胖乎乎的小肥手去搓她的紐扣,仰起紅通通的臉去嗅那種誘人的味道。很多年過去了,想起童年,總有那種畫餅充饑的甜味穿越悠遠的歲月回來,那仿佛也是她的味道。
仿佛就是第二年的春天,她突然就訂婚了,再來我家時,她燙了一個時髦的卷發,圍著一條那年頭能讓所有鄉下女孩眼珠子掉出來的黑白紅三色相間的毛圍巾。像個大人一樣接受完我家人的恭喜之后,就偷偷地拉著我的手跑到一邊,她從褲兜里摸出一塊漂亮的美人圖案的手絹興奮地對我說:“你看四姨這個新手絹。”結果當然又是我用一塊臟兮兮的擦鼻涕手絹換走了她訂婚的新手絹。不久,她就結婚了,四姨夫是城里的知青,家里窮點,但是人長得非常帥,我傻乎乎地吃著糖,高興的不得了。出嫁之后不久,她就把那條讓我掉眼珠子的三色圍巾送給了開始懂得趕時髦的我。那條圍巾厚墩墩的,戴在脖子里熱乎乎的,我戴了很多年,上初中時,它終于不再時髦,表姐用它給外甥女做了一條褲子。許多年后,我突然很后悔沒有把它保留下來。
13歲時,我來城里的大伯家讀書,和她相隔十幾里,每到星期天,我就獨自坐著公交車去她家。那時,她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生活拮據,不得不四處打臨工。但每次去,她都會給我做好吃的,大多數是包餃子,再買一點別的水果蔬菜。因為忙,她的家里一點都不干凈整潔,但我還是喜歡去,我喜歡站在她家黑乎乎的廚房邊上看她撈出熱氣騰騰的餃子,直到現在,我還是最愛吃她包的餃子。走時,她也總會給我幾毛錢,讓我買車票、買零食。學校門口有二分錢一杯的沙棗和炒葵花籽,她給的小錢夠一周的零花。
我上五年級的那個夏天,她在建筑工地上當小工,一次去她家,恰好在公交車站碰見了她,她穿著四姨夫淘汰的破舊工作服,戴著一頂破舊的男式帽子,灰頭土臉地往家走,正午灼熱的陽光打在她曬得通紅的臉上,那么無精打采。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她的無奈,生活的艱澀使得她不再是那個帶著我漫山遍野“奔刀子”的“四毛猴”。很多年后想起這一幕,仍是辛酸。那天,她在回家的路上買了菜和肉,給我包餃子,回時,她送我,上車時,她往我衣兜里塞了兩塊錢,說:“自己買點吃的,四姨上班掙錢了。”因為知道她生活的艱苦,此前,媽特地安頓過我,不許要她的錢,她就用那樣的方式給我。到家時,我發現,寶貴的兩塊錢竟然被小偷偷走了,為此,我懊喪了很長時間,不是因為兩塊錢可以買多少零食,而是,她要在烈日下工作多久才能掙到那兩塊錢。
時光,在聚聚散散中悄然飛逝,此后,我奔走在求學的路上,見她的次數不再頻繁,直到父母遷來城里定居。我們再次成了彼此家里的常客。那時,她已完全適應了城里的生活,雖然仍舊是打工,但經濟條件好了很多。她時不常地給我買一些父母并不贊同的時髦衣物,圍巾、涼鞋、裙子、毛衣什么的,每一件都是我最喜歡的禮物,為我青春路上的光彩添上濃重的一筆。每年過年,我們兩家固定聚兩次,她會把最豐盛的飯菜留到我們來。她的廚藝日益精湛,我爸打趣她:“啥也不會干的四毛猴,現在總算出息了。”她則大著嗓門回擊我爸:“你以為呢,我現在不是‘猴了,我進化成人了。”我們便大笑。
不知不覺中,我長大了,她就老了。表妹結婚了,有孩子了,她晉升為姥姥了……大表妹的孩子過生日,她上臺講話、唱歌,優美高亢的聲音再次帶我回到童年,我在狠勁兒鼓掌的同時溢上淺淺的淚。接著,她邀請我上臺唱歌,向所有的來賓介紹她心目中優秀的外甥女。我看著臺下起勁地為我鼓掌的她,燦爛的笑容如花般綻放在她沉淀了半生歲月的臉上,往事歷歷再目。
原來,無論時光怎么轉變,在我心里,她,永遠是那個給我買小人書、和我交換手絹、給我包餃子、拉著我的手陪我穿過故鄉廣袤原野,帶我看電影的“四毛猴”。
你是原野里的蒲公英
如果每個女人都是花,那么,她一定就是初春原野里最早盛開的蒲公英,一點若有若無的嬌黃怯生生地綴在稀薄的綠草間,等待踏春的人來觀賞,而假如整個春天都不曾有人來,便在春末白了頭,乘一段寂寞的清風飛向天涯。她就是這樣的。
我記事的時候,她的腿就壞了,冬天坐在炕腳的陽光里,夏天坐在大門口屋檐下的石墩上,納著一年四季都納不完的鞋底,旁邊是一杯水,一本書,一支用鐵鍬把改制的拐杖。渴了喝水累了看書,上廁所就扶著墻很吃力地起來,拄著拐杖慢慢地挪著走。如果我正好在旁邊,她也會微笑地看著我說:“來,當個拐棍。”我便趕忙站起來去托著她的手,幫她站起來。
她不漂亮,個子不高,雖然是貧瘠窘迫的年代,但常年的不能行走也導致了微胖。她是村里那個年齡段唯一識字的女人,我們是親戚,我管她叫大嫂,她的小女兒美和我同年,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美總有太多干不完的活兒,每次去找她玩,她總是讓我等著她干完活后才能跟我一起玩,我坐在大嫂的旁邊等著美,大嫂就和我聊天,她從不把我當小孩,問我家里的事情也講很多大人的道理給我聽。
鄉村的冬天寂寞而漫長,放露天電影可謂一件盛事。每當趾高氣昂的電影放映員馱著大箱子出現在夕陽那一端,孩子們就炸了窩。我和美第一時間來到放電影的空地上,給大嫂和各自的奶奶占位子。深夜無邊,我和美以及家里的其他小孩,圍著溫暖的棉被,挨挨擠擠坐在大嫂旁邊,衣兜里裝滿炒瓜子和大豆。花花綠綠的電影,大多看不懂,遇上她熟知的題材,大嫂會給我們略略講一下電影的背景和相關歷史事件,我的腦海里便會出現種種聯想。
上了學以后,迷上了大嫂那兒的書。她的書其實不是她的,是她的大女兒大美走街串巷借來的,大多是連環畫,圖文并茂引人入勝,有了小人書,等美的時光不再單調。《紅樓夢》《聊齋》是我最喜歡的。因為是借來的,她把書鎖在窗下的小紅木箱里,有書時,她會讓我自己上炕去取。取了書,我如獲至寶,便安靜地坐在她旁邊磕磕絆絆地讀,遇到不認識的字就問她,她很喜歡教我認字并給我講解。白天,我沉靜在撲朔迷離的故事里,晚上做著千奇百怪的夢,我的童年時代,大約有一半時間在她家度過。再后來,我借堂姐的語文書看,依舊坐在大嫂旁邊的小板凳上,遇到那么多不認識的字,都一一問她。她納著鞋底,結實的麻繩穿過厚厚的布底,發出細微的嘶嘶聲,美剁豬菜的當當聲空曠地回蕩著單調日子的余音。沙棗花開了,暗香隱約從熟知的那幾棵樹上氤氳而來,美好的童年就那樣在漫長的等待和生澀的閱讀里偷偷溜掉了。
長大了,斷斷續續從大人們口中知道了大嫂的故事。她是饑荒年代從外省來的,那時,雖然瘦弱但雙腿是健康的,因為要生存,她的哥哥將19歲的她嫁給了我大哥之后,便離開了。所以,在我們村,她沒有任何親人。也不知道為什么,她和大哥的感情似乎不是很好,她生了第二個兒子之后,一場大病使她再也站不起來了。慢慢地,所有人都叫她“拐子”,包括她的婆婆,對于這個帶著輕蔑的稱呼,她似乎也能平心靜氣地接受。腿拐了之后,她又生了三個孩子,可是,慢慢地,她和大哥的感情就更不好了,慢慢地,村里關于大哥的傳言多起來。記憶里,大哥從來沒有笑臉,我也沒見過他和大嫂說過一句話,只要他回來,家里所有的人都會變得小心翼翼,連我也會識相地趕緊逃跑。很多年之后,有了愛人,有了孩子,才知道那時候的大嫂守著一個沒有溫暖的男人是多么痛苦,才知道她不讓孩子們出去玩是害怕孤獨,才知道我的存在也曾給她帶去過快樂。而大哥,一定也有著說不出的苦。那是一個艱澀而隱忍的時代。
12歲那年,我要外出上學,走之前的一段時間,她總是笑著調侃我:“啊呀,這是要當城市人去了吧?走出去也別忘了這土窩窩哦。”我說:“那是當然的”。寒暑兩個假期,我一如既往往她家跑。找美玩,也找她聊天,聊城里的見聞,聽她的夸贊。就在這年,她的病情進一步惡化還引發了哮喘,過年時,人們都說她胖了,其實是浮腫。大年初二一早,我去給她拜年,她穿著新做的灰布外套,坐在炕沿邊,疲倦地和我說笑,喉嚨里不時有絲絲的喑啞。她的鐵鍬把做的拐杖已好久不用,寂寞地立在水缸旁。
第二年8月,我開學前夕的那個黃昏,我大娘驚惶失措地來喊我媽說:“拐子不行了。”我心里很是驚慌害怕,想跟著媽去看一看她。可是奶奶說:“不要去了,你還是小孩呢,明天又要出門走遠路,你大嫂可能是不行了。”我便獨自坐在離她家不遠的矮墻上,等著我媽帶回好消息。太陽即將落山時,聽見美撕心裂肺哭喊媽媽的聲音,我知道那是大嫂走了,我跳下來跑到墻角,眼淚嘩嘩地流下來。那年,我和美都只有13歲。
第二天凌晨,我離開家鄉回城里上學,我不知道大嫂的葬禮是怎樣的情形,可眼前總清晰地浮現出:蔽舊的灰白厚帆布搭起簡陋的靈堂,金黃耀眼的棺材前擺著呆板的紙人紙馬紙房子,棺材里裝著伴我走過快樂童年的她。她的孩子們跪在黝黑的瓷盆前,紙錢與紙灰隨風飛揚……初秋的晨光微曦,圍攏了送葬的人群,美穿著大孝的瘦弱身影……
15歲那年,爸媽帶著我們全家搬離故鄉,此后二十幾年,都不曾回去。我和美還有她的哥哥姐姐們都極少相見了,偶爾有彼此的消息在親戚間傳遞,我總是不斷地想起那時單純美好的時光。十幾年前,大哥過世了,下去陪她。
我不知道她的兒女如何回憶她,可是我,總在四月的風掠過原野時,想像她的荒冢,想起她渴望完美卻最終抱恨而去的人生。
如果每一個女人都是一種花,她一定就是原野里的蒲公英,曾寂寞無聲地盛開在無人問津的春風里……
素箋流年
秋風又起,瑟瑟地掠過白楊,便有鑲了黃邊兒的葉飄下來,落在皺著波紋的水塘上,一蕩一蕩沉下去。周邊的平房拆了又拆,一圈蔓延的荒草,一片林立的高樓,小村散落的十幾戶人家,世外桃源般過著隔絕的日子,幾十口人望眼欲穿地期待著拆遷,但這中間不包括秀兒。這是2006年的金秋九月,距那些歡笑與淚水的過往又遠了一年。
哥哥第一次來她家,就是這樣的九月,碧藍的天空上流過潔白的羽狀的云。15歲的秀兒拖著系了紅綢的麻花辮站在灼灼的陽光下,怯怯地望著陌生的他。母親的臉上現出平時鮮有的笑喊她:“這孩子,愣啥?這是你三姨家的小杰哥哥呀,幾年不見,認不出來了?”三姨是母親遠房的表妹,若在老家,這樣的親戚大約和鄉鄰沒什么區別。可是,在這舉目無親的異鄉,母親和三姨竟情同手足。至于小杰哥哥,秀兒是真的記不起來了,也許就是三姨家那個逮了螞蚱往她衣領里塞的頑皮小子吧。可是,面前的他高大英俊又斯斯文文,完全不是昔日剃著光頭、拖著鼻涕的頑劣模樣。
那年,哥哥19歲,報名參軍,入伍之前奉母親之命來看望二姨。那年,秀兒剛升入初三,開學不久便逢鄉下中學為鄉下老師而特設的“農忙假”。母親在田里忙碌,客人便全程由秀兒來陪。哥哥高中畢業,廣博的知識讓秀兒嘆服。空寂的打麥場,麥事已畢,只留下一垛垛金山一樣泛著黃光的秸桿兒,秀兒帶著自家的花狗坐在麥秸垛的陰影里,聽博學的哥哥講《紅樓夢》。秋陽里,淡粉、淡黃的野花頻頻地隨風搖曳,秀兒想象著林黛玉的裙據,也有淡粉淡黃的碎花隨著她輕盈的步態而搖擺。遠處的魚塘波光粼粼,為僻遠而單調的鄉村添上一道亮麗的風景。許多年后,秀兒看見這魚塘,就會想起哥哥繪聲繪色的講述:“這個妹妹,我見過的。”這是寶黛初會時,賈寶玉的臺詞,而誰的人生會一如初見般美好?
那次,拗不過秀兒的挽留,哥哥在她家住了七天。七天,之于人生不過瞬間,于小杰,卻是一生中美好時光的開端。他猜想,秀兒留他也許不過是想聽完《紅樓夢》,而他卻深深被秀兒的單純美麗所俘獲。鄉村九月的黃昏,透明而燦爛,向日葵收攏了花瓣,層層疊疊地低了頭,在夕陽里涂抹了滿身金黃,下地的人們三三兩兩地歸來,拖著散漫隨意的腳步。哥哥陪著秀兒抱柴做飯,秀兒挽起碎花布襯衣,露出潔白的小臂,嫻熟地在露天的灶臺邊灌開水、切菜、削土豆。哥哥在灶邊的木凳上坐著,柔情蜜意地看著她,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偶爾添一把柴。紅黃的爐火烘烤著他的臉,也烤熱了他的心。
分別時,秀兒送哥哥到村口的水塘邊,沒有了故事可講,似乎已找不到話題。秀兒緊緊抿著嘴望著遠處日漸蒼黃的大地,情竇初開的小杰則目不轉睛地望著秀兒天真的眼睛、長長的麻花辮、白底藍花的小布衫。車快來時,小杰摸出鋼筆遞給秀兒,讓她把學校的地址寫到他掌心里。終于,晚點的公交車稀里嘩啦從黃土里騰過去,小杰走了。秀兒不知道,?他剛一落座便緊緊握起手掌流淚了。
不久,哥哥寫來了信,一張穿著軍裝的照片英氣逼人,他鼓勵秀兒好好學習,外面的世界很廣闊,有著數不盡的新鮮東西。哥哥的信,是秀兒生平接到的第一封信,她當晚便在昏暗的燈光下給他寫了回信,第一次寫信,不知道該怎么寫,便東拉一句,西扯一句,居然寫滿了兩頁信紙。
那年春節過后,秀兒突地長大了許多,一個寒假沒有收到哥哥的來信,她居然開始心慌意亂。再次給他寫信時,她居然開頭就寫上了“親愛的哥哥,我好想你!”她不知道,這句含糊不明的話竟讓小杰用幾個不眠之夜去玩味,仿佛也是從此,秀兒和小杰都明白了彼此的心跡。此后的信件往來便是最火熱的情書。
服役的第二年,小杰考上了軍校,有了自由的寒暑假。第一個寒假的第二天,便借著看二姨的借口來看秀兒。秀兒初中畢業進了工廠,已出落得如花似玉。深冬的黃昏,夕陽一躍入山坳,大地便被暗淡的藍霧籠罩,結了冰的魚塘似一面巨大的鏡子反著月白的光,高大古老的枯樹背面,小杰輕輕將秀兒擁入懷中:“秀兒,你等我三年,一畢業我就讓我媽和二姨說,我帶你離開農村,去我工作的地方,一起生活再也不分離,你愿意嗎?”那是秀兒憧憬過無數次的未來,哥哥給她描述的城市,無數次出現在夢境里,怎能不愿意。那晚,哥哥將秀兒裹進軍大衣,輾轉地親吻。清亮亮的月光為證,秀兒的心里再也容不下別人。
秀兒的母親是三村五里出了名的厲害角色,為人精明能干又伶牙俐齒,不僅對丈夫兒女說一不二,就是在鄰里之間也是名聲在外。秀兒從小對母親百依百順,所以那年,當三姨親自來問二姐是否能結個親家之時,秀兒的母親震驚之余終于惱怒:“你也不怕別人笑話,咱們是姊妹,怎么能結親家?”繼而數落小杰:“你怎么也跟著你媽起哄,她是你妹妹。”小杰拿出血緣關系的親疏分析,終沒抵過二姨一句“怕別人笑話。”母親的決絕只能讓秀兒偷偷抹淚。被拒絕的那個盛夏,哥哥來看她,只要沒有別人,秀兒就對著小杰哭。一個月明星稀的午夜,秀兒試圖偷偷溜進小杰的房間……以為木已成舟母親能屈服,可是,女兒的行徑激怒了母親,她背著秀兒跑到三姨家,一通謾罵從此不再來往。
小杰不肯屈服,依舊給秀兒寫信,寫到單位,他開了工資給秀兒買禮物寄來,棉布碎花的連衣裙、開司米毛衫。每個暑假,秀兒會偷偷去看望小杰,在遠離人群的山坳里,秀兒枕著小杰的胸膛,青石崖上,綠樹蔥籠,流云掠過山巔投一片淡淡的影子在身邊,秀兒無數次期望時光就此停止,好讓她的愛情能夠持續到永遠。小杰說:“永遠,就是你離開家,和我一起走,我們不是封建社會任人擺布的《紅樓夢》。”秀兒也幾次動了心,可是最后也沒能下決心。說不清是誰毀了秀兒的愛情。此后,哥哥仍不斷地來信叫她去找他,她卻終于沒有勇氣再邁出一步。
哥哥36歲那年結了婚,三姨親自來邀請秀兒及母親,她哭著來又哭著走,老姐倆倒是和好如初了,但三姨沒見到秀兒。秀兒躲在魚塘邊的老樹下,看著三姨的背影消失在白花花的鹽堿地那邊,眼淚嘩嘩地流下來……相聚無望,是秀兒先提出分手讓哥哥另覓愛侶,不再給他回信,讓他斷了念想。可心中的劇痛怎能自禁。
秀兒從此關閉了愛情的門,閑暇之時,她學會了做手工、剪窗花、織毛衣、工藝品刺繡和后來的十字繡。填滿了每一個時段的空檔,她便不再思念他。母親似乎發動了她所有的三親六友給秀兒介紹對象,可是秀兒一個都不去看,秀兒40歲那年,母親去了。她去時,秀兒哭得死去活來,那一刻,曾為母親犧牲過的愛情成了一樁不足掛齒的小事。
父親搬到了弟弟家,唯一的家產留給了沒成家的秀兒。秀兒守著生她養她的這一方土,守著曾經有過美好愛情的地方,漸漸地安之若素。母親去世后,秀兒信了佛教,工作之余便潛心研究佛經,她知道自己最終也研究不出什么名堂,但她相信,來世,一定能和他一起走。
哥哥婚后在千里之外的一個小城定居了,聽說,那是個山清水秀的地方,想必嫂子也是秀美過人的吧,秀兒不曾見過。其實,小杰的妻子相貌平平,只是初識時有一條與秀兒一樣的大辮子。當城里的女孩紛紛亮出各色發式時,她為他守住了麻花辮的夢。也許時間真的能讓一切改變,哥哥轉業了,哥哥回家過年了,哥哥喜得貴子了,盡管他不再來看她,他的種種消息她還是有的,而終于,終于能將他當成一個遠親家的哥哥。
流年似水,從秀兒早已平靜的心間匆匆淌過,對于她來講,天長地久抵不過曾經擁有的美麗過往。哥哥十年寫來的信,2389封,整整一個書柜,收藏了秀兒的一生。
那是從前,是車馬慢、信件也慢的日子,仿佛一生只可以愛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