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縫隙就是詩的縫隙
文 | 杜鵬
第一次記住呂德安這個名字,是在一本由米家路教授編選的旅美華人詩歌選集《四海為詩》里讀到的他的那首《古琴》。以前只知道他是“第三代詩人”中的代表詩人之一,但并沒讀過他的作品。《古琴》中有這樣一句詩,“房間里多出一個洞穴的生活”,這句詩一下就擊中了我,并讓我回味了很久。當時我對呂德安的背景知識了解幾乎為零,但是這句詩讓我產生了一種對一個詩人生活的想象,想象他或許真的在過一種游走在“房間”與“洞穴”之間的生活。在筆者看來,在現代社會,成為一個百分之百的“避世型”詩人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真正的詩人,無論其詩學觀點是先鋒還是保守,其實都是在選擇一種近似于在“房間”中過著“洞穴”生活的人生。
這本《在山上寫詩 畫畫 蓋房子》是呂德安的隨筆集,以他1994 年到1995 年在山中筑居的日記為主體,其中還夾雜著大量照片、繪畫、詩歌、訪談,以及一些碎片式的雜感。與梭羅的《瓦爾登湖》不同的是,這本隨筆集對山中風景的描述并不多,更多的是詩人在世俗生活中尋找“山”和在“山”中尋找世俗生活的游蕩過程,與詩人的那部長詩《適得其所》之間有著一種“互文”的關系。雖然呂德安在福建老家的這處居所并非“洞穴”,和都市生活相比,卻近似于“洞穴”。不知道呂德安在創作這首《古琴》之時是否有計劃要蓋這棟山里的房子,總之在筆者看來,結合這本書來看,這句“房間里多出一個洞穴的生活”更像是一個小小的暗示。
呂德安的文字有種“透氣感”,充滿了縫隙和可能性。而這種文字中的縫隙并不使其文字流于輕浮,卻相反增加了文字的開放性,使其在流動中隨時保持著與外部空間的平行與滲透。在敘事中,他幾乎不用“做”出來的句子,而只用“流”出來的句子。比如當他寫到在山中留宿時,他寫道:“遠方在發甜。第二天我醒來,覺得自己在群山的搖籃里,變得經得起呼喚了。”一句“遠方在發甜”,就是很典型的“流出來”的文字,僅僅五個字就把山的味覺帶進了一個更大的空間里去。再例如寫到在山中發燒時,“我整個人變得虛浮,好像中了邪似的,將我整個放在另一個身體的重量中。我抵抗,驅趕,留著大汗。”這樣的句子的節奏一看就是一氣呵成,而非精雕細琢而作。這段文字的語速完全是和作者的呼吸節奏,尤其是病中的呼吸節奏結合在一起的。筆者雖然尚未見過呂德安,但是單從這兩句話,就可以想象到這是一個說話緩慢、語調不高的人。一個寫作者,尤其是一個詩人,他的語調其實就是他的風格。當我們被一個寫作者所真正吸引,也往往是因為對方的語調。同理,我相信山也是有“語調”的,山的“語調”反映在它的節奏。單從這本書中的描寫來看,呂德安所居住的這座位于宦溪鄉的山,定不是什么名山大川,可這山的“語調”一定與居住在這里的詩人的語調頗為接近,舒緩,平穩,透氣。
呂德安不是一個像梭羅那樣的“避世主義者”,相反,他更像是一個能在各種生活中間找到微妙的平衡的人,他既能在出世生活中找到“入世”(如接待朋友,出國旅居,等等),同時也能在入世生活中找到“出世”(如寫詩,畫畫,山中蓋房)。在山中蓋房本身就像是在用另一種方式“寫詩”,因為蓋房需要找到“山”的縫隙,就像寫詩需要找到“生命”的縫隙那樣。而這“山”的縫隙,既是“實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實體”上的縫隙益于居住,“精神”上的縫隙則益于“棲息”。呂德安作為一名生活在大山里的藝術家,這種生活的緣分,使他找到棲息的“縫隙”的同時,也找到了山的“縫隙”。
從這本書的設計上看,它的設計師也是一名頗為擅長尋找“縫隙”之人,與普通的隨筆集不同的是,這本書在設計上將照片、繪畫、訪談,以及詩句插入在散文中間,讀起來有著一種近似于一步一景的效果,一本厚達300 頁的書,筆者用一下午讀完并沒有任何審美疲勞。在這個電子書逐漸蠶食掉實體書市場的時代,我想這樣用心的設計,或許能在某種程度上來放緩一下這種蠶食的速度,并讓這本真正好的書不至于淪為數據的奴隸。
LIN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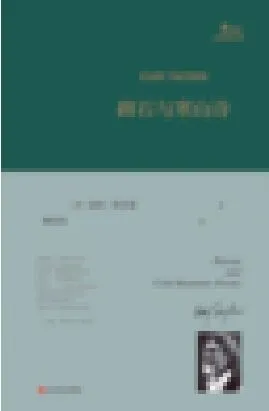
《砌石與寒山詩》加里·斯奈德 著 柳向陽 譯人民文學出版社&99讀書人2018年8月出版
加里·斯奈德是美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詩人之一,他受唐朝詩僧寒山子影響,常年在山中禪修。這本書是斯奈德在五十年代將日文翻譯的寒山詩轉譯到英文,并在美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得寒山成為美國一代文藝愛好者的精神領袖。這本《砌石與寒山詩》由翻譯家柳向陽將加里·斯奈德對寒山的英譯用現代漢語的方式將其“譯回”中文,并配上寒山的原作,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寒山詩歌經過這幾度翻譯之后所呈現出來的新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