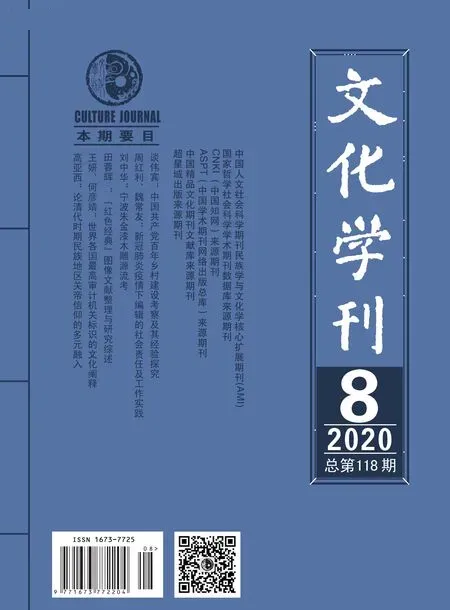對比賞析鄧恩和彭斯的愛情詩
萬海艷
《離別辭:莫悲傷》和《一朵紅紅的玫瑰花》都是深受讀者喜歡的愛情詩,許多文學愛好者、學者皆從不同角度賞析過,但較少有將這兩首詩進行對比研究。本文擬從韻律和修辭角度進行文本細讀,分析這兩首詩通過相似的方式傳達出的不一樣的離別愛意之主題。
約翰·鄧恩于1572年出生在倫敦一個富商之家,接受了良好教育,博覽群書,學識深厚,詩歌創作獨辟蹊徑,善于運用奇特的比喻(conceit)來傳達詩歌主題,是玄學派詩歌的代表人物。鄧恩年輕時個性狂放,生活放蕩不羈。任掌璽大臣秘書時,他愛上了掌璽大臣的外甥女,與之私奔并私自結婚。雖然為此經歷官司,遭受監禁,但夫妻二人感情深厚,婚姻生活相對穩定。《離別辭:莫悲傷》寫作于1611年,在恩主羅伯特先生的懇請下,詩人答應陪同出使法國,此時正值妻子懷孕且身體情況不大好,因而不愿意與之分別。為了寬慰妻子、勸妻子不要悲傷哭泣,臨別作此詩以贈妻子,表達自己無限愛意。
1759年,羅伯特·彭斯出生于蘇格蘭西南部艾爾郡的佃農家庭。雖然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但受母親影響,他熱愛民謠,喜愛收集和整理蘇格蘭民謠,詩歌創作也多以蘇格蘭民謠形式展開。《一朵紅紅的玫瑰花》寫于1794年,是彭斯根據蘇格蘭民謠創作的一首膾炙人口的歌謠體詩歌。詩歌讀起來清新自然,雖為告別詩,但熱情洋溢,感情誠摯[1]。
一、詩歌結構和韻律
兩位詩人雖然出身背景和經歷不盡相同,但兩人在詩歌中對愛的態度都是認真和誠摯的,在離別詩中傾向于采用相似的方式來傳達不同的愛意。兩首愛情小詩皆運用一定的詩歌形式包括章節和音韻來展現主題。兩首詩都采用四行為一小節的章節形式,每一小節的韻式大體為“ABAB”,干凈整潔,體現了詩人在表達愛意上的嚴肅認真。兩首詩主要采用抑揚格作為詩歌節奏,英詩90%采用這種音步,原因在于比較接近口語的節奏[2],這也非常適合愛情主題,向愛人/情人表達愛意時顯得親切自然。

相較于《離別辭:莫悲傷》,《一朵紅紅的玫瑰花》全詩的格律規整很多,基本上為抑揚格四音步和三音步的交替。每一個小節四行為“長短長短”結構,先長后短,讀起來輕快,讓人感受不到分別的悲傷,反而能更加清楚感受到一種熱情洋溢的愛情,讓人心情愉悅,篤信愛情。這種格律形式也是貼近民謠特色,讀起來朗朗上口,展現民歌特有的清新自然和真摯淳樸。
二、詩歌修辭手法
兩首詩皆富有修辭之美,詩人善于運用修辭手段,如用明喻、暗喻、夸張等來表達情意,但二者傳達的情意是有差別的。《離別辭:莫悲傷》這首詩里的愛是相互的,是心心相印的,是純潔高尚的愛,詩人表達愛的方式沉著冷靜。詩人寫此詩的目的是勸慰妻子面臨分別不要不舍,更不要悲傷,只有妻子安定,才會讓在外的“我”心安,感情至誠至深。《一朵紅紅的玫瑰》則是熱戀中的男子向女子傳達的愛慕之意,是濃厚強烈、熱情洋溢的愛,是直敘胸臆式傳達出來的。此詩表達的是男子對女子單方面的愛,女子的美讓人醉心,不忍與之分別。
《離別辭:莫悲傷》開頭第一節便描述了死亡的場面:
As virtuous men pass mildly away,
And whisper to their souls to go,
Whilst some of their sad friends do say
The breath goes now, and some say, No;[5]
詩人用明喻的手法(as的使用),將自己與妻子的分別比作德高之人的靈魂與肉體的分離。德高之人對待死亡處之泰然,悲痛的人們卻更注重肉體的存在。通過明喻這一修辭手法,詩人向妻子強調的是他們的愛更多的是精神之愛,不在乎肉體的暫時別離。即使分開,心也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Walton在鄧恩傳記里曾提及,鄧恩在妻子分娩死胎之時出現了幻覺,他看到妻子頭發散披在肩頭,手里抱著一個死嬰,在他的房間來回兩次。由此可見詩人與妻子之間的精神情感聯系之深。詩人希望勸慰妻子保持內心平靜,大可不必像世俗的愛人分別時慟哭。接下來的五小節,詩人主要用對比手法對比詩人與妻子的精神之愛和月下情人的肉體之愛,進一步強調彼此在經歷了那么多之后的心心相印,即使分別,“我們”的愛不會破裂,而是延展(expansion)。最后三節詩章,詩人則用奇喻(conceit)手法,將自己與妻子的靈魂比作圓規的兩只腳“as stiff twin compasses are two”,妻子的靈魂是固定的那只腳(the fixed foot),“我”則是移動的那只腳(the other far doth roam)。
Thy soul, the fix’d foot, makes no show
To move, but doth, if th’other do.
And though it in the centre sit,
Yet, when the other far doth roam,
It leans, and hearkens after it,
And grows erect, as that comes home.[6]
固定的腳并非真正地固定不變,只要移動的腳動了,它也會在原地跟著轉動。當移動的腳在遙遠的地方漫走時,固定的腳會跟著側身傾聽。一旦移動的腳回到原地,固定的腳就立馬直立。圓規的比喻形象地說明了“我”與妻子的關系——相互依靠,同心同德。丈夫陪同恩主出差法國,遠遠在外,妻子懷孕在家,但每時每刻都心系丈夫,傾聽著丈夫的消息,只有丈夫回到家,她才能心安氣定。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在別人遭遇不幸或情緒低落時,安慰別人就需要同理心,同理心是感受別人所感受的,從別人的角度看問題。該部分就是詩人從妻子的角度,體會妻子的不舍與分別的焦慮,讓妻子知道自己是懂她的,也進一步體現了詩人對妻子的了解和兩人之間強烈的情感維系是不在乎肉體的分別的。最后兩行“thy firmness makes my circle just, and makes me end where I begun”勸慰妻子要淡定,不要擔心、憂心,妻子的“堅定(firmness)”讓“我”在外才能放心、安心。這兩行詩中出現的“圓”(circle)有多重含義。字面意義為圓規畫的圓,與前面兩小節的圓規比喻貫通始終。引申義可以理解為“我”與妻子分別后回家團圓。完成出使任務后,“我”回到妻子身邊,就如同圓規畫完圓之后回到起點。“圓”也可以理解為“我們”之間的愛是圓滿的,分開只會證實“我們”的愛的堅定。此三節詩章奇喻的使用將幾何學的知識運用到詩歌中,不僅體現了詩人的學識與奇思妙想,更展現出了詩人與妻子之間的深厚情感,巧妙地勸慰妻子不要害怕分別。
《一朵紅紅的玫瑰花》第一節也運用了明喻的修辭手法。前兩行將愛人/情人比作六月里剛剛綻放的嬌艷欲滴的紅玫瑰,旨在贊美情人迷人、醉人的外在。六月和剛剛綻放(newly sprung in June)說明情人正值青春年少,充滿活力與熱情。紅紅的玫瑰(a red, red rose),紅色的重復強調愛人/情人肌膚紅潤,艷如玫瑰。后兩行將愛人/情人比作和諧動聽的樂曲(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贊美情人性情溫柔、優雅和甜美。從第一節可以看出,說話者通過贊美情人來說明自己的愛意——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我被你深深地吸引,進而傳達出自己不忍與情人分離的情感。該詩的后三節,詩人主要運用夸張手法,直抒胸臆式地表明自己對愛人/情人的深厚愛意。第一個夸張為“I will luve thee still/till a'the seas gang dry”(愛你愛到海水都干涸),第二個夸張為“and the rocks melt wi'the sun”(愛你愛到石頭都融化),第三個夸張為“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life shall run”(愛你愛到生命終止),承接著的三個夸張實則是熱戀中的男子向情人表達的山盟海誓,情感充沛飽滿、真摯熱烈。最后一個夸張為“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uve, Tho'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即使萬水千山我也會回到你的身邊),作為一首分別詩,詩人在這里點明主旨——你那么美,我是如此愛你,我對你的愛至死不渝,我是如此不舍得離開你,我們的分別只是暫時的,即使前面有千山萬水,我也要回到你的身邊。
三、結語
《離別辭:莫悲傷》和《一朵紅紅的玫瑰花》皆為離別詩,都運用了律體詩的主要特點,用音律和章節形式以及修辭手法來傳達一定的愛意,方式近似,但傳達的情感不盡相同。面對分別,《離別辭:莫悲傷》的基調是悲傷的,妻子依戀丈夫而不忍分別,寫此詩的目的是勸慰妻子,突出強調了“我們”是相濡以沫、心心相印,分離不是愛的破裂而是延展,“我們”的愛是精神維系之愛,情比金堅;《一朵紅紅的玫瑰花》的基調則是明朗的,“我”要與你分別了,你的美讓人陶醉,讓“我”深深著迷,愛你至死不渝,“我”不忍與之分別,即使分別,也只是暫時的,此詩傳達的是男子對女子的深深依戀,突出強調的是“我”對情人的炙熱愛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