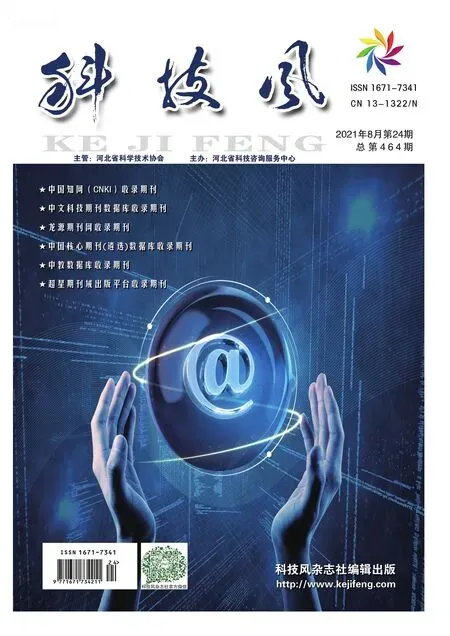淺談自動駕駛與駕駛員被動疲勞
摘 要:自動駕駛被認為是緩解駕駛員駕駛壓力、減少交通事故的一項技術,但就目前所能達到的自動駕駛水平而言,還需要駕駛員承擔監督者的角色,這會使得駕駛員更容易進入被動疲勞的狀態。本文首先介紹了被動疲勞的概念和產生機制,然后介紹了國內外相關研究現狀,最后總結并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自動駕駛;被動疲勞;多巴胺
駕駛疲勞一直是安全駕駛領域研究的熱點,約20%的交通事故與駕駛疲勞相關,而自動駕駛被視為緩解駕駛員駕駛壓力、減少交通事故的一項技術。在車輛自動駕駛時,駕駛員似乎可以完全脫離駕駛任務進行其他活動,但這么做也降低了駕駛安全性。2019年12月,一輛搭載特斯拉Autopilot的車輛連續撞到警車和路邊車輛,而事發時駕駛員正在照顧后座的狗。現階段的自動駕駛并非完全安全,因此按照目前的法規要求,駕駛員在使用自動駕駛功能時仍然需要監管車輛,但駕駛員在執行監管任務時仍然可能進入駕駛疲勞狀態。
一、駕駛員被動疲勞的定義及產生機制
目前學界并未對疲勞的定義形成統一觀點,因此存在多種研究角度。Desmond和Hancock[1]在2001年提出了主動疲勞和被動疲勞概念,主動疲勞是由于持續的高負荷工作產生的,例如駕駛員在手動駕駛模式的繁忙市區場景需要頻繁的控制方向盤、油門和制動踏板,被動疲勞則是持續的低負荷工作、缺乏刺激和激勵產生的,在進行自動駕駛監管任務時,駕駛員可能會因為長時間單調乏味的監管任務而產生被動疲勞。
被動疲勞的產生機制可以通過多巴胺疲勞產生學說解釋。多巴胺是第一個被驗證為在中樞性疲勞起作用的神經遞質,它和人的動機相關。當個體在執行一項任務時,大腦會先對任務進行評估,得出目標任務的回報獎勵和付出努力的比例關系,若評估結果為高努力低回報,多巴胺活性就會降低,大腦就會產生厭倦感而進入疲勞狀態。反之,多巴胺活性就會增強,任務動機增強并且疲勞感減輕或消失。在自動駕駛監管條件下,駕駛員需要時刻準備從系統手中接管車輛,這要求駕駛員付出一定水平的努力去保持注意力,若駕駛員長時間付出監管努力而沒有得到相應回報(自動駕駛運行正常,不需要駕駛員進行接管),就容易導致多巴胺活性降低,駕駛員進入被動疲勞狀態。
二、自動駕駛場景下的駕駛員被動疲勞研究現狀
(一)自動駕駛監管條件下會導致被動疲勞發生
目前國外學者大部分都基于模擬駕駛器對自動駕駛場景下的疲勞發展進行研究。大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在L3級別的自動駕駛下,單調的監管工作強化了被動疲勞,這使得在自動駕駛時,駕駛員的疲勞發展速度相比手動駕駛時更加迅速,根據Vogelpohl等人[2]的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駕駛員在使用自動駕駛15-35min內就會出現疲勞跡象,而且現象更為極端,駕駛員出現直接昏睡的概率更高,這一點在Feldhütter等人[3]的研究中得到了驗證,在他們的實驗中,25%的被試在使用自動駕駛系統15min后就出現了明顯的疲勞跡象。
(二)被動疲勞會對自動駕駛的安全性造成負面影響
目前L3級別的自動駕駛仍然需要駕駛員在合適的時機接管車輛,這要求駕駛員對運行的自動駕駛車輛進行監管,而被動疲勞的產生會降低駕駛員的監管績效,例如駕駛員警覺性的降低、注意力無法集中,駕駛員的情景意識(Situation Awareness,SA)也會隨之下降,這使得駕駛員可能無法及時地對交通情況做出正確判斷,駕駛者的反應時間也會變慢。被動疲勞也會對駕駛員的接管績效產生影響,Feldhütter等人發現發生被動疲勞的駕駛員在面臨接管情況時會具有更大的負擔和壓力,同時在接管之后的駕駛安全性下降,Saxby等人[4]通過一小時的模擬駕駛實驗誘導不同類型的駕駛疲勞產生,發生被動疲勞的駕駛員在接管車輛后,頭30s內車輛的橫向位置標準差(SD of Lateral Position,SDLP)顯著大于其他兩種駕駛疲勞狀態時(主動疲勞和控制組疲勞),表明駕駛員在接管車輛后對于車輛橫向位置的控制能力下降,而且發生被動疲勞的駕駛員在接管車輛后應對緊急事件的反應時間上升了(被動疲勞組>控制組>主動疲勞組),同時增加了車輛發生危險碰撞的概率(被動疲勞組>控制組>主動疲勞組)。
(三)被動疲勞的生理指標表現具有特殊性
被動疲勞的特殊成因會導致個體的一些生理表現與傳統手動駕駛疲勞不同。在以往的駕駛疲勞檢測研究中,常使用腦電EEG、心電ECG和眼動指標作為駕駛疲勞的檢測生理指標,而根據Kyle Anthony Bernhardt[5]的研究,被動疲勞的EEG參與度更低,Theta波和Alpha波比值最初升高且穩定。在竇廣波[6]的研究中,被動疲勞的心率變異性表現更加顯著,多個指標例如SDNN,rMSSD,LF,VLF都與主動疲勞和控制組疲勞有顯著差異,同樣在其研究中,被動疲勞組的瞳孔直徑展現出更低的水平。這些生理指標的差異將會影響駕駛疲勞檢測技術在自動駕駛車輛中的應用。
三、總結和建議
自動駕駛是人類100年前就開始的夢想,如今隨著技術進步,自動駕駛已不再是一句空話。但就目前看來,自動駕駛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有條件自動駕駛確實能夠一定程度上降低駕駛員付出的生理和心理努力,但是這帶來了新的問題和挑戰。自動駕駛使駕駛員的角色從參與者轉變為監管者,使得被動疲勞更易發生,因此駕駛員在監管過程中更易出現嗜睡等脫離駕駛的現象,同時在接管車輛后更易造成安全危害,例如應對危險事件的反應能力下降。因此,在自動駕駛時繼續監測駕駛員的狀態是十分有必要的,系統應在接管之前判斷駕駛員是否做好了接管準備,并相應地調整好轉向、制動以及其他安全支持保證接管過程的安全進行。但是在應用疲勞檢測技術時,應考慮被動疲勞的生理表現特殊性,針對性測量疲勞閾值,提高被動疲勞判別的準確率。
從被動疲勞的產生機制上看,低工作負荷是主要誘因,因此在使用自動駕駛時稍微增加一些駕駛次任務也許可以減緩駕駛員被動疲勞的發展,例如使用更加互動的人機交互,運用一些瑣事詢問來保持駕駛員的警覺性,或者使監管行為更加游戲化,激發駕駛員參與監管的動機。總之,技術開發商在研發自動駕駛時應該更加謹慎,從用戶的角度考量設計以減少被動疲勞的發生。
參考文獻:
[1]Hancock P A,Desmond P A.Active and Passive Fatigue States[M].Hancock P A,Desmond P A,eds.Stress,Workload,and Fatigue.London:LEA Publishers,2001:455-465.
[2]Vogelpohl T,Kühn M,Hummel T,Vollrath M.Asleep at the automated wheel-Sleepiness and fatigue during highly automated driving[J].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2019,126:70-84.
[3]Feldhütter A,Hecht T,Kalb L,Bengler K.Effect of prolonged periods of conditionally automated driv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tigue:with and without non-driving-related activities[J].Cognition Technology and Work,2019,1(21):33-40.
[4]Saxby D J,Matthews G,Warm J S,et al.Active and passive fatigue in simulated driving:Discriminating styles of workload regulation and their safety impact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Applied,2013,19(4):287-300.
[5]Kyle Anthony Bernhardt.Differentiating Active And Passive Fatigue States With The Use Of Electroencephalography[D].Grand Forks: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2018.
[6]竇廣波.駕駛員被動疲勞的行為分析與測量[D].大連:遼寧師范大學,2017.
作者簡介:蘭成輝(1994—),男,福建霞浦人,碩士,研究方向:駕駛疲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