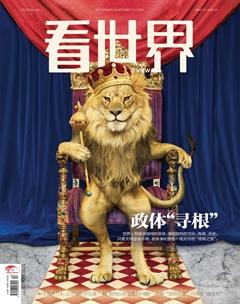《花木蘭》:已盡力但不完美
塵雪

本篇圖:《花木蘭》劇照
在推遲了大半年后,迪斯尼真人版電影《花木蘭》終于在美國時間9月4日面世。9月11日,中國大陸影院也上映了該片。
迪斯尼真人版《花木蘭》的故事講述了1300年前,年輕女子花木蘭為了拯救年邁的父親,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在從中原到西北的廣袤征程中,她從緊張的訓練和戰爭中存活下來,在同營好友洪輝和導師董將軍的鼓舞下,以及女巫仙娘的激發下,發現藏在自己內心的戰士,并且最終從外族侵略者手中救回了皇帝和她的祖國。最后,木蘭選擇回家看望父母和妹妹。她是否會接受皇帝的任命?故事的結局是開放性的。
2020年的《花木蘭》通過一個父親的角度講述花木蘭的故事。這估計是最貼近原著精髓的視角了,因為花木蘭是“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代名詞。她跟父親的感情非常要好。
在西方人眼中的東方文化與時尚,是絢爛華麗的皇家旗袍,并沒有鮮活的中國當地時尚與文化。
沒有了1998年迪尼斯動畫版中,花家祖先派出心地善良的木須從旁保護木蘭,真人版《花木蘭》賦予花木蘭強大的“氣”和軍事兵法謀略,讓傳奇自圓其說。此外,該片重視呈現中國功夫和軍事搏斗,木蘭的人物價值觀和情感內核是“忠勇真”+“孝”。
西方如何呈現東方?
迪斯尼真人版的導演是妮基·卡羅。她的電影作品曾于1994年入圍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
卡羅拍攝的第一部好萊塢電影《決不讓步/北國風云》(2005年),由查理茲·塞隆主演,根據1988年的真實事件改編—那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樁起訴成功的性騷擾官司。該片曾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演員和最佳女配角獎的爭斗,并獲得金球獎提名。卡羅頗受好評的電影《鯨騎士》,講述新西蘭古老部落毛利族的酋長孫女的故事。卡羅拍攝的幾個故事都是女性題材。由這位新人導演來拍,似乎也比較合理。
真人版《花木蘭》開篇,木蘭在家人要求下見媒婆,媒婆點出中國古代女性的美德是安靜禮貌、沉靜優雅,是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而非武功打斗、保家衛國。而那些不推崇傳統美德的女性形象,被視為“女巫”。在古代歐美,那些前資本主義時代想要進入男性主宰的勞動市場,或是擁有杰出技能的、不合主流社會規范的女性,被視為“女巫”,她們要么被淹死或燒死,要么像仙娘那樣被拋棄、流放。
真人版《花木蘭》的西方式改編還包括,將木蘭的“傳奇性”歸結于其超強大的“氣”,說她是鳳凰化身;鞏俐飾演的仙娘,擁有幻術(西方稱為“黑魔法”),則是老鷹的化身。仙娘擁有比男性更強的能力而不被承認,繼而走上“邪路”—正是這一人物形象,讓很多中國觀眾感到牽強。

《花木蘭》導演妮基·卡羅
一位豆瓣網友說:“鞏俐戰斗力和幻術這么強悍,就因為大家不認可她,她就給柔然人賣命?理由何在?那柔然統領就是被她一刀秒的水平,她為何要卑躬屈膝呢?”“鞏俐也是多此一舉,既然會巫術這么牛逼,干脆變成一個內侍或妃子,趁皇帝不注意把他干掉,然后直接自己做皇帝不行嗎?”

顯然,仙娘這個角色的人物塑造還需要更加合情合理化。殺人如麻的她,居然被花木蘭一句話“女性也能領導軍隊,我們這樣的人也有一席之地”就勸回了頭,簡直讓人莫名其妙。“前一秒還為獲得人們的認可不惜忍辱負重,下一秒突然就不想活了,為保護木蘭而獻身?”正因為仙娘的轉變塑造得不夠深入,以至于觀眾看到她死的那一幕,心中毫無波瀾,有些可惜。
此外,皇帝被仙娘假扮的丞相蒙騙,單人前往一處類似建筑工地的地方跟柔然統領約戰,這也是西方的決斗文化。中國觀眾會覺得皇帝傻,區區一國君主,怎么隨隨便便單人去決斗?他最后被柔然統領五花大綁,還被后者用刀磨出來的火花威脅,即將命喪火爐,這個場景,因為中西文化差異,令一些觀眾感到荒謬可笑,缺乏常理邏輯。
這是“美國女兵”花木蘭,根本就不是中華巾幗英雄。
對中國文化的錯位解讀,讓中文世界的網友驚呼:外國人對中國故事的理解真是莫名其妙!這些讓我想起一部講述西方如何在紐約大都會藝術館呈現中國時尚的紀錄片《鏡花水月》。在西方人眼中的東方文化與時尚,是絢爛華麗的皇家旗袍,并沒有鮮活的中國當地時尚與文化。它只呈現了鏡花水月般的窺探,讓人感嘆:西方人能否真正理解中國服飾與時尚背后的文化和價值觀?
是勇敢、風趣而聰明的“美國女兵”?
顯然,迪斯尼真人版的優點,在于武術編排與好萊塢特效呈現。尤其是兩軍對峙時雪崩那場戲,以及木蘭見媒婆防止茶杯摔落的那段動作設計,非常出色。

創作者還非常注重細節和顏色,木蘭居住的福建土樓叫延福坊。木蘭見媒婆前梳妝打扮的那場戲,展現中國服飾和化妝術,滑稽意味濃厚。演員們沒有戲劇化地夸張表演,情緒克制,這很難得。劉亦菲曾在接受西方媒體采訪時說,軍隊不同士兵陣列的服裝顏色各異,木蘭的紅色戰袍在熒幕上呈現得很好看,真人版擅長用顏色講述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迪斯尼大膽起用西方觀眾眼中的新人—劉亦菲,以及非大牌導演妮基·卡羅和編劇勞倫·希內克。
遺憾的是,觀眾并沒能看到木蘭從“一個女孩成長為一個戰士,繼而從一個戰士成長為一個領袖,再從一個領袖成長為一個傳奇”的過程。她自我身份認同的轉變也有些潦草,難以跟觀眾產生共情。
此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花木蘭是迫不得已才替父出征,并非迪斯尼真人版電影中,那么爽快地去參軍。木蘭似乎并不知道戰爭和男性世界的殘酷性,或許是因為她擁有強大的“氣”吧。片中木蘭推崇的理想女性“勇敢、風趣而聰明,但不一定要漂亮”,這也很符合西方男性審美。有觀眾直接說,這是“美國女兵”花木蘭,根本就不是中華巾幗英雄。
此外,中西文化符碼的翻譯轉換,也顯得不夠流暢自然。片中,成語“四兩撥千斤”被翻譯成“4盎司可以移動1000磅”,讓人捧腹大笑。還有皇帝賜予的玉佩上碩大一個“孝”字,與劍上巨丑無比的“忠勇真”,都未能呈現中國漢字書法之美。片中出現的強行融合中國元素,彌漫著熟悉的左宗棠雞風味。例如,“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竟然直接就拍了兩只兔子在草地上跑的畫面,再配上木蘭的臺詞:“我騎著馬看到兩只兔子并排奔跑,我想一個應該是公的,一個應該是母的,但是你知道嗎?你不能真的分辨得出來,因為它跑得非常快。”這樣的詮釋,真的非常簡單粗暴。
對于美國女性來說,花木蘭的榜樣作用或許沒有那么強烈。她們的女性榜樣,可能是在男權社會里無畏、冷靜的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或是前第一夫人奧巴馬·米歇爾,或是虛構的神奇女俠。再加上,西方視角解讀中國文化,本身就非常困難,諸多弊病只待時間與更多具有跨文化敘事能力的創作者們來克服。不管怎樣,這部電影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