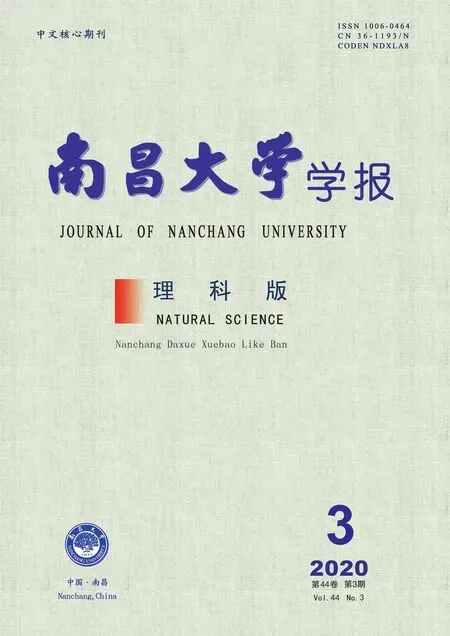一類高、中低技術產業企業的競合博弈策略
盧美華,肖莉娜
(江西科技學院理學部,江西 南昌 330022)
以博弈理論為基本工具,產業組織理論(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中技術競爭的形態受到廣泛的研究[1];即使是產業形態的巨大差異,理論抽象出一些技術博弈模型基本上揭示了現實中的博弈競爭形態[2-3]。其中,嵌入在整個產業生態鏈中,特別是博弈實踐中,具有各種技術層次的企業,不同企業參與的博弈形態和采用的競爭策略大相徑庭[4-5]。而按照企業的技術層次劃分可以刻畫一大類現實中的企業競爭形態,豐富市場中企業競爭和博弈的一些結論,特別是這代表了一類引領和跟從性的產業競爭關系[6-7]。
高新技術企業和中低技術企業不僅簡單代表技術水平,事實上,由于企業集群的特性,還代表了區域競爭力的差異;特別是通過業務外包,不同技術層次企業必然組織在同一產業鏈條上。國內文獻中,高新技術競爭受到廣泛的研究,但對中低技術競爭的研究卻十分匱乏。國際上卻早在“歐洲中低技術產業政策與創新”(PILOT)項目中,就發現中低技術企業的新技術實現能力是區域創新源泉[8]。另外中低技術企業博弈時在主從關系和協調關系上具有十分鮮明的特征,為此,本文從博弈主從關系上刻畫一類中低技術產業中技術競爭的博弈策略。
1 基本模型設置
OECD國家在《奧斯陸手冊》最先按研發投入劃分了企業技術層次,如表1。
給出了實踐中企業技術層次識別,張可、左媛[8]發現中低技術產業中創新主要在于技術培訓(STT)和新設配的獲取和應用(FEQ),這實證了中低技術產業創新中的從屬位置。另外,營銷學對搜尋品、經驗品和信任品,及對非檸檬市場的研究表明預期市場規模、品牌流行性都能提升保留價格,而性能提升更能保留價格。
為此模型化這一技術市場的競爭形態,設各技術層次企業參與同一產品市場競爭,S為預期市場規模,Q為現實銷售數量,按反需求函數形式,確定P(Q,S)=P(Q)+H(S)為保留價格。這里P(Q)代表正常市場消費數量Q確定的消費者保留價格。但研發投入導致對產品質量提升或者功能擴展能提升消費者的保留價格,并且也能擴大產品市場份額,表現為預示市場規模S的提升上,并且保留價格和預期市場規模匹配;為此,設H(S)為預期市場規模下提高的保留價格。


2 基本結論
通過計算并比較一些均衡特征,可以揭示不同技術層次在市場上的博弈策略選擇。區分第一種情況,高技術企業研發技術采取市場公開,從而所有進入市場的企業具有相同的生產成本,但高技術研發企業具有市場進入的先發優勢;第二種情況,高技術企業研發技術收費許可,仍然具有市場進入的先發優勢。


由此均衡特征為
由此,顯然可得如下命題。
命題1技術層次差異企業競爭均衡下,高技術企業預期規模下一半市場,中低技術企業均分一半預期規模市場。
命題2存在最優預期規模實現的均衡,并且最優規模是穩定的。實現最優預期規模,中低技術企業仍處于Cournot均衡。
證明首先,由均衡特征中包含預期規模S為參數,均衡特征是預期規模的狀態相依的。顯然,即使實現最優預期規模,中低技術企業仍處于Cournot均衡。
另外,設最優預期規模為S*,則最優規模S*滿足系統方程S*=Q(S*),且系統方程決定穩定的狀態就是最優規模。如下依據S、H(S)求解方程S*=Q(S*)。
命題2需要穩定型S*=Q(S*)。圖1中,S=Q(S)雖然以S1、S2、S3為不動點,當然此三個不動點因H(S)之性狀可以退化為一個、兩個不動點。由曲線Q=Q(S)必然穿越曲線Q=S的方式可知必然存在穩定型不動點。圖1中,至少S2是穩定型不動點。從而命題2得證。
命題3中低技術企業具有參與市場實現預期規模的動力。即使市場成本上高技術企業和中低技術企業一致,特定情形下高技術企業仍然具有實施技術開發,具有擴大中低技術企業數量實現預期市場規模動力。

由S*同時滿足
(式1)
(式2)
(式3)。
在第2種情況下,仍然是在技術博弈下而非生產博弈下,標準化高技術企業生產成本為0,而高技術研發企業采取技術收費許可,中低技術企業或者承受舊技術的生產成本,或者承受新技術許可成本。為方便,設中低技術企業接受技術收費許可,從而也和高技術企業的生產成本為0一致。考慮技術收費的多種形式,邊際產品收費τ,或者一次性技術許可總費用λ;事實上,這兩個許可費用可以合并為費用向量,(τ,λ)=(τ,0)即為邊際產品費用,而(τ,λ)=(0,λ)即為一次性技術許可總費用。
命題4在技術邊際效應強的市場下,高技術的研發企業能收取一次性費用時,特定情形下高技術研發企業有動力擴大中低技術企業數量。


命題5在技術邊際效應強的市場下,高技術的研發企業收取邊際產品費用時,特定情形下高技術研發企業有動力擴大中低技術企業數量。
證明考慮固定性邊際產品費用,即τ(Qi)為常數τ。
高技術和中低技術企業分別最大化如下利潤函數:
Ll=qlP(Q,S)+k(Q-ql)
計算均衡條件得:ql(S)=[A+H(S)-2τ]/2(k+1)
qf(S)=[A+H(S)-2τ]/2(k+1)
Q(S)=[(A+H(S))(2k+1)-2kτ]/2(k+1)
P(S)=[A+H(S)+2kτ]/2(k+1)
從而最大均衡利潤分別為:
Ll=(A+H(S))2/4-k(A+H(S)-2τ)2
Lf=[(A+H(S)-2τ)/2(k+1)]2,i=1,2,3,…,k
為后續計算方便,設H(S)=θS。并設S*=Q(S*)自行實現,則:
Q(S*)=[(A(2k+1)-2kτ]/[2(k+1)-θ(2k+1)]
為保持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穩定性,至少需要θ<2(k+1)/(2k+1),在此情形下,可計算全部均衡特征如下:
ql(S*)=[(k+1)A-θτk]/[2(k+1)-θ(2k+1)]
qf(S*)=[A-(2-θ)τ]/[2(k+1)-θ(2k+1)]
P(S*)=[A+2kτ(1-θ)]/[2(k+1)-θ(2k+1)]
Ll(S*)=ql(S*)P(S*)+kτqf(S*)
Lf(S*)=ql(S*)[P(S*)-τ]
再計算邊際費率效應:
顯然,均衡產業規模隨邊際許可費用的上升而下降。并且一般情況下要求θ <1,而θ<1也能保證dP(S*)/dτ>0,均衡價格隨邊際許可費用的上升而上升。
當然現實均衡價格并沒有隨邊際許可費用的上升固定方向變化,而是依邊際收費率而定。當現實中均衡價格隨邊際許可費用下降時,要求dP(S*)/dτ<0,這等價于θ>1(這里當然仍然有θ<2(k+1)/(2k+1)),這里發生特異情況,一般可能是市場上還沒有跟從性企業才能出現。
考慮高技術企業技術收費下最大化利潤,一階條件為0如下:
可得高技術企業的最優邊際許可收費為:

3 案例分析和結論
在早期ICT產業中的一些企業采用技術封鎖博弈策略卻導致市場失敗,形成技術過時的局面。典型例子是1987年IBM公司設計了一款新型微信道結構,但該公司采用了專利壁壘行為,限制了基于該微信道結構兼容技術的發展,幾乎導致該微信道結構的失敗。兩年后,該公司改變了博弈策略,免費了該技術專利才形成了良好的產業配套生態,否則就形成技術過時的局面。另外,在Yahoo郵箱收費時,Gmail郵箱免費策略也具有本文競爭策略的影子;免費經濟學中都有廣泛的現實案例,都應證著本文各個命題,在各種場合都存在自主邀請和主動擴大競爭性行為,以做大整個預期市場規模并實現市場規模。當然,這些案例與典型的智豬博弈不相同,該博弈特征是以“后發優勢”為基礎形成“搭便車”行為;而本文的博弈策略主要是“邀請競爭”,以發揮市場規模效應。
當集中到中低技術產業企業的博弈策略,以我國的中低端手機芯片產業為例[9],美國高通、因特爾和我國臺灣聯發科為高技術企業,而我國大陸企業展迅通信、華為海思和中芯國際為中低技術企業;美國高通公司在我國早期“市場換技術”的思路下,其預期市場規模十分龐大,高通早期采用歧視性高昂專利收費,并擴大市場規模,推動各類芯片企業、手機配件企業、手機組裝企業提升規模,我國早期的“山寨手機、野手機、黑手機或高仿手機”的繁榮局面就是一種邀請性競爭和高技術企業主動擴大競爭的局面。近期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也受到廣泛關注,華為是科技戰的一個焦點,一些技術專家對科技戰中的華為進行了準確的分析[10]。華為公司在5G技術上是高技術企業,最近華為準備以一次性專利收費交易向全世界轉讓5G核心技術,即購買方一次性買斷永久使用相關技術和知識產權的權利,即使當前愛立信、諾基亞在內的國際通信巨頭的5G技術跟華為有很大差距,美國的5G技術更不給力。華為策略體現了“華為利益分享”,事實上技術實力的不均衡已經影響到全球5G市場的興旺,這并不符合華為的利益。在藍牙技術華為也是高技術企業,但華為并沒有用自己超級藍牙技術單挑傳統藍牙利益聯盟體。華為在操作系統技術上應該還是低技術性企業,從而華為的鴻蒙操作系統的重點在于應用生態建設,也需要提升并實現預示市場規模。
本文收集權威文獻建構不同技術層次企業博弈邏輯起點[1-14],并收集現實案例支撐研究結論;諸多案例顯示,當前市場和產業業態快速變異,技術提升、技術融合、應用場景的擴展都要求企業在參與市場是采用靈活的博弈策略。高技術企業不必完全殲滅中低技術企業,中低技術企業也不應單純采用價格競爭戰略,所有企業都應該擯棄陳舊的博弈策略,貫徹合作競爭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