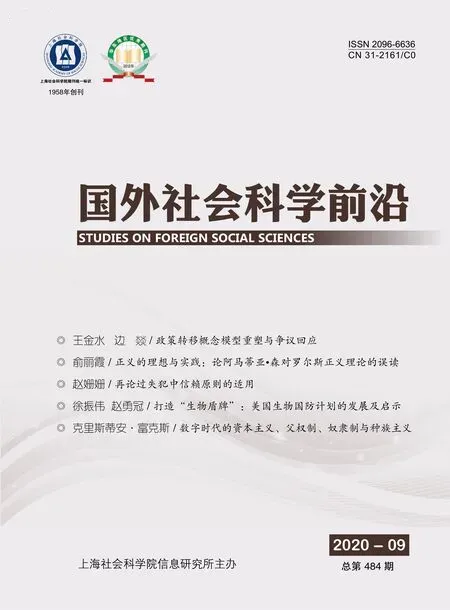政策轉移概念模型重塑與爭議回應
——基于多案例的質性研究分析 *
王金水 邊 燚
內容提要 | 政策轉移相關文獻梳理的結果表明,目前學界關于此研究存在四個爭議性問題,即:政策轉移框架在現階段是否需要更新及其各要素是否有重要性程度的排序、政策轉移理論主體在全球化視野下是否有變更、政策轉移理論是不是一個完善的理性過程以及政策轉移理論是否有必要建立嚴格的理論界限。針對這四個爭議性問題,本文通過質性研究軟件NVIVO對92個政策轉移案例重新編碼并繪制出政策轉移概念模型,在分析各編碼要素的基礎上,對爭議性問題作出回應:“軟轉移”與“網絡”成為政策轉移新趨勢;政府主體地位在全球化視野下未動搖;理性主義精神指導政策轉移實踐;政策轉移沒有必要建立嚴格的理論界限。在國際政策網絡中,政策轉移的質性研究,能夠拓寬我國政策學習以及政策傳播的思維空間,因而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應采取積極的政策學習態度。具體而言,作為政策轉移網絡中的互動主體,政府必須能夠掌握政策轉移的主動權,協調社會公眾、專家與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推動政策學習的理性轉移。
一、政策轉移研究的衍化及其爭議
政策轉移是在全球傳播的支持框架內,在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背景下誕生的。如歐文·E. 休斯(Owen E.Hughes)所說,“在過去的20年中,由于西方各國政府致力于回應技術變革、全球化和國際競爭的挑戰,其公共部門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革……這一時期的變革代表了一種新典范的變遷,即由支配20世紀大部分時期的傳統公共行政模式轉變為‘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的模式。與政府有關的官僚制理論正在被各種經濟理論與市場規則所取代。”1[澳]歐文·E. 休斯:《公共管理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3~24頁。新公共管理理論是相對于傳統行政管理的一種新的管理范式,其強調政府管理中的“3E”,即“經濟、效益、效率”,重視績效評估、市場原則,將政府管理競爭化、市場化。盡管新公共管理運動后來面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性”“經濟學帝國主義”“新泰勒主義”的批判和“新公共服務理論”“網絡治理理論”等新范式的挑戰,受到不小的沖擊,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引起了一場全球性的治理革命,這既是全球化、網絡化、市場化所帶來的必然改變,又是政府在治理革命中尋求自我革新與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新公共管理時代”,信息網絡將國家間的物理距離無限縮短,政府面對治理挑戰與國家競爭壓力時會轉而尋求其他國家的治理經驗,政策轉移相關理論由此產生。
政策轉移理論是從比較政治學中逐漸發展而來的。1David P. Dolowitz and D. Marsh, 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 A Review of the P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2010, pp. 343-357.政策轉移理論作為比較政策研究的發展性研究理論,其意味著比較政治研究向比較政策研究的理論轉向。20世紀50—60年代是比較政治學發展的繁榮時期,該時期也是行為主義取代以往制度主義和歷史主義成為主導范式的時期,研究者們將動態的政治決策過程與政府活動產出即政策問題納入比較研究的范疇之中。2張親培、張海柱:《比較公共政策研究:回顧與展望》,《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年第6期。比較政治研究向比較政策研究轉向既是行為主義范式對政治學影響的結果,也是政治學為應對國家發展與全球化變革增加其適應性的必然產物。為了考察政策在時間或空間上的傳播方式,描述各國相似政策的傳播順序,于是就有了一些疑問:(1)這一政策是如何實施的?(2)這一政策傳播過程是否可以歸納為政策研究的一般框架之中?因為這些疑問,政策擴散概念由此產生,而后與政策轉移有關的一系列理論才得以成為研究焦點。
政策轉移并非單一理論的闡述,而是大衛·多洛維茨(David P. Dolowitz)和戴維·馬什(David Marsh)在總結歸納多個政策傳播相關理論后產生的,將政策趨同、政策擴散等相關概念進行整合而形成的一般通用框架。3Evans M, Understanding Policy Transfer: A Multiple Level, Multipl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 77, 2002, pp. 361-385.他們歸納了包括“教訓吸取”“政策擴散”“政策趨同”等多個龐大而分散的理論群體,最后歸納為“政策轉移”這一概念,并建立了系統的理論框架。產生于比較政策研究的政策傳播理論并不關注轉移政策的過程,為了克服政策傳播研究的弱點,政策擴散研究應運而生。4David P. Dolowitz and D. Marsh, 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 A Review of the P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2010, pp. 343-357.政策擴散被定義為“社會系統成員之間通過某些渠道進行傳播創新的過程”,5Berry F. S. and Berry W. D.,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Models in Policy Research,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Routledge, vol. 2, 2018, pp. 263-308.更側重于對轉移條件及過程的關注而非政策轉移內容的研究。
而與政策擴散幾乎同時誕生的政策趨同,其概念被定義為“社會變得更加相似的趨勢,在結構、過程和表現上的相似性的過程”。6Colin J. Bennett, What Is Policy Convergence and What Causes I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1, vol. 2, p. 215.政策趨同理論認為,隨著社會越來越多地進行工業基礎設施建設,某些決定性過程開始運作,這些過程隨著時間推移在同一模式中形成相似的社會結構、政治過程和公共政策。由于其內容更龐雜,也受到了一些批判,如有人認為趨同研究并不是一個連貫的理論立場。還有人認為,它反映了各種理論和認識論主張,是一個包含大量基本描述性或比較性證據的“多形式的動物園”,有豐富的寶貴見解,但理論建構有限。7Colin J. Bennett, What Is Policy Convergence and What Causes I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1, vol. 2, p. 215.所以到了20世紀80年代,一項重要的批評性評論認為:“這個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它沒有揭示新政策的內容。它的魅力在于過程(process),而不是實質(substance)。”由于這種感知需要回答擴散研究忽視的問題,學者們開始轉向吸取教訓和政策轉移的研究。
“吸取教訓”非常類似于傳統的政策制定理性說明,強調政策決策是通過公共機構或其代理人的結構化干預來追求有價值的目標。8M. Hill, 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Modern State, Third edition, London: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pp. 23-24.其具有將理性政策制定與明顯非理性決策形式區分開來的潛力,深化了理性決策的概念。1James O and Lodge M., The Limitations of 'Policy Transfer' and 'Lesson Drawing'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3, vol. 1, pp. 179-193.如果說“吸取教訓”是從政府的理性決策來探討政策的傳播,政策轉移則試圖通過外部影響和不同國家政策的趨同來包含有關國內政策變化的概念。
道洛維茨和馬什將政策轉移界定為:“在一個時間或地點存在的政策、行政管理安排或機構被用于在另一個時間或地點來發展有關政策的知識、行政管理安排和機構的過程。”2David P. Dolowitz and D. Marsh, 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 A Review of the P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2010, pp. 343-357.這一概念為學界所公認。道洛維茨和馬什還創立了“道—馬模型”,內容包括“為什么轉移”“誰介入了轉移”“轉移了什么”“從哪里轉移”“轉移程度”“轉移限制”“如何證明政策轉移”“為什么失敗”等八個分析因素。這八個因素作為政策轉移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被不斷探討、補充,理論與爭論也讓政策轉移理論研究轉向概念的爭論與框架的完善之中。而目前政策轉移研究開始重點向“軟轉移”與網絡治理方向偏斜。關于政策轉移中“軟轉移”與網絡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依托某一實例進行研究,在全球化、網絡化視閾下擴展政策轉移理論研究思路與范疇,為政策轉移理論突破“方法論民族主義”與“理性行為假設”開拓了解釋路徑。
與此同時,政策流動被研究者認為是一種政治化的、充滿權力的、社會建構的過程,3J. Peck and N. Theodore, Mobilizing Policy: Models,Methods and Mutations, Geoforum, vol. 2, 2010, pp. 169-174.可能發生在政府的不同層級,因為思想和技術的運動重塑了政策轉移之間的權力關系,破壞了這些決策網絡之間的邊界。政策流動的研究更傾向于探索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中、在開放的網絡政治環境中政策的變異過程。政策行為者的定義也更加寬泛,包括非政府組織、顧問、媒體、規劃者、倡導者和鄰里協會等。尤金·麥卡恩(Eugene McCann)和凱文·沃德(Kevin Ward)特別著眼于城市政策的流動性,他們建議關注城市政策是如何由與其他地方的聯系和所處的政治競爭共同構成的。4Mccann E. and Ward K., Relationality/Territoriality: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Cities in the World, Geoforum, vol.41, 2010, pp. 75-184.同樣,規劃學者也主張采用關鍵方法來更好地理解日益增長的跨國規劃思想流動。5Patsy Healey, Circuits of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Planning Ideas and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37, no. 5, 2013, pp.1510-1526.與其說麥卡恩與沃德重新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不如說是補充了政策轉移的概念,使得先前政策轉移研究中缺失的關于“價值重構、制度重構”的部分完整起來,更加側重對于“軟轉移”部分的研究。
政策轉移既代表了比較公共政策研究的發展成果,也代表了全球化視閾下全球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其更加注重對于國內與國際兩個場域分歧的分析,對全球化的一種回應是提高政策學習的能力,使決策者能夠反對主權的衰退和因為全球化帶來的政策本土化缺失。6David Dolowitz, Transfer and Learning: One Coin Two Elements, Novos Estudos Cebrap, vol. 2, 2017, pp. 35-56.當然,政策轉移理論并非完美無缺,政策轉移研究的歷史盡管只有短短幾十年,但是關于政策轉移理論的批評卻從未停止。首先是關于政策轉移工具的非嚴謹性。現有的政策框架已經無法滿足政策轉移的要求,學者們不斷認識到建立一個政策轉移工具是難度極大的并且無法達到完美境地。7H. Wolman and E. Page, Policy Transfer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n Information-theory Approach, Governance, vol.4, 2010, pp. 577-501.第二個爭議是有學者認為政策轉移理論與其他理論并沒有明顯的界限。1James O. and Lodge M., The Limitations of 'Policy Transfer' and 'Lesson Drawing'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2, 2003, pp. 179-193.第三個批判是政策轉移是在理性的假設前提下,而政策制定過程與政策制定者在制定過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也會影響政策轉移進程。2James O. and Lodge M., The Limitations of 'Policy Transfer' and 'Lesson Drawing'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2, 2003, pp. 179-193.第四,有學者批判政策轉移理論需要在全球化、網絡化背景下廓清政策轉移主體,避免“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傾向。3H. Wolman and E. Page, Policy Transfer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n Information-theory Approach, Governance, vol.4, 2010, pp. 577-501.通過這四個對政策轉移理論的批判,可以看出政策轉移理論在發展過程中面臨一些爭議,即:(1)政策轉移框架在現階段是否需要更新,各要素是否有重要性程度的排序?(2)政策轉移理論主體在全球化視野下是否有變更?(3)政策轉移理論是不是一個完善的理性過程?(4)政策轉移理論是否有必要建立嚴格的理論界限?這在以往以理論爭辯或單一政策轉移案例分析的文章中并不能得出結論。因此,在之前的分析工具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就需要新的分析工具與分析方法來回應對于政策轉移理論的爭議。
二、政策轉移的質性研究設計
本文進行的案例研究是建立在政策轉移相關案例具有共通性的基礎之上的,盡管所篩選的案例涉及不同國家或地區、不同研究主題、不同時間段,但是所篩選案例都是建立在政策轉移理論共識之上。同時,建立在“政策擴散”“政策趨同”等概念框架之上的政策轉移理論初期就承認政策轉移之間的共性,其邏輯基礎就是政策之間的可借鑒性。
政策之間的共性也符合全球化的背景。有學者認為全球化意味著“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化”。4J. A. Scholte, Defining Globalisation, World Economy, vol.31, no. 11, 2008, p. 6.其被認為需要與世界范圍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融合同質化。盡管全球化在另一方面促進了文化的多元化,5J. A. Scholte, Defining Globalisation, World Economy, vol.31, no. 11, 2008, p. 12.但是這一觀點揭示了全球化帶來的全球范圍內包括政策領域的相似性趨勢。基于這樣的理論前提,才能夠賦予案例分析以合理性。
NVIVO軟件是功能強大的質性研究計算機輔助分析軟件之一,它提供質性研究者處理文件、PDF、圖片、音頻、視頻、數據集與矩陣框架等多種類型,可以進行數據的搜尋與編碼工作,以布爾邏輯為檢索基礎進行數據的網絡建構。6劉世閔、李志偉:《質化研究必備工具NVivo10之圖解與應用》,經濟日報出版社,2017年。本文采用質性研究方法,運用NVIVO軟件對政策轉移案例進行歸因分析。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又稱質的研究、質化研究。質性研究強調對研究對象進行后實證和經驗主義的考察分析,從批判立場對研究對象進行“解釋性理解”。7約瑟夫·A. 馬克斯威爾:《質的研究設計:一種互動的取向》,朱光明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質性研究橫跨不同的學科,同時也被許多復雜的、相互關聯的名詞、概念與假設圍繞。多數學者使用質性研究或質性探究通常包括民俗志或人種志(ethnography)、個案研究(case study research)、自然主義的探究(naturalistic inquiry)、民俗方法論、生命史方法論(life history methodology)、敘事研究(narrative enquiry)等。8郭玉霞、劉世閔、王為國:《質性研究資料分析:NVivo 8活用寶典》,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本文借用NVIVO軟件對政策轉移案例進行質性研究,通過編碼對政策轉移各要素進行歸納分析,通過多案例研究重新建立政策轉移框架,以便把握重點要素,加深對政策轉移理論的理解。

表1. 政策轉移框架
本研究樣本來自對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涉及關鍵詞為“政策轉移”文章中的案例進行重新編碼分析。在web of science上共搜索主題詞為“政策轉移”的文章共計798篇,除去與主題無關、無案例研究、未檢索到的文章,所采用案例分析文章共92篇,其中涉及“城市研究”22篇、“氣候政策研究”9篇、“環境研究”29篇、“教育研究”12篇、“醫學”3篇、其他類型17篇,在案例類型上基本遵循多樣的原則。92篇中,涉及“發達國家”研究59篇,“發展中國家”研究22篇,二者均涉及有11篇,因為政策轉移研究起源于發達國家,在比例上發達國家占比較大,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在最近的研究中有所增加,在國家分布上基本遵循多樣性的原則。在案例分析方法上,46篇文章采用訪談法進行分析,15篇文章采用歷史追蹤法,11篇文章采用文獻綜述法,20篇文章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在案例分析方法上基本遵循多樣性的原則。
所有案例分析遵循扎根理論的三種編碼過程:首先,對案例進行開放式編碼,選取基本編碼內容,進而建立關聯式編碼,最后歸納出核心編碼,從而建立起整個編碼框架。具體操作內容如下:首先通過對案例描述對所涉及內容進行開放式編碼,如“左翼和右翼聯合政府,或者至少是福利國家取向強烈的政府,都促進了全民長期護理計劃的建立”。1Paul Cairney, The Role of Ideas in Policy Transfer: The Case of UK Smoking Bans Since Devolu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9, vol. 16, no. 3, pp. 471-488.這一內容就可編碼為“政府治理需要”。“《氣候公約》發揮了論壇的作用,展示各國的緩解和適應活動,從而帶來積極的強化效應和群體壓力。”2C. Koski, Greening America's Skylines: The Diヵusion of Low-Salience Policie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 38, no. 1, 2016,pp. 93-117.這一內容就可編碼為“國家或地區競爭壓力”。而這兩個開放式編碼最終可以歸納為“關聯式編碼”——“政策轉移原因”。由此步驟對92個案例進行編碼,共產生開放式編碼43個,其中包含14個開放式子編碼,共涉及參考點共781個,產生6個關聯式編碼,最終核心編碼為“政策轉移框架”。表1為編碼示意圖,參考點越多,該編碼在案例中出現的頻率越高,證明該內容在案例中的共識性越高。
三、研究結果與爭議回應
根據政策轉移多案例的質性研究,本文建立了全新的政策轉移框架,可以看出這一框架雖然沒有完全脫離“道—馬模型”的分析要素,但是各分支之間的構成內容發生了變化,并且各要素的重要性可以根據參考點數量清晰的表述。因此,本研究將通過質性研究構建新的政策轉移理論框架,并對四個針對政策轉移的爭論作出回應。
(一)“軟轉移”與“網絡”——政策轉移新趨勢
政策轉移理論第一個爭論點是“政策轉移框架在現階段是否需要更新,各要素是否有重要性程度的排序”。通過質性研究的編碼過程對每一個編碼的參考點數量作出明確的梳理,可以看出“思想”在政策轉移中的角色突出,其中包括:“政策轉移內容”中“思想”所占比例最高,“政策來源國”的影響中“政策思想”所占比例最高,“政策轉移條件”中“意識形態相似性”所占比例最高。這說明思想要素貫穿政策轉移始終,影響政策轉移程度,成為政策轉移必不可少的條件。這一結論在以往的政策轉移文獻中雖有提及,但不是政策轉移研究重點,說明政策轉移各要素在該質性研究中有重要性之分,也說明了政策轉移各要素的重要性會隨著所處背景不斷更新,這一理論框架是動態而非靜止不變的。
思想要素在政策轉移理論中重要性的變化與當前的全球化背景緊密相關。這一點在編碼中也可以明顯體現:“政策轉移條件”中“全球化”也占比很大。“全球化”與“政策變革”之間的關系在學界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議題,其中目的論支持者和功能主義支持者認為全球化是由系統邏輯決定的機制創新,1Marcus André Melo, Institutional Choice and the Diヵusion of Policy Paradigms: Brazil and the Second Wave of Pension Refor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5, no. 3,2004, pp. 320-341.制度創新和新的政策范式是全球化的功能要求。也有學者認為國際性機構是促成“全球化”與“政策創新”相聯系的主要推動力。2Marcus André Melo, Institutional Choice and the Diヵusion of Policy Paradigms: Brazil and the Second Wave of Pension Refor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5, no. 3,2004, pp. 320-341.但是這兩種觀點都有各自的缺陷:前者沒有從微觀層面論證全球化與政策變革的聯系,后者陷入政治霸權主義和政治精英主義的理論之中。隨后,“思想”被認為是促成全球化時代“政策變革”的重要因素,在這里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思想是一種意識形態統治的機制,3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 vol. 46, no. 1, p. 1.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明顯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第二種觀點強調思想是獨立變量,4Hall P. A.,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5, no. 3, 1993, pp. 275-296.其認為因為思想所包含的理性因素使得在復雜的社會中,擁有法律理性的政府占主導地位,并且在社會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建構主義也對“思想”的作用起到重要作用,其認為在社會建構主義視角中,其以一個動態變化的世界為前提,強調主體間的理解,即決定行為者理解什么樣的行為是重要和合適的。因此,思想在社會建構主義框架中至關重要。1K. Fierke and K. Jorgensen,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34.“ 思想”這一要素在“政策轉移框架”內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說明了政策轉移的重點由具體政策向“軟轉移”即思想方向的偏斜,也說明了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的重要作用。但是,思想是無法量化但影響深遠的,這也增加了政策轉移研究的難度,因此在政策轉移研究中應該更加關注“思想”這一要素的重要作用。
“網絡”也是“政策轉移框架”值得關注的要素,其在“政策轉移條件”關聯式編碼中是與“全球化”相當的開放式編碼要素,僅次于“思想相似性”。這里的網絡并不是指“互聯網”,而是“全球公共政策網絡”2Diane Stone, Transfer Agents and Global Networks in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1, 2004, pp. 545-566.,也是“政策導向學習的框架”3Colin J. Bennett, What Is Policy Convergence and What Causes I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2, 1991,p. 215.。它代表了一種軟性、非正式和漸進的模式,用于在國際范圍內傳播思想和政策。通過網絡,參與者可以建立聯盟、分享話語并構建定義國際政策社區的共識性知識。網絡還使行動者能夠在其國內背景之外運作。
“網絡”的重要意義可以采用現代“空間政治”理論中的“收斂空間”理論來加深解釋。我們可以將“收斂空間”理解為一個“動態系統”,其構建在空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復雜性基礎之上,通過在特定時間在特定地點召集來自不同利益群體和資源的人來促進知識的產生、交流和合法化,同時基于地點的意識形態和差異在空間內進行談判。因此,收斂空間是在限定的時間里形成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短暫的。然而因為收斂空間是存在實體,其最終作用于人類實體,因此,它也是永恒的。4P. Routledge, Convergence Space: Process Geographies of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Network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28, no. 3, 2010, pp. 333-349.“ 空間政治”理論賦予“空間”以政治屬性,把其作為獨立變量考察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政治行為,“網絡”是由政治行為者基于共同利益促進交流的產物,其賦予了“網絡”合法性的解釋。
(二)政府主體地位
政策轉移的第二個爭論點是“政策轉移理論主體在全球化視野下是否有變更”。以往的政策轉移文獻對政策轉移主體有過詳細的論述,“道—馬模型”中對于政策轉移參與者有明確的界定,分別為民選官員、政黨、公務員、壓力團體、政策企業家和專家、跨國公司、智囊團、超國家政府、非政府機構和顧問。但是以往的政策轉移文獻對于政策轉移主體的重要性區分是模糊的,特別是隨著全球化網絡的建立,跨國機構或是非政府組織在政策轉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掌握大量的政策信息、利用自身跨國優勢作為政策轉移代理人為政府服務,并且擁有龐大的專業精英團體。政策轉移研究者也偏愛對于這類政策轉移主體的研究。然而根據“政策轉移框架”中的編碼,可以看出“政府”在政策轉移進程中依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在“政策轉移原因”關聯式編碼中“政府治理需要”開放式編碼參考點僅次于“國家或地區競爭”,“政策轉移參與者”關聯式編碼中“政府”開放式編碼參考點最多,“政策轉移限制因素”關聯式編碼中“政府”開放式編碼參考點最多。此外,在“政策轉移參與者”關聯式編碼的“專家”開放式編碼中,有大量涉及專家參與的文獻都是經由政府組織的,并沒有編入其中。
與新公共管理或新公共服務所倡導的政府角色不同,政府在政策轉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反映了政府在決策選擇、制定、執行、反饋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學者從“國家中心理論”視角探討政策轉移中的政府角色,其根植于轉型理論,將政策轉移視為轉變國家的關鍵戰略。1Mark Evans, Policy Transfer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Policy Studies, vol. 30, no. 3, 2009, pp. 243-268.國家間的競爭與全球政治環境的相對穩定使得政治精英從現實出發,通過在全球經濟領域的利益訴求尋求更大范圍的政治有效性。1998 年2月6日,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在美國國務院發表講話,概述了新工黨和新民主黨共同的“中左翼五項明確原則”,其涉及管理、教育、稅收、外交等多個領域,2Mark Evans, Policy Transfer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Policy Studies, vol. 30, no. 3, 2009, pp. 243-268.這一原則反映了英美雙方政策轉移的政策內容,也反映了政府在政策轉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府隨著全球化信息時代的到來,并沒有因此削弱在政策轉移中的作用,反而因為信息網絡的完善,政府意識到自身角色的轉變,使得政府成為推動政策轉移的關鍵力量。
(三)理性主義精神指導政策轉移實踐
政策轉移的第三個爭論點是“政策轉移理論是不是一個完善的理性過程”。“理性”是公共行政的重要概念,理性主義精神貫穿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其發端于古希臘,興盛于近代西歐,不同于哲學意義上狹義的唯理論,后者只是指與經驗主義相對立的一種認識論,而廣義的理性主義把人類理性當作知識的來源和驗證。3顧肅:《自由主義基本理念》,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14頁。近代政治學科學主義沖擊了政治學理性主義,對于超越性正義的至上正義的追求,似乎已經被實踐的技術方法所取代,這造就了社會價值的喪失,直至羅爾斯的《正義論》,才使得公共行政與政治學提出回歸理性主義的研究議題。
“吸取教訓”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理性政策制定與明顯非理性決策形式區分開來。4C. Argyris and D. Sch?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 MA: Addison Wesley, vol. 5, 2008, p.23.“ 吸取教訓”的概念深化了政策過程中的理性決策要素。其中“道—馬模型”中將政策轉移原因分為“自愿”“混合”“強制”三類,其中“自愿”即經驗吸取被稱為“完美理性”,“混合”即面對國際壓力進行的政策轉移被稱為“有限理性”,“強制”政策轉移自然歸為“非理性”過程。但是對這一觀點的批判者認為,“盡管在大多數政策轉移研究中都假設了合理性,但很少有行動者是完全理性的。大多數人在信息有限的情況下行動,或者在有限理性的范圍內行動。”5James O and Lodge M., The Limitations of 'Policy Transfer' and 'Lesson Drawing'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2, 2003, pp. 179-193.事實上,道洛維茨和馬什在探討政策轉移理論時,也討論了有限理性的含義,認為研究議程應該包括新制度主義的見解。6D. Dolowitz and D. Marsh, 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A Review of the P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1992, pp. 343-351.新制度主義探討了組織、結構、文化、規范和習俗怎樣構成社會行為,如何在行動者之間分配權力,以及怎樣塑造個人的決策過程和結果。因為政策轉移研究者更偏向于對轉移過程的探討,使得對新制度主義中有限理性的探討并沒有成為政策轉移研究的重點。在“政策轉移原因”關聯式編碼中,將其開放式編碼分為五個,分別為“政府治理需要”“國家或地區競爭”“自身發展需要”“強制轉移”“本國政治壓力”。按照“道—馬模型”中對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有限理性的劃分,“政府治理需要”與“自身發展需要”應該為理性主義,參考點共計53;“強制轉移”應該為非理性主義,參考點為5;“國家或地區競爭”與“本國政治壓力”為有限理性,參考點共計70。由此可以看出,在政策轉移原因中,有限理性占多數,理性主義次之,非理性主義最少。這印證了政策轉移的理性主義假設前提是合適的,當國家或地區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對國內外壓力之時就會通過理性決策進行政策轉移,也有些國家或地區會因為自身發展主動尋求政策革新,只有少數國家或地區在政策轉移過程中是被動的。這一編碼結果驗證了政策轉移理論理性主義假設的合理性,但是也對后續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關注點,即外部性壓力是政策改革的重要動力,在國家競爭愈演愈烈的國際環境中,國家或地區政府不得不尋求新的政策來進行自我革新以面對壓力。
(四)政策轉移沒有必要建立一個嚴格的理論界限
在前期的政策轉移研究中,自“道—馬模型”建立以來,政策轉移研究者的關注點在于政策轉移理論框架的完善上,理論爭論一方面為政策轉移理論的完善與發展提供了基礎,使得政策轉移理論實現了從“因變量”到“自變量”的轉型;但是另一方面使得政策轉移理論陷于理論框架的爭辯之內,不免使得研究者懷疑其理論貢獻。隨后,政策轉移理論轉向實證研究,多數文章以政策轉移理論為理論依托,采用訪談、數據分析等方法,通過對國家或地區具體政策轉移過程的追蹤或評估,評價國家或地區具體政策轉移案例,為后續政策實施提供方法指導。從本文所選取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案例呈現出多樣化、分散化的趨勢,政策轉移理論成為評估政策過程的理論工具。而通過對第一個批判的回應,“軟轉移”與“網絡”成為當前政策轉移研究熱點。這是全球化在政策研究領域的體現,這一時期的政策轉移理論為“軟轉移”與“網絡”在政策轉移中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
從政策轉移理論的基本脈絡可以看出,政策轉移研究者并沒有在當前國際環境發生劇烈變革的情況下囿于理論的爭辯,而是敏銳地察覺政策轉移理論的動向,使其更好地為政策研究服務。理論爭辯固然有利于理論的發展與進步,但是過多的理論爭辯則會使得理論本身成為束之高閣、玄而又玄的純粹理論本身。任何意識形態或理論的誕生都是有著深厚的現實背景的,任何理論的發展也都是因為現實的需要而不斷演進的。理論固然有其超越性,可以指導實踐,但根本上是源于實踐而非空想的,理論的最終歸宿也應該是現實社會,其本身反映著當代社會的變革。在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中,通過學者的交流與探討可以成為政策的風向標與指路燈。因此,通過對上文的總結與當前資料的回顧,政策轉移理論沒有必要建立一個嚴格的理論界限,嚴格框架的建立是不符合目前政策轉移發展方向與研究要求的,而應把政策轉移理論作為理論范式回應政策環境變化、評估國家間政策互動和預測政策領域研究動態。
四、政策轉移質性研究帶來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于政策轉移理論框架的編碼,對四個爭議性問題的回應可以看出政策轉移理論并非完美無缺,其在發展進程中存在爭議,在批判中吸納進步,不斷適應政策研究領域的新變化,為政策研究服務。我國學界對于政策轉移理論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大多數文章都是介紹國外政策轉移理論研究概況,也有部分文章與實際政策轉移案例相結合,但多集中于教育領域,這也與政策轉移理論案例研究本身的限制有關——其需要調查政策轉移過程,但這一過程通常是具有獲取難度的,案例研究需要研究者進行深入調查,這對于很多學者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此,把握當前政策轉移研究前沿議題尤為重要。
政策轉移研究中對于“軟轉移”的關注反映了政策傳播過程中“思想”的重要作用。在全球化、網絡化視閾下,“思想”借助新的傳播媒介不需要實在依托就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流動,這也為我國意識形態工作造成了難度。當政策轉移成為國家或地區制定政策的必要途徑,如何把握政策轉移過程中的意識形態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在新自由主義席卷全球時,其依托所謂“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傳播大肆宣揚西方價值觀。但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單純的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導致了2008年以來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1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西方“三大預言”為什么落空》,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330/c40531-28237111.html。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使得我國在國際政策傳播領域更應該警惕政策思想中的“意識形態”傳播,在汲取西方優秀政策思想的同時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避免政策傳播“意識形態化”。
政策轉移研究中對于“網絡”的關注強調了全球化環境下“網絡”建立的趨勢。政策轉移中的“網絡”最早可以追溯到“政策網絡”理論,早期政策網絡分析側重于研究利益集團和政府機構之間的關系,而后政策網絡被上升到宏觀治理層面的高度。2朱春奎:《政策網絡與政策工具:理論基礎與中國實踐》,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頁。政策網絡理論不僅迎合了描述自然和社會系統的復雜度的需要,更反映了人們對于社會認識視角的一種變革——“社會不再是被一種處于中心的智慧或能力所控制,相反卻分散在為數眾多的行為單元中。”3砳之:《政策網絡:公共政策分析新路徑》,《群眾》2017年第24期。“ 政策網絡”的各個派別在定義其基本內涵時都是從政策角色角度出發,探討政府與其他角色的互動關系。政策轉移理論中的“網絡”吸納了“政策網絡”理論范式中對“網絡關系”的關注,政府作為政策制定的行為者在“網絡”中扮演重要的中介作用,與專家團體、利益集團、公眾等建立多元互動的非正式中觀單位。這對于我國政策轉移實踐的啟示是,在國際政策網絡中,作為發展中國家應采取積極的政策學習態度。同時在國內政策轉移網絡中,政府必須掌握政策轉移的主動權,在政策轉移網絡中作為互動主體協調社會公眾、專家與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推動政策學習的理性轉移。因此,政策轉移理論經由比較政治學文獻梳理,而后在新公共管理框架中誕生,經歷了理論的爭辯、實證分析、“軟轉移”與“網絡”政策轉移等發展階段。政策轉移理論的質性研究,為我國面對全球化與網絡化新環境,如何適應政策學習環境、把握政策學習方向,在政策傳播過程中怎樣面對“思想”傳播等問題提供了理論借鑒,拓寬了思維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