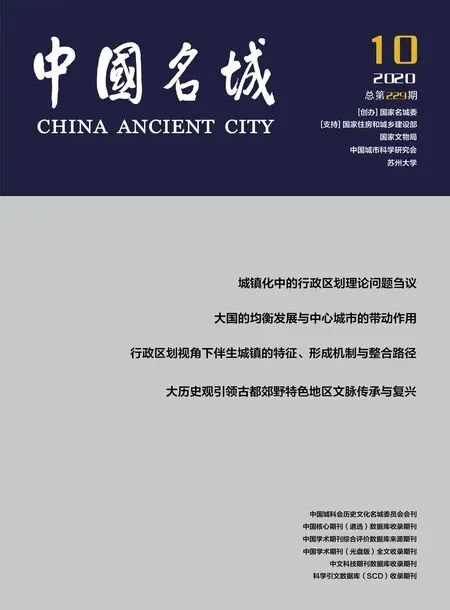中日韓行政區劃比較與空間治理啟示*
朱建華 修春亮
導語
行政區劃是大政國基[1]。中國自秦始皇在全國范圍推行郡縣制開始便有了規范統一的區劃體制。行政區劃是國家權力再分配的重要形式,中國區劃體制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制,而西方國家更多體現了地方自治。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因此,中國行政區劃管理體制有必要借鑒國外的先進治理體系和制度。通過解讀20年來區劃研究知識圖譜,發現區劃研究逐漸從區域經濟、城鎮化轉向管理體制改革[2]。減少區劃層級、推行省直管縣是主要趨勢[3]。有學者通過新區與行政區劃的耦合,建構了新的區域治理體系[4]。
西方學者更多集中于研究大都市圈區劃改革[5-6]、層級壓縮[7-8]及政區合并[9-10],尤其是地方自治[11-13]。劉君德等對國外行政區劃模式進行了總結,將世界各國的區劃體制分為英美、法德以及蘇聯3大模式,蘇聯模式對中國影響較大[14],美國的縣級政區設置也對中國區劃調整提供了經驗[15]。近年來俄羅斯也進行了行政區劃改革,增加了一級聯邦區來防止國家分裂[16]。國內還有學者也介紹了國外的行政區劃調整經驗和對我國區劃調整和改革的啟示,尤其在城市型政區和縣級政區方面存在很大差異[17-18]。
行政區劃具有歷史繼承性,同時也有明顯的地域型特征。中國、日本和韓國同處于東亞文化圈,在地緣位置上一衣帶水,在地域文化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行政區劃體制方面也是一脈相承,因此國內有許多學者研究了日本、韓國與中國的行政區劃比較與啟示[19-20],多側重于類型和模式和城市區劃制度的比較[21-22]。近年來,關于日韓都市圈空間結構等方面的研究對中國都市圈行政區劃設置研究也有較大啟示[23-26]。日本和韓國受中國古代行政區劃設置的影響較大,但后期有很多的探索和創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行政管理體系。目前,國內對日韓兩國行政區劃體制改革和創新的研究比較少。因此,本文基于比較視角,分析日韓兩國在行政區劃與空間治理體系方面與中國的差異,對今后中國的行政區劃體制改革和城鎮化進程提供一定參考。
1 中日韓行政區劃類型、層級與幅度的比較分析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省級行政區劃層面調整較少,總體格局較為穩定,近40年來主要是增設了海南省和重慶直轄市。但是,在地級、縣級和鄉鎮級行政區層面調整比較頻繁。自1978—2018年,地級市由97個增加到293個,縣級市由93個增加到375個,市轄區由511個增加到970個。
近代日本行政區劃始于明治天皇時期。1871年日本廢藩置縣,廢除260余藩劃分為3府72縣。1890年調整為1廳3府43縣,政區格局初步形成。1943年東京府改為東京都,1947年北海道廳改為北海道,賦予市町村地方自治權,使市町村成為日本的第二級行政區。
韓國的建國(1948年)歷史較短,因此韓國行政區劃調整相對比較簡單。1946年漢城市(今首爾)和濟州道分別從京畿道和全羅南道析置出來。1963—1997年,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和蔚山陸續升格為廣域市。2006年設立濟州特別自治道。2012年設立世宗特別自治市。至此,形成了韓國的行政區劃基本格局:即被稱為“廣域自治團體”的一級行政區,被稱為“基礎自治團體”二級政區以及面、邑、洞等基層政區。
1.1 行政區類型
日本、韓國現行區劃制度和名稱主要來源于中國唐朝時期。其中日本的都、道、府均是中國唐朝時期的區劃單位,“都”就是首都,“道”相當于今天的省,“府”是指較大的城市。而日本的“縣”和韓國的“郡”來自中國秦朝的“郡縣制”。
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行政區劃設置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除了常規的行政區劃設置類型外,還有一些特殊型政區。中國在少數民族人口集聚區域設立了民族自治政區,設立了5個民族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981個民族鄉。內蒙古自治區還有特殊的“盟—旗—蘇木”區劃體制。此外,在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后設置了2個特別行政區。日本一級政區以縣為主,但也有3種特殊類型:都、府、道(圖1)。韓國的特殊政區有濟州自治道以及世宗特別自治市(圖2)。

圖1 日本行政區劃格局圖
1.2 行政區劃層級
各國區劃層級一般考慮國土面積、人口數量、歷史文化傳統以及政治體制等因素[21]。中日韓3國雖然地理位置接近,但是國土面積、人口數量以及政治體制迥異,因此行政層級與體系各不相同(表1)。

圖2 韓國行政區劃格局圖

表1 中日韓行政區劃層級比較表
1.2.1 中國四級與三級并存的管理體制
中國行政區分為4個層級:省、自治區—市、州、盟、地區—縣、縣級市、市轄區—鄉、鎮、街道,但也有部分地區實行三級制:(1)直轄市,沒有省這一級。4個直轄市都是“直轄市—區(縣)—街道(鄉鎮)”三級制類型;(2)“省直管縣(市)”,沒有地級市這一級。海南省、河南濟源、湖北省天門、仙桃、潛江等屬于“省—縣(縣級市、林區)—鄉鎮街道”三級制類型;(3)地級市直管鄉鎮街道,“直筒子市”下面不設區縣。共有儋州、三沙、東莞、中山、嘉峪關5個不設區的地級市,屬于“省—地級市—鄉鎮街道”三級制類型;(4)縣級市或市轄區直管社區,沒有鄉鎮街道這一層級。三亞市、內蒙古二連浩特市等屬于“省區—地級市—市轄區(縣級市)”三級制類型。
1.2.2 日本兩級扁平化管理體制
日本區劃層級較少,實行都、道、府、縣—市、町、村兩級管理。截至2018年,日本共有1都(東京都)、2府(大阪、京都)、1道(北海道)、43縣,共47個一級政區。都道府縣下設有791個市、744個町、183個村共1 718個二級行政區。東京都下設23個特別區,除東京外,另有17個規模較大的城市設有市轄區。北海道由于面積較大,在道與市町村之間設有14個綜合振興局(原為支廳),為特別地方政府。
1.2.3 韓國三級管理體制
韓國的行政層級為三級。截至2018年,韓國共有17個一級政區:1個特別市、1個特別自治市、6個廣域市、8個道和1個自治道。一級政區下面共設有228個二級政區:73個自治市、86個郡、69個自治市轄區。三級基層政區有3種類型:面(鄉)、邑(鎮)、洞(街道)。此外自治市當中有12個特定市設置了“區”。
1.3 行政區劃管轄幅度
中國34個一級政區除了港澳臺及4個直轄市外,其他27個省區平均管轄12.37個二級政區,二級政區平均管轄8.4個三級政區,三級政區平均管轄14.4個四級政區。中國區劃結構呈現高聳式金字塔特征,每一級政區管轄幅度比較小。日本一級政區平均管轄37.0個二級政區,管轄幅度大、層級少,屬于典型的扁平式管理結構。韓國一級政區中除世宗市(無二級政區)外平均管轄14.5個二級政區,管轄幅度比中國略大。
1.4 行政區劃管理體制改革
中國許多地區正在由四級向三級改革,走“扁平化”行政管理模式,提高行政效率,節約行政成本。在管轄幅度方面,自1986年農村改革開始大規模的鄉鎮合并,中國鄉鎮數量從1985年的91 338個,到1995年下降為47 136個,到2018年下降到31 552個,與改革前的1985年相比鄉鎮數量減少了約三分之二。街道數量從2000年的5 902個增加到2018年的 8 393個,增加了2 491個。
日本行政區劃改革方向是在層級方面取消了“郡”,在管轄幅度方面進行市町村大規模合并。日本曾經有“郡”(介于縣與市町村之間),1923年廢除了郡制,但在選舉、郵政和統計等事務中仍起作用[27]。1965年日本頒布了《市町村合并特別法例》,鼓勵市町村合并,但一直到1999年市町村總數由1965年的3 392個下降到3 232個,這一時期變化并不大。在1999—2006年期間推行大規模的政區合并,史稱“平成市町村大合并”。2006年3月僅剩1 821個市町村。根據日本總務省數據,截至2018年底共有1 718個市町村,與1999年相比二級行政區數量減少了近一半。長期以來町的數量一直最多,通過市町村合并后,町和村的數量持續下降,相反市的數量不斷增加,2010年市的數量開始超過了町。并且,部分中核市和特例市通過整合,升格為了政令指定市,例如濱松和新潟兩市分別由12個和13個市町村合并而成。日本的市町村合并加速了城鎮化進程,通過城鄉一體化帶動了一批城市的發展[28]。日本城市數量的增加和市町村的合并是和城市化快速推進相吻合的。
韓國自建國后長期跟中國一樣,實行城鄉分離管理,從原來的郡劃出城市化地區單獨設立“市”,類似于中國的“切塊設市”。1994年開始設置“都農復合形態市”,改革的原因是城鄉分離型政府割裂城鄉共同生活圈。韓國城市設置模式由“切塊設市”走向了“市郡合并”或“整郡設市”,例如,1998年全羅南道的麗水市、麗川市和麗川郡合并為新的麗水市。1996年后韓國設立的14個市中有13個為“都農復合形態市”。因此,近年來韓國設立的市也都屬于地域型城市。
2 中日韓城市行政區劃體制的比較分析
在建制市數量方面,截至2018年底,中國共有672個,日本有791個市,韓國共有85個市。但是不同城市有著不同的行政等級和權限,設置標準也不相同,并且規模較大的建制市下面分設了市轄區,小城市一般不設置市轄區。
2.1 城市行政等級體系
中國的城市等級體系主要分為“三級四等”,包括直轄市、地級市、縣級市3個主要層級,還有15個副省級市。日本根據人口多寡劃分城市為4個等級:政令指定市、中核市、特例市、一般自治市,等級越高的市權限越大。其中,政令指定市共有20個,擁有“縣”一級的權限,中核市有45個,特例市有39個,一般自治市共有687個。韓國的城市分為3個等級:特別市或廣域市、特定市和自治市。韓國共有8個特別市或廣域市,15個特定市,62個自治市。
總體而言,中日韓三國的城市等級體系有較多相似性,不同行政等級的城市具有呼應和一致性。日本的都、府以及韓國的特別市和廣域市相當于中國的直轄市;日本的政令指定市和韓國的特定市相當于計劃單列市;日本的中核市、特例市相當于地級市;日本的一般自治市和韓國的自治市相當于縣級市。但是,城市的隸屬關系存在明顯不同。日韓城市之間無隸屬關系,城市直接歸都道府縣管轄,而中國城市行政等級較多,出現了地級市代管縣級市的普遍情況。
2.2 城市建制設置標準
通過比較發現,中日韓三國不同等級的市設置標準差異較大(表2)。其中,中國設市標準要高于日本和韓國,而且有許多縣、鎮已經達到了設市標準卻未設市,這也是中國建制市數量相對偏少尤其是小城市比例較少的主要原因。但是地級市設置標準較低,一般由地區(省政府的派出機構)改設為地級市,如最近西藏的山南地區改設為山南市,新疆的哈密地區改設為哈密市。中國直轄市、副省級市等高等級城市沒有明確標準,而日韓兩國對高等級城市設置有明確的人口標準。

表2 中日韓城市建制標準比較表
2.3 市轄區設置的比較分析
在城市市轄區方面,中國的地級以上城市普遍進行分區,但也有5個地級市沒有設置市轄區,而縣級市無論規模大小均沒有設置市轄區。也就是說,中國城市根據行政等級而不是人口規模來設置市轄區[29]。
日本城市數量多,但設置市轄區的市僅有18個。其中,東京都下面分設了23個特別區,此外還有大阪、名古屋、京都等17個政令指定市設置了市轄區。1992年,日本只有13個城市劃分了市轄區。自大規模推進市町村合并以來,埼玉、靜岡、堺市、濱松和新潟5個市通過合并周邊市町村,均升格為政令指定市,并分設市轄區。日本市轄區的總體特征是數量多且規模偏小,18個設區城市共有186個區,其中最多的大阪設有24個區(平均每區不到10 km2),最少的靜岡市設3個區。186個市轄區中面積超過100 km2的僅有19個,而不足10 km2的卻多達30個,人口不足10萬的區多達39個,日本很多市轄區其實就是一個町的規模。這種市轄區格局導致城市分區后,下屬機構規模過小、數量過多,市與區的管理協調難度加大[30]。
韓國市轄區設置標準為人口不得低于20萬人,超過50萬人可設2個區,超過75萬人可設3個區。首爾分設了25個區,6個廣域市分別有4—15個市轄區。根據設區標準,韓國的水原等12個“特定市”也可設置市轄區,共設有35個市轄區。因此,韓國特別市、廣域市和特定市共設有104個市轄區。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日本791個城市中設區市僅有18個,設區市占比僅有2%左右;韓國85個城市中設區市也只有19個,占比約22%;而中國設區市有293個,占城市總數的44%。其中,中國市轄區數量最多的是重慶市(26個),北京、上海和天津3個直轄市各有16個市轄區。中國有70個地級市僅設一個市轄區,而日本設區市至少有3個區,韓國設區市至少有2個區。中國市轄區設置標準偏低,新增市轄區大多數為大城市周邊的縣或縣級市改設而來,城鎮化率偏低,許多市轄區與縣沒有太大區別;而日韓的市轄區基本是建成區,城鎮化水平接近100%。中國還有一種特殊的“飛地”市轄區,有30個城市的部分市轄區與主城區并不相連,比如重慶市的萬州區與主城區中間隔著幾個縣。中國缺乏設置市轄區標準,市轄區設置比較隨意且混亂。相對而言,日本、韓國設置市轄區較為嚴格。與日韓相比,中國設立市轄區的城市數量較多、但多數設區市的市轄區數量偏少(全國平均每個設區市管轄3.2個市轄區),市轄區規模大但人口密度和城鎮化水平較低。
3 空間治理啟示
日本和韓國國土面積都不大,歷史上曾經借鑒過中國唐朝時期的行政區劃管理體制。但是,日韓兩國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較高,尤其是在城市行政區劃設置與現代化都市圈管理體制方面有很多值得正處在高速城鎮化進程中的中國學習借鑒。
3.1 行政區劃層級與管轄幅度方面的啟示
在行政層級方面,中國應適當減少行政管理層級,在條件合適的部分地方實現省直管縣(市)、縣級市直管社區。在管轄幅度方面,各級行政區的管理幅度需要有一定的合理限度,管轄幅度過大不利于精細化管理和為轄區居民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影響管理效能;管轄幅度過小會造成行政資源的浪費,造成行政機構和編制過于臃腫。中國一級政區數量偏少,應適當增設直轄市,中國僅有4個直轄市,而韓國有9個特別市和廣域市,中國應當從減少省級政區行政管轄幅度、培育區域增長極的目標出發,將深圳、青島、大連等經濟實力強、區域帶動效應大的城市升格為直轄市,達到分省的目的,不斷優化省級政區行政管轄幅度。日本減少“郡”這一層級以及“市町村大合并”,有效地提升了治理效率,而且增加了市的數量,大幅壓縮了實力較弱的町和村。給中國的啟示是,應當通過縮小省區和合并小縣的改革,可以為減少行政管理層級,實現省直管縣提供基礎支撐。例如,河北省有24個縣面積不到500 km2,而且很多小縣彼此相鄰,可以進行整合。
3.2 城市型政區發展啟示
根據日、韓城市型政區的數量和標準而言,中國的城市型政區數量明顯偏少,設置標準明顯偏高或缺失。首先,完善設市設區標準,穩步增加城市數量,尤其是培育新生中小城市。日本國土面積和人口遠低于中國,但是城市總數比中國還多100多個,而韓國面積和人口僅相當于中國一個普通的省,但是城市數量比中國任何一個省區都要多。而所有省當中最多的山東省共有44個建制市,排名第二的廣東省有41個建制市,山東和廣東兩省建制市總和才相當于韓國的建制市數量。因此,需要增設一批中小城市,不僅可以考慮將一些經濟發達縣和特大鎮改設為市,也可以依托一些開發區、風景名勝區進行切塊設市,促進設市模式的多元化。其次,在城市建制名稱方面,中國城市行政等級太多,國內學者提出可以學習日本的都、府制,將直轄市改為“都”,地級市改為“府”,以便區分城市等級[31]。第三,在市轄區方面,日韓的市轄區設置標準更為嚴格,與建成區范圍大致吻合。而中國的市轄區規模差異大、城鎮化水平低、缺乏標準,因此,中國應當盡快制定市轄區的設置標準,在新設置市轄區的時候嚴格把關,并且盡量減少“一市一區”現象。
在城市行政區劃模式方面,日韓城市大多數為狹域市(韓國13個“都農復合形態市”屬于廣域市),屬于“城鄉分治”模式,城市范圍基本全是建成區,統計口徑上更符合城市的概念;缺點是同一個城市連續建成區可能包括了多個城市,導致“碎片化”管理,難以協調發展、效率不高。而中國的城市基本都是廣域市,屬于“城鄉合治”模式,市域范圍包含了廣大農村區域,優點是為城市向外拓展留足了空間,缺點是城鄉的概念相混淆,建制市實際上屬于區域的概念,統計數據包含了不少農村地域,城市還承擔了管理農村和發展農業等功能。這方面給我們的啟示就是,中國在保留“廣域市”模式的同時,應當嚴格劃定各等級城市的“城區”范圍,作為一個各項指標統計區,在與國外各大城市比較分析的時候應當用“城區”的統計數據做對比。
在城市行政區劃改革方向上,中國在快速城鎮化的背景下出現了大規模的“撤地改市”“撤縣改市”,城市市轄區改革方向為“內城合并,外城擴張”,即老城區小的市轄區合并,大城市周邊縣市改區,例如北京市內城的東城區和崇文區、西城區和宣武區進行了合并,而外圍的延慶縣、密云縣改為市轄區。日本多個城市通過市町村合并升格為政令指定市,例如2010年熊本市通過合并植木町和城南町,人口突破70萬,2012年成功升格為政令指定市。隨著政令指定市數量的增加,日本市轄區數量也在不斷增加。日本也存在“市改區”的趨勢,例如2005年巖槻市并入埼玉市,改設為巖槻區。韓國的城市行政區劃改革方向為“減郡增市”,出現了不少“市郡合并”“整郡改市”的區劃調整案例。由此可見,行政區劃調整是城鎮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日本和韓國都在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相應的行政區劃調整,中國在增加建制市的同時,也需要通過大城市周邊的“縣市改區”來提升中心城市的競爭力。
3.3 空間治理體系的啟示與借鑒
日韓兩國已基本實現了地方自治,充分激發了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活力。中國除了少數民族地區,還沒有實現地方自治。未來中國應當制定《地方自治法》,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限,構建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情的“地方自治體系”。與日韓兩國不同,中國大量的新城新區等經濟功能區打破了原有的行政區劃管轄體制,而且設置了管委會等機構。未來應當借鑒日韓新城新區的設置經驗,樹立行政區劃的權威性,強化行政區的法定性,在依法治國和構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上規范我國新城新區的設置。此外,日本東京都市圈、韓國首爾都市圈與中國的京津冀都市圈行政區劃結構比較相似(圖3),日韓首都圈的行政管理和區域協同發展模式十分值得我國的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借鑒,例如成立都市圈委員會等協調機構,在交通銜接、產業分工、空間管制及生態環保等方面實施更有效的管理。

圖3 中日韓首都圈行政區劃空間結構對比圖
4 結語
中、日、韓同處東亞文化圈,地域文化相近,在行政區劃設置上有很多相似點,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區別。日本和韓國早已步入發達國家行列,兩國行政區劃設置經驗和改革方向對我國優化行政區劃設置和推進管理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一方面,與日韓相比,我國的行政層級和管轄幅度不盡合理,應該積極推進行政層級的優化,逐步實現四級制向三級制的轉變。在管轄幅度方面,通過撤鄉并鎮、小縣合并等方式,優化行政管轄幅度,精簡人員機構,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斷增設城市型政區,不斷優化我國的城鎮體系等級規模結構。截至2018年,日本城市化水平已達到93%,韓國城市化水平達到82%,而我國城鎮化水平僅有59.58%。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在今后20年中國行政區劃調整的需求會不斷增加,設市設區的空間仍然很大。因此,中國政府做好設市設區規劃,積極引導地方政府優化行政區劃設置,增設城市型政區,成為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