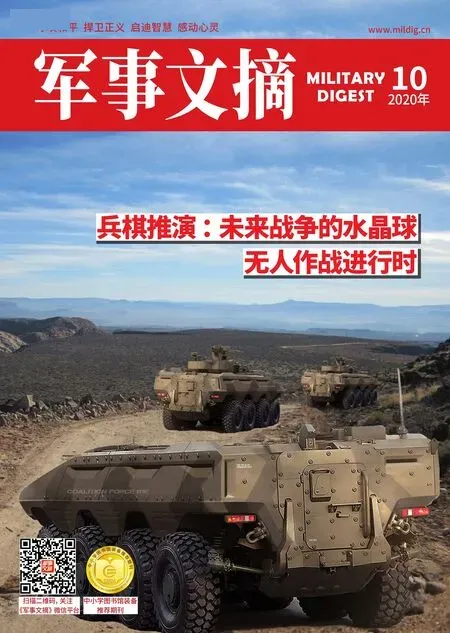無人化裝備給偵察情報帶來的新變化
胡勁松 黃文濤

偵察歷來是勇敢者的行動,危險系數高,條件艱苦,但隨著高新技術的飛速發展,各類無人裝備層出不窮,涌現出高空偵察衛星、無人偵察機、全地形無人偵察車、無人船和無人潛艇等各式各樣的無人偵察平臺,為偵察行動無人化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偵察行動呈現出向“無人化”迅速發展的新趨勢,這必將給偵察情報工作帶來新變化。
作戰功能逐步增強,情報與作戰融為一體
近年來,無人化裝備數量呈現爆發式增長,裝備體系日趨完備,偵察功能越發強大,其在戰場的應用也成加速普及態勢。
無人化偵察裝備常態使用。無人偵察平臺自越南戰爭首次投入使用以來,幾乎出現在之后西方大國主導的所有世界局部戰爭中。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利用5顆成像偵察衛星,保障前線作戰指揮官在12~24小時內得到伊軍動向情報;科索沃戰爭期間,美軍派出捕食者、獵人、全球鷹等無人機進行偵察,為多國部隊不間斷地提供戰場信息;阿富汗戰爭中,美軍使用派克波特地面偵察平臺實施洞穴搜索任務;伊拉克戰爭中,美軍使用地面偵察平臺獲取戰場態勢感知,有效地保障了巷戰中的情報偵察;敘利亞戰爭中,美俄幾乎將戰場當成無人偵察平臺的實驗場。無人化偵察裝備具有體積小、造價低廉、對作戰環境要求低、戰場生存能力較強等諸多優點,既能降低戰爭成本又可減少人員傷亡。據此可以預言,在未來戰場,無人化偵察裝備將被更加頻繁地運用于情報偵察,并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偵察情報作戰功能日益凸顯。當無人偵察技術不是一種、兩種,而是以“技術群”的面目出現時,無人化偵察裝備的功能也隨之日益拓展。在實踐運用過程中,特別是搭載各種致命和非致命武器后,無人化偵察裝備正逐步從單純的情報、偵察、監視平臺向綜合作戰平臺發展,其打擊能力的提升,使偵察情報與攻擊行動逐步融合,促使偵察情報由輔助性作戰保障向直接遂行交戰任務轉變。美軍在聯合作戰準則(JPl-02)和空軍作戰準則(AFDD2-9)中對情報、監視、偵察(ISR)作戰作了明確的定義,認為“ISR屬作戰行動而非支援行動,是各種作戰行動的基礎,是跨軍種、跨領域的聯合行動”。縱觀近幾場局部戰爭,軍事情報的內涵、地位與作用已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偵察情報的對抗領域不斷拓展,手段運用更加多樣,基本功能不斷擴展。偵察情報不僅成為關鍵的戰斗力要素、體系作戰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業已成為一種獨立的作戰樣式,其作戰屬性日趨明顯,偵察情報與作戰越來越趨向一體化。
兵力密度迅速降低,人員角色面臨改變
人類戰爭發展的歷史表明,戰場上作戰人員的密度,隨著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發展而呈現下降趨勢。信息時代,無人偵察裝備日趨智能化,致使任務區域的偵察人員數量急劇減少,進而促使其在偵察情報工作中的角色悄然發生改變。
戰斗“位置”正在后移。集偵察、監視與打擊能力于一體的無人化偵察裝備,如地面無人偵察車和戰術無人機,正逐步取代偵察人員遂行抵近偵察和敵后偵察任務,迫使偵察人員從前沿陣地向更加安全的地區轉移。通過操作系統軟件,遠離一線戰場的偵察人員以非現場、非接觸地方式實施偵察行動,從而開辟情報偵察的嶄新樣式。
能力需求有所改變。無人化偵察裝備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對操作人員的素質要求也越來越嚴格,這種素質不是體能,而是智能,即相當的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適應未來作戰所需,偵察人員需對自身能力素質進行“更新”,重點突出情報融合和綜合研判能力訓練,實現從偵察技能向分析研判情報能力轉變。
兵員結構急需重構。由于系統的操作員不受年齡、性別限制,以往由男性偵察兵為主實施的偵察行動,現在女性坐在計算機前操縱設備就能完成任務,而且年齡的要求也隨之大幅放寬,不論是剛剛成年的新兵還是年過半百的老兵都能勝任。這些變化將導致偵察人員大幅減少,技術專家和保障人員相對增加,無人化偵察裝備將成為偵察分隊的主體力量,從而使兵員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
生理影響大幅降低。偵察情報危險性大,工作強度高,偵察人員容易身心疲憊,從而導致工作效率下降。但無人化偵察裝備只要電力供應及時,幾乎可以全天24小時始終如一地保持高效工作狀態。美國的全球鷹無人機可以飛行41個小時,并全天候、高效率地執行偵察監視任務。如此長時間飛行,對有人機駕駛員而言是難以承受的,而且難以保證不出差錯。未來戰場,無人化偵察裝備將從介入偵察行動轉為主導偵察情報工作,其“不知疲倦”的優良特征將有效降低由于人類疲勞所帶來的敵情錯漏的可能。
技術偵察比重上升,戰場迷霧呈現新的變化
信息時代,無人技術的飛速發展,使人的智能開始轉移或物化到裝備上,而裝備性能的提升,將促使技術偵察成為情報獲取的決定性因素。
技術偵察的地位更加重要。現代戰爭已覆蓋陸、海、空、天、電、網等多維戰場空間,偵察范圍急劇膨脹,加之敵方通信設備的保密性、部隊偽裝的嚴密性、機動的快速性等都有了極大地改進和提高,對如此高度現代化的敵人進行偵察,光靠傳統的偵察手段已難以滿足作戰情報所需。隨著無人化偵察裝備陸續登上戰爭舞臺并加速普及應用,以往那種主要依靠偵察人員前出或深入敵后獲取情報的行動場景將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類先進的高空衛星、隱蔽飛行的無人機、功能齊全的裝甲偵察車、靜噪巡游的無人潛航器等,它們將利用自身及加裝的特殊電子設備,在多維戰場空間大范圍的開展偵察活動。這些先進的技術偵察手段,偵察距離遠、速度快、覆蓋面大,效率遠勝人力偵察,在未來戰場必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美軍的全球鷹無人機

美軍鎖眼-12光學成像衛星
傳統環境因素的干擾作用明顯減弱。地形、氣象、天候等自然環境歷來是影響情報偵察效率的重要因素,但隨著軍事技術的進步和偵察裝備性能的提升,這種影響將大為改善。美軍鎖眼-12光學成像衛星的地面分辨率達0.1米,長曲棍球雷達成像衛星能識別地下數米深的目標,暗星無人機裝備的合成孔徑雷達能從地面雜波中區分出固定目標和運動目標,并能有效地識別偽裝和穿透掩蓋物,捕食者、影子等無人機均能克服夜暗和雨霧等影響,全天候執行偵察任務。偵察技術的強勢崛起,將有效克服傳統環境因素所造成的不利影響,使物理空間的戰場環境逐漸“晴朗”。
網電空間因素的影響力日益增強。當技術的進步逐漸撥開傳統“戰爭迷霧”之時,網絡和電磁等虛擬空間因素對偵察情報的影響正急劇增大。一方面,龐大而復雜的網絡支撐著整個情報體系的高效運行,但網絡本身的脆弱性也帶來了極大的安全隱患。網絡空間的開放互聯、龐大的用戶群體、被動的防御特性、未知的安全漏洞,使得網絡攻擊隱蔽性強。情報的處理、分發須臾離不開安全穩定的網絡支撐,網絡一旦癱瘓,偵察情報工作將舉步維艱。另一方面,戰場上的無人化偵察裝備種類繁多,特別是重點區域和要害目標附近,用頻裝備數量龐大,導致局部電磁擁擠,容易發生頻率自擾現象,而且敵極有可能對我實施電磁干擾、壓制,使得無人化偵察裝備的穩定運行遭受嚴峻考驗。因此,在未來戰場,盡管偵察行動日益無人化,但在網絡和電磁空間環境等新型“戰場迷霧”的干擾下,偵察情報工作仍將面臨不少困難。
平戰界限趨于模糊,情報對抗重心開始前移
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關鍵技術的相繼突破,無人偵察裝備的續航時間和偵察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使偵察情報呈現出新的特點。
偵察監視融為一體。戰場情報需求具有長期性和動態性的特點,同時滿足這一要求,需要偵察與監視逐步融合,其實現的前提是偵察長時化。隨著動力技術的提升,部分無人化偵察平臺巡航值守時間長達數年。如美國波音公司開發的禿鶩太陽能高空無人機,可以依靠太陽能飛行長達5年,由于它的高度比衛星低,滯空時間長,其偵察效率要遠遠高于衛星。類似這樣的無人機,既能長時間的搜集情報,又可及時捕捉動態信息,使偵察與監視之間的“間隙”逐步彌合。
平戰情報無縫對接。各種無人化偵察裝備在信息系統鏈接下,構成了外層空間、空中、地面、海上、水下立體的全方位、全天候偵察探測系統,多種偵察手段取長補短,各類情報相互印證融合,戰場感知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使得和平時期的情報積累與戰時情報需求實現無縫銜接。如伊拉克戰爭前,美軍早就完成了伊全境的地形數字化,并繪制了三維地形圖,還調用雷達成像衛星對伊拉克進行全天候、全天時的嚴密監視,這些戰前得到的情報為美軍戰時核實目標,指揮作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抗重心向前推移。美國空軍負責情報的大衛·德普圖拉中將在2007年的一次發言中說:“去年6月份我們在伊拉克擊斃了扎卡維,這次行動包括無數的分析時間,約600個小時的捕食者行動時間,以及10分鐘的F-16打擊時間。”在這個案例中,發現、定位、跟蹤和鎖定的過程要比打擊時間長得多。這反映出,在未來戰場,先進的偵察設備使戰場透明度空前增大,原本需要在臨戰前或戰中派人深入敵后探測的情報,通過平時的偵察、監視,便能預先掌握,情報搜集的準備工作在戰前幾個月甚至更早時間就已展開,而真正交戰的時間卻越來越短,迫使情報對抗起始時間大大提前,以往隱蔽的戰前偵察活動將變得異常激烈,交戰的重心也隨之前移。
行動隱蔽手段靈活,情報獲取趨于實時化
信息化戰爭,誰能更快、更準、更安全地獲取情報,誰就能更主動地掌握戰場先機。無人化偵察裝備以其隱蔽、小巧、智能和網絡化的優勢,成為偵察情報的“新寵”。
行動隱蔽風險小。派間諜打入對方機構或深入對方國土竊取情報,風險大,難度高,一旦敗露,可能引發重大的外交危機和政治沖突,但隨著航天技術、新材料技術、納米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無人裝備正朝著信息化、隱形化、微型化方向發展。偵察衛星掠過天空,隱形無人機飛躍國土,無人潛艇游弋海疆,都可以悄無聲息地開展偵察情報工作。未來使用蒼蠅機器人、蜜蜂偵察兵、昆蟲探測器進行偵察,即使翻越墻壁、穿門入戶也難以被人察覺,大大降低了行動風險,使情報收集方在政治上更為主動、更為隱蔽。

挪威黑色大黃蜂無人機
情報獲取手段多。與人相比,無人化偵察裝備更加不怕“犧牲”,在戰場上敢于沖鋒陷陣,能夠毫不畏懼地突入敵方陣地探測情報。一是誘敵開機獲參數。偵察分隊可派遣部分無人機或地面裝甲偵察車充當誘餌,引誘敵方雷達開機,使己方迅速掌握敵方的雷達頻率和陣地位置,為后續的反輻射武器提供參數。二是混合編組強行偵。當敵對空防御較為嚴密時,可采取無人干擾機和無人偵察機混合編組的方式,由若干架無人干擾機在前,擔負干擾、壓制任務,掩護后方無人偵察機強行突入敵方縱深陣地執行電子偵察和照相偵察任務。情況緊急時,甚至可將前方無人干擾機作為“敢死隊”,大量消耗敵防空武器,掩護無人偵察機直接飛抵目標上空執行偵察任務。三是勇闖禁區實地查。種類繁多的無人化偵察裝備可進入危險區域實施偵察任務。如三防偵察機器人可進入染毒地域檢測受染情況,各型地面偵察車能突入交戰區收集情報,微型裝備如身長僅0.1米的挪威黑色大黃蜂無人機,能靈巧地進入建筑物和地下室,及時向后方操作人員傳送實景畫面。
網聚信息反應快。在戰場網絡的鏈接及融合下,每一個無人偵察平臺的預警范圍都不僅僅是其自身偵察設備的預警范圍,而是部署在不同空間的整個偵察預警網絡的預警范圍。預警時間,也將取決于戰場網絡系統中某一預警平臺最早發現目標的時間,從而使得重點監視區域的目標“出現即被發現”成為可能。置于網絡之中的無人化偵察設備一旦獲取信息,便可通過數據鏈系統瞬間將信息集聚到情報數據庫之中,并以通用態勢圖的形式呈現在作戰指揮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而后依據指令,快速準確地并行分發給行動在各個戰場空間的作戰力量,為其提供近乎實時的共享情報,使其盡早獲知戰場態勢,先敵采取作戰行動,進而掌握戰場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