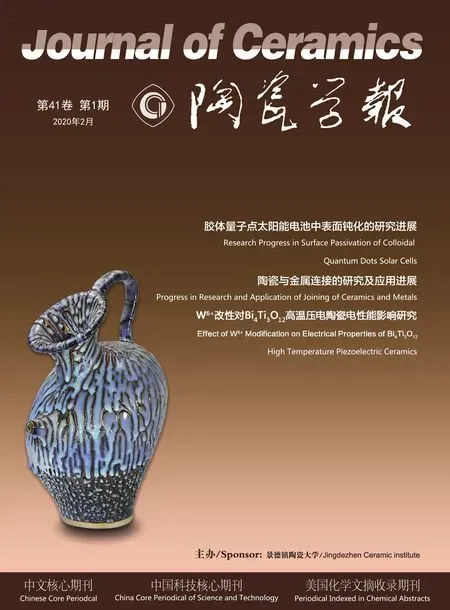見證雕塑瓷廠的發(fā)展與變革,暢談陶瓷藝術的發(fā)展之道
——采訪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劉遠長
陳麗萍,任東方
(1. 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江西 景德鎮(zhèn) 333403;2. 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 科技藝術學院,江西 景德鎮(zhèn) 333001)
【采訪時間】:二零一九年三月
【采訪地點】:劉遠長工作室
【采訪人員】:陳麗萍,任東方
劉遠長(1939-),男,江西吉安人。一九五九年考入景德鎮(zhèn)陶瓷學院美術系雕塑專業(yè),一九六三年大學本科畢業(yè)后分配在景德鎮(zhèn)市雕塑瓷廠,從事陶瓷雕塑設計與創(chuàng)作,后歷任美研所所長、雕塑瓷廠副廠長、廠長等職。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代表作品有《哈哈羅漢》、《天女散花》等。
1 劉遠長的藝術實踐與藝術思想
1.1 雕塑瓷廠藝術實踐與陶院教育的區(qū)別
劉遠長一九六三年進入雕塑瓷廠后,既在普通車間工作過,后來又長期在“創(chuàng)研室”搞創(chuàng)作。一九八一年做美研所兼職所長,一九八四年升任副廠長,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任廠長。
談到這些經歷,劉遠長認為雕塑瓷廠的藝術實踐與景德鎮(zhèn)陶瓷學院教育相比,有四個不同:

1.4 藝術理論建設很重要
劉遠長認為無論是學校育人還是藝術創(chuàng)作,甚至社會與企業(yè)的發(fā)展,包括藝術理論在內的“理論建設”都很重要。他認為,“在學校中一定有一個積極向上的正確理論。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理論,就缺乏一種精神,就像企業(yè)文化。一個企業(yè)沒有文化,就沒有企業(yè)精神。一個城市也是這樣的,如果你沒有文化,也就沒有精神。大氣成景、厚德立鎮(zhèn),這很重要。立德才能立業(yè),這就是為什么說理論很重要。”(引自口述)
關于當代藝術理論建設的現狀,劉遠長認為目前比較缺乏。他說:“景德鎮(zhèn)的陶瓷藝術現在這么活躍,但是卻缺乏一支理論隊伍。”原因在于:“現在的創(chuàng)作力量和創(chuàng)作的門類都在不斷的壯大。過去有那么一兩個人寫文章就行了,可以寫景德鎮(zhèn)的十大瓷廠各有什么樣的特點,有幾篇文章就可以了,但是你現在不夠了,時代在發(fā)展,創(chuàng)新門類多、品種多、人員多。理論上就顯得少啦!”(引自口述)
如何進行藝術理論研究?劉遠長認為有幾件事情很重要:第一,理論研究要有“歷史感”,即“理論隊伍要多談一些景德鎮(zhèn)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第二,理論研究“要客觀”,過褒過貶都不可取。他認為“有些搞理論的對景德鎮(zhèn)就很悲觀,這個落后,那樣不行。有的人就很樂觀,這樣行那個好。理論應該怎么做?好的在哪里,差的在哪里,哪些應該去弘揚去發(fā)展,哪些應該去制止去限制?”“現狀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應該怎么去發(fā)展?”第三,理論研究要“通俗易懂”,即“正確的理論在整個行業(yè)都有很大的影響,這些理論要通俗易懂”,不能“書寫出來,最后誰都沒有去看,沒有產生任何的影響。這就很糟糕了。”第四,要有“記錄與搶救精神”。他說:“我們現在是丟掉了很多東西。有血有肉的東西,沒有人記錄下來。我覺得這方面我們景德鎮(zhèn)人要去搶救。像戴榮華,他可能有很多東西想要說,對藝術創(chuàng)作都有很多自己的看法,這些東西是書本上沒有的,是他的創(chuàng)作經驗和人生經歷。姚永康也是,非常有思想有見解,但是現在都聽不到啦!他們過世之后才覺得沒有記錄下來很可惜。”(上述引文詳見口述)
劉遠長也認為當今理論研究遇到了很多困難,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他認為“現在景德鎮(zhèn)理論的發(fā)展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這個需要教育部門、政府部門能給予立項,理論的發(fā)展才得以保障”;第二個困難是當今“誘惑太多”,許多人不愿做理論,他說“再者景德鎮(zhèn)的創(chuàng)作太活躍,誘惑太多,搞理論的需要耐得下性子、甘于寂寞,腳踏實地地去做。”
1.5 當代藝術創(chuàng)作如何才能出“精品”或“經典”
劉遠長認為,當代藝術創(chuàng)作要想創(chuàng)作出經典之作,不僅僅是藝術家個人的事情,同時“需要政府、高校、研究院應該有責任與擔當,每個部門分析自己的任務。”他認為,“哪些地方該怎么樣?哪些地方不該怎么樣?比如說行會,你要統計目前各個行業(yè)如:粉彩、古彩、雕塑分別有多少家,協會的會長應該做哪些工作?一年中要組織多少展覽,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展覽或者展銷。現在行政手段弱化了,但是有經濟手段。運作展覽的錢從哪里來?一個是要有項目,另一個是自己籌,第三個,你自己出錢。”(引自口述)
在創(chuàng)作經典過程中,尤其要發(fā)揮政府與行業(yè)的作用,打造“品牌”,確立“品牌意識”。他認為,“政府說要與世界對話,怎么對話?那我們就要鼓勵做品牌、做高檔產品,限制能源消耗大的產品。要提倡低消耗,那么在藝術的要求上就要精益求精,充分發(fā)揮自己的腦力和手藝,科學技術、藝術構思的部分要強化,不要去侵權和仿冒別人的創(chuàng)作品牌意識就是貨真價實,事實上就是一個知識產權的問題。我們可以用法律的手段來約束企業(yè)。也要用思想文化的觀點來啟導企業(yè),因為陶瓷藝術本來就是一個高尚的行業(yè)。”(引自口述)
1.6 藝術教育要將“認識”和“德育”放在重要位置上
關于“認識教育”,他認為“應該把‘認識’放在學校教育重要的位置上。因為你要求他創(chuàng)新,提示他注意手上功夫,但他根本不聽你的。一進入學校,學生都以為自己會做藝術家,所以你要說做手藝,人家都不滿意。做學生就應該腳踏實地、扎扎實實,在一個行業(yè)上學點東西,走出一條路來,要有這樣一種思想才行。”(引自口述)
關于“德育教育”,他認為:“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應該把“德”擺在第一位。我們不能培養(yǎng)一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學校是否名牌就看你這個學校教育出的人是怎樣的。我有的時候就說我是景德鎮(zhèn)陶瓷學院畢業(yè)的,我在這里起了什么作用?我做了什么事?我應該怎么做?”(引自口述)。
2 雕塑瓷廠與景德鎮(zhèn)陶瓷藝術文化
2.1 關于雕塑瓷廠的創(chuàng)建及簡況
雕塑瓷廠于一九五五年由市工藝合作社、雕塑合作社和美術合作社合并而成“工藝美術瓷廠”,一九五六年更名為雕塑瓷廠,廠址在新廠“金雞嶺”,設有“成型車間”與“彩繪車間”,建廠之初有人員“兩百多人”,主要是以職工家屬、文教家屬為主。劉回憶說:“雕塑瓷是有工藝要求的,因此它由工藝社來帶動,工藝社是占龍昇等人,它是以帶學徒的形式從事工藝生產的。家屬進廠里來,要對其進行培訓,還要考試。學徒要三年才能畢業(yè)。”(引自口述)
人員規(guī)模發(fā)展及構成:“一九五五年建廠的時候有兩百多人,一九五七年的時候大約就有五百人了,一九五八年的時候大約就有七百多人。人員過多,后來又精簡下放。人員最多的時候是在改革開放之后了,大約有1400多人。改革開放的前期,廠里進來了很多人。主要有六批:第一批是廠里職工多子女,但無子女參加工作的照顧兒子,兒子可以來廠里上班。第二批是家屬工轉正,開始家屬工不足,他們工作了這么多年也轉正了。第三批是帶子傳藝,那些技術好的,你的兒子可以帶進來,但是這些人員要經過考試。第四個是退休頂替,你退休了,你兒子也可以來。第五個是病殘退休,你有病可以提前退休,你的兒子也可以來。第六個是‘批條子’。”(引自口述)
生產機構設置:建廠之初便設有“成型車間”與“彩繪車間”,他回憶說:“成型車間有倒?jié){、修坯、翻模、印坯等幾塊,比如說他倒了漿,我來修坯。這兩個完全不同的工序,但我一直要把這個坯修完,就是一個人做一段事情,工序較長,但相對來說比較獨立。”(引自口述)
一九六二年設“創(chuàng)作組”,一九六四年改成“創(chuàng)研室”。另外還有專門負責泥料、顏色釉配方的小組。剛開始是一個人,后來是一個小組,不同的東西要用不同的裝飾。
市場與銷售: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起初主要是代表國家的“出口公司”接單,他們直接到廠里來訂貨,瓷廠并不直接面對市場。
“文革”后期,“隨著市場的慢慢放開”,“除了出口公司的訂單,自己也會做一些作品走內銷市場,像古玩市場也會來訂貨。我們的產品也在南昌友誼商店、工藝品商店售賣,所以后來除了一個出口公司還有一個內銷公司。內銷公司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有一個景德鎮(zhèn)陶瓷駐地的聯絡部,聯絡部展銷的是景德鎮(zhèn)十大瓷廠生產的陶瓷。在這些地方有些市民要買景德鎮(zhèn)的陶瓷,就買三四級品的陶瓷。一二級的銷售到國外去了,外銷有不要的也會走內銷市場。每個級別價位不同,假如一級品是一百的話,那么三四級只占一二級品 70%的價,五級品就只占 50%的價,價格相差很大。”(引自口述)
一九七八年,出口公司取消后就自己找市場,進行企業(yè)市場化改革。他回憶說“一九七八年出口公司就沒了,我們基本上就自己找市場,當時我們廠有1400多人,負擔也很重。在市場上也面臨著很多競爭,個體戶跟你爭原料、爭市場、爭人才,個體戶一般拼幾個人就可以做東西,于是他們就到雕塑瓷廠去請幾個工人,晚上去幫他做東西,廠里事實上就已經空了,所以必須要轉型。”(引自口述)
上世紀九十年代轉為市場經濟之后,“廠里的人員結構也要轉。要根據市場經濟來調節(jié)自己的內部結構,干部要能上能下,工人要能進能出,當時有句叫法:打破鐵飯碗,砸爛鐵腳椅。臨時去抓訂單,談生意。”(引自口述)
2.2 雕塑瓷廠與傳統“行會”、“會館”的異同
新中國成立前,景德鎮(zhèn)的陶瓷生產“主要是一家一戶的作坊”,每個行業(yè)都有“行會”,“比如說做雕塑瓷,那就是雕塑瓷行業(yè),行會有行業(yè)性質的管理。市場經濟一定離不開行業(yè)協會”。行會之外,還有“會館”。“會館跟協會還有不同,比如說福建會館,它是所有在景德鎮(zhèn)的這個行業(yè)中的福建人參加的。有做箱器的、有做圓器的、也有繪畫的,但都是福建人。”(引自口述)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國有化改造運動中成立的包括“雕塑瓷廠”在內的“十大瓷廠”主要是“行政管理”,財產為國家和集體所有,從而取消了私有作坊。
劉遠長認為盡管有上述區(qū)別,他仍然認為,“其實無論是行業(yè)管理還是行政管理,都很好。初級的行政管理基本上是按照官窯的標準來做。那個時候工人要考試,產品有嚴格的質量標準,出了質量問題是要受處罰的,甚至要去勞動改造。那個時候工人的勞動素質、就業(yè)素質、勞動態(tài)度都非常好。當時有一定的政治工作,幾乎天天晚上要進行政治學習,加強自身的思想教育。領導帶頭勞動、帶頭工作,用毛澤東思想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剛分到雕塑瓷廠的時候,早上還要到后面的山上去讀書,讀毛澤東選集。那個時候這種政治思想要求的非常嚴格,所以凝聚力比較強”(引自口述)。
2.3 關于雕塑瓷廠對景德鎮(zhèn)陶瓷生產與藝術創(chuàng)作的貢獻
第一,最早引進梭式窯,提高了產能,降低了成本。劉遠長回憶說,“我當廠長的時候引進了梭式窯、慢慢的搞明清園租賃承包等等。引進梭式窯我們應該是最早的。那時候是全市第一家從澳大利亞引進的。梭式窯有五大優(yōu)點:速度快、能耗少、質量好、無污染、垃圾減少了。”(引自口述)
第二,為出口創(chuàng)匯貢獻很大。他回憶說,“景德鎮(zhèn)的陶瓷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的創(chuàng)匯收入貢獻很大,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可出口的東西很少,那個時候國家需要外匯,唯有景德鎮(zhèn)的陶瓷可以換取,整個景德鎮(zhèn)的陶瓷出口量都很大,用泥土換外匯。”“在一九八二年有一個指標是100萬美金,光雕塑瓷廠一年就這么多,它的內銷是不算在內的。我接管的時候大約是1000萬美金,比如說你做的產品大的可能有多少個?你做小的可能有多少個,有時候會做些小玩具、小動物,它的量就比較多。在一九八零年雕塑瓷廠獲得了“散花牌”輕工業(yè)部頒發(fā)的質量獎,當時就是因為雕塑瓷廠的產品換匯率比較高,出口量比較大,單件產品的價值比較高,而且藝術的造型比較好。”(引自口述)
第三,材料研發(fā)上,雕塑瓷廠在“泥料配置”與“顏色釉配方”上有很大貢獻。他回憶稱,“我們有專門負責泥料、顏色釉配方的小組。剛開始是一個人,后來是一個小組。不同的東西要用不同的配方,比如說我們做毛主席像,有1.7米、1.8米的,1.8米的成品的話泥料就要做到2米多,作品一只腳站著,這個姿態(tài)一般的泥巴是不行的,那么就有工人專門配泥料。再比如說顏色釉,我們這里有一個姓金的師傅,他就端一盤子試片給你看,反復去實驗。比如烏金釉,烏金釉開始是會流動的,而且還有點帶黃色。后來他千錘百煉變成了全市最好的烏金釉,又薄又黑又不流,師傅的名字好像是叫金工圣,今天店面的位置大概在東二路。還有無光黑釉,當時我們跟他提出來說最好烏金釉不發(fā)亮,那時我創(chuàng)作了一只水牛,我的要求是顏色釉不發(fā)亮又很薄,薄到坯體上我刻劃的牛毛一根一根的給體現出來,后來他就實驗出了無光黑。我們廠各個部門都很獨立,有自己的工藝師傅。”(引自口述)
3 結 語
景德鎮(zhèn)雕塑瓷廠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組建,主要從事陶瓷雕塑的創(chuàng)作與生產,其產品出口到東南亞各個國家,在計劃經濟時代為國家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外匯收入。它也是景德鎮(zhèn)最早引進梭式窯的陶瓷單位,改變了傳統的燒窯模式,節(jié)約了能源、減少了環(huán)境污染。它在泥料、釉料上做了眾多的工藝性的突破研發(fā)。它的存在見證了從新中國成立之后景德鎮(zhèn)陶瓷藝術的發(fā)展之路,其中有著老一輩藝術家的艱辛和努力,也有著眾多的曲折和收獲。我們需要對那段歷史銘記于心,才能更好地珍惜今天自由、開放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
在此次采訪中,劉遠長大師還暢談了當下的陶瓷藝術以及藝術教育的發(fā)展,景德鎮(zhèn)的陶瓷雕塑或者陶瓷藝術由于能源的短缺,應該從粗放型向精細型方向發(fā)展,要多創(chuàng)作經典的精品之作,減少原材料的浪費。當然藝術發(fā)展不僅指實踐創(chuàng)作,還包括藝術理論的發(fā)展,實踐要有理論指導,才能明確方向,而景德鎮(zhèn)在陶瓷理論的發(fā)展方面是稍微欠缺的。同時也要注重德育在陶瓷藝術教育中的重要性,做到樹德立人從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