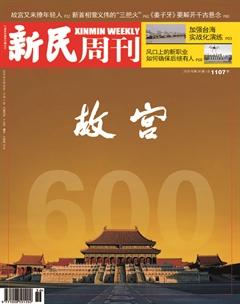光影折疊:故事內外的紫禁城
馬棟予

編者按
陰狠卻又美艷的妖后、悲劇氣質的末代皇帝;戲說里的插科打諢、宮斗里的愛恨欲孽;紀錄片帶來的清流、綜藝節目裹挾的熱鬧……背景舞臺,只有一個:曾經的紫禁城。光影折疊,屏幕上的故宮,另具獨到的美感。
1980:故宮影像再現的黃金時代
香港導演李翰祥的“清宮三部曲”,是1980至1990年代大銀幕上最重要的故宮影像。《火燒圓明園》(1983)、《垂簾聽政》(1983)與《一代妖后》(1989)在稗官演義、歷史正劇和香港成熟商業劇情片模式之間尋找到了一種平衡。也為我們留下了紫禁城重要的影像。紫禁城的乾清宮等巍峨的建筑始終是男權正統的象征,但是在著名商業導演李翰祥的鏡頭下,反而是后宮、頤和園、圓明園這些能夠容納女性的空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細膩體現。尤其是集合了劉曉慶和鞏俐兩大影后的《一代妖后》中對于慈禧內闈生活的“艷情化”呈現,堪稱1980和1990年代之交華語商業電影暗流中涌動的歷史艷色。李翰祥也以境外導演的視角,接續了“南下香港”影人的血脈與大陸久違的歷史演義題材,這也造就了“清宮三部曲”當時在內地與港臺、海外獲得巨大的成功。彼時剛飾演過王熙鳳、武則天等重要女性人物形象的劉曉慶飾演的慈禧也成為了華語影史的經典形象。《一代妖后》中劉曉慶那陰狠駭人卻又美艷動人的形象將紫禁城的陰郁氣氛表現到了極致,宮廷與女人從此在中國影視史留下重要的一幕。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中國影視史上紫禁城與女性人物結緣的重要原點。
名導貝納爾多·貝托魯奇執導的《末代皇帝》(1987)也是一個非常具有象征意義的事件。幼年的溥儀身著龍袍在太和殿前的影像構成的電影海報恐怕在世界影史上都有一席之地。古老的東方帝國的宮廷被西方藝術家的新銳攝影機開啟了門戶,一個極具東方主義色彩的時刻。尊龍陰柔俊美的形象和氣質則更加激發了西方世界的想象。很多影迷后來不明白的是,為什么《末代皇帝》會充斥著一種令人費解的魅力。整個20世紀是全球史不斷勾連的歷史,而我們對于紫禁城的想象和理解也是透過“西洋鏡”完成的。影像作為一種技術本來就是西方現代世界的產物。《末代皇帝》中的紫禁城是貝托魯奇最摯愛的凝視對象,比起略顯妖魔化的慈禧、濃墨重彩的溥儀等人物,故宮仿佛是貝托魯奇鏡頭下中華帝國的女子,在歷史的面紗下誘惑而動人。許多人都無法解釋這部異國制作的片子所激發的我們的深層感受。《末代皇帝》其實還提出了許多電影理論甚至文化理論的重要命題,比如《末代皇帝》是不是一種“世界電影”,影像是否是跨民族國家的?《末代皇帝》展示了以西方“透視法”呈現紫禁城的可能性。也表明了西方文藝中的“成長敘事”(一個男人的成長故事)與中國史傳傳統(帝王本紀)的交匯、融合之可能,《末代皇帝》提供了一種跨越文化傳統的敘事可能。而這種在1980年代就展現出來的格局與氣象,是令三十年后李亞鵬、黃奕、蔣勤勤領銜主演的電視劇版本的《末代皇妃》(2004)相形見絀的。

《火燒圓明園》劇照。
混沌、躁動但卻充滿能量的1980年代也在故宮的身上留下了時光的痕跡,中與西、古與今在80年代競相喧鬧。
于中國大陸成長起來的第四代、第五代導演們大多從表現鄉土題材起步,因此重要的歷史題材要到1990年以后才逐漸開始復興。而清宮題材這一波復蘇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將在電視小熒屏中走進千家萬戶,也開始為逐漸升溫的大眾文化熱潮做了鋪墊。
1990年代:影視并蒂齊開
導演郭寶昌的《日落紫禁城》(1998)在世紀之交的清宮正劇大潮中投下女性主義的色彩。在《大宅門》中精彩的男人群戲對比之下,《日落紫禁城》的女人戲無疑更加動人。劉若英飾演宮女,斯琴高娃飾演慈禧和蔣雯麗飾演珍妃也是難得一見的演員陣容。由于采用小宮女的視角來展現大清帝國的衰亡時刻,后宮就無疑成為最重要的表現領域。《日落紫禁城》對慈禧、珍妃等充滿爭議的人物進行了當代文化史上重要的梳理和謄寫,劇本扎實細致,以至于對于很多80后、90后文青來說,《日落紫禁城》(而不是《似水年華》或《人間四月天》)才是寶島“奶茶”劉若英在大陸最初的驚鴻一瞥。

《蒼穹之昂》劇照。
與《日落紫禁城》并駕齊驅的是《康熙微服私訪記》(1997)、《還珠格格》(1998)、《鐵齒銅牙紀曉嵐》(2001)、《格格要出嫁》(2002)、尤小剛“清宮秘史”系列等一大波清宮戲說系列與清宮文化被大眾消費的開始。
而到了2000年代第一個十年將要結束時,彼時尚未執導《后宮·如懿傳》的導演汪俊已經貢獻了他的口碑之作《蒼穹之昴》(2010)。日本著名女演員“阿信”田中裕子來飾演中國近代史爭議人物慈禧彰顯了邁入21世紀的中國影視業跨國合作的萌芽(當時有一批外籍演員如韓國女演員張娜拉、“人魚小姐”張瑞希等來中國發展,甚至出演歷史題材劇作的例子)。《蒼穹之昴》的服裝道具和化妝造型在當時收獲了很大的贊譽 (田中裕子的慈禧造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認可),將故宮點綴得更為鮮活。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是后來現象級的《甄嬛傳》劇組實際上接手了《蒼穹之昴》的服道化并在其基礎上發展了《甄嬛傳》的服道化。
2010+ 女頻時代的宮墻
宮斗題材雖然較早可以被追溯到TVB港劇《金枝欲孽》(2004),但是真正成為現象級的話題則仍然要數鄭曉龍打造的《后宮·甄嬛傳》(2011)。接下來飽受爭議的《宮》系列(《宮鎖心玉》、《宮鎖珠簾》、《宮鎖連城》等)則因為在視覺上的粗制濫造(“影樓風”、“阿寶色”等蔑稱甚至成為網絡流行詞)而廣受詬病。顯然觀眾對影視城再造的宮廷景色和不夠考究的服道化很不買賬。
這么一來《延禧攻略》(2018)的高口碑就不僅是“于正制作”或“橫店制造”(或許是某種意義上的中國制造)的口碑逆襲。于正不僅僅在服化道方面將傳統技藝(多種“非遺”級別傳統技藝的呈現)與西方時尚界主導的“色譜”中的莫蘭迪色進行了完美融合,也讓宮廷劇與網播形式、彈幕觀看形式有效結合。要知道《甄嬛傳》(2011)的播出和火爆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于傳統的電視播放,而《延禧攻略》這一更具有“網游格調”的名字則是流媒體平臺時代(愛奇藝)的“爆款”。稍后的《后宮·如懿傳》在流量意義上的挫敗則主要歸因于《延禧攻略》對于時代脈搏更精準的把握。當然《如懿傳》在視覺上的最初承諾也沒有兌現給觀眾,使得即使有電影大片級別的卡司陣容也不敵小妮子“魏瓔珞”的奇襲。

宮斗劇鼻祖級的《金枝欲孽》海報。
某種意義上來說,由于《如懿傳》在美術上的折中態度,使得《如懿傳》在視覺呈現上凌亂不堪,觀眾很難抓到視覺的重點,每一幅都是絢爛的背景,大制作、大導演、大演員,三大模式難免讓觀眾視覺疲勞。這讓《如懿傳》最終沒能夠在影像美學的層面留下令人深刻的印象。《如懿傳》中的紫禁城,猶如一只剛刷完新漆的大船,龐大但是臃腫,厚重但是輕率。《如懿傳》在美學上的尷尬有點類似于李少紅和葉錦添在2010版《紅樓夢》中遭遇的滑鐵盧。
紀錄故宮“清流”
2012年首播的《故宮100——看見看不見的故宮》,以100個章節的方式顯微鏡式地呈現了故宮的建筑美學,英文譯為紫禁城的100個不朽形象(100 timeless images of the forbidden city),這是央視紀錄片頻道的重磅力作,也是從建筑本體的角度對故宮所做的最充滿敬意的影像描繪。《故宮100》構思精巧,以極小的篇幅展現故宮的幽微之美,至今都十分值得觀眾重溫。

《我在故宮修文物》實際上更是描繪一種特殊的情感態度,一種面對歷史與文化之溫情與敬意。
紀錄片作為一種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題材,也和文學領域的“非虛構”一樣成為2010年代以來勢頭最猛的敘事方式。《我在故宮修文物》(2016,英文名:紫禁城中的大師們)可以稱之為2010年代中國紀錄片井噴期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式作品。相比《故宮100》仍然將故宮建筑、歷史作為核心的呈現對象,《我在故宮修文物》則“以人寫景”。用十分抒情的方式刻畫了一個曾經的無名群體。從表面來看,《我在故宮修文物》無疑是在歌頌新時代所推崇的“匠人精神”,但實際上更是描繪一種特殊的情感態度,一種面對歷史與文化之溫情與敬意。《我在故宮修文物》堪稱“指尖上的中國匠人”,讓故宮迷們從另一個維度品咂故宮之味。“我在故宮修文物”也回應了進入改革開放第四個十年的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訴求:故宮不再是禁地,而是中國凡人在其間實現創造美學的場域。某種意義上《我在故宮修文物》也昭示了中國文學(化)從大敘事轉向小敘事的過程,一如文學大師沈從文從“文學時代”走入“文物研究時代”,最終成為文物研究的巨人。
彈幕流動的宮墻?
《故宮上新啦》(2019)是中國新綜藝時代的產物,將明星真人秀、文創產業、觀眾互動、故宮文化呈現巧妙地融為一爐,大打“中國創新”、“中國制造”牌。《故宮上新啦》與2019年宮墻色號口紅,故宮角樓餐廳等一眾商業新秀展現了中國網紅經濟的熱潮——故宮已經成為了文創時代、電商時代網紅經濟的新角力場。與《故宮上新了》中接受觀眾檢驗的款款文創商品一樣,我們也一直好奇著紫禁城還將以怎樣的形式在虛擬視覺世界被呈現。
光影繼續
2019年末故宮的煙花表演,2019年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接任單霽翔成為故宮新掌門,再到2020年初“故宮郭美美”驅車故宮私人游引發網民討伐,故宮仍然牽動著中國人的心。對于故宮的美學呈現事實上也是一種權力的體現,是普通中國人對美學民主的情感寄托。
2020年是中國和世界歷史的分水嶺,紫禁城仍然是中國這一文明體中重要的政治符號和文化符號。相信故宮600年大展之際,短視頻、vlog將會成為最為重要的光影再現方式,而故宮將依舊佇立在歷史與當下、真實與虛幻的中間地帶,散發著其獨特的光暈。
紫禁城六百年,影視藝術的發展不過只有百余年,但是光影的魅力卻在于能夠以萬花筒般的多重視角將其折疊、再現。光影重塑了故宮的形象,因為現代人的視覺經驗早已是被媒介化了的,對于一般的外國人甚至中國人來說,我們對于故宮的認識多少依靠著光影;而故宮同時也給予了光影,因為光影必須有所附麗,才得以顯現其存在的美感。故宮的光影折疊告訴我們,藝術必須附著歷史才得以實現其存在,沒有無歷史的藝術,亦沒有無藝術的歷史,光影變換之間,便是歷史滄桑,便是展眼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