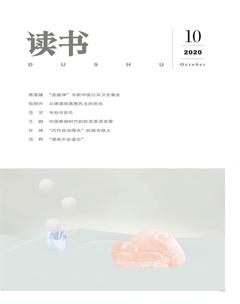書到老來方可著
李成晴
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
提起《論語》,不同學人的腦海中,大約都會有不同的圖景定格著,在筆者而言,則是《論語·憲問》篇里這個孔子擊磬于衛的現場。當言不盡意,只剩肉身與金石在廣袤的時空之下相擊撞的時候,孔子在想些什么?聲聲磬音,傳達出的是孔子的低喟,或詠嘆。
有從容沉思的時空條件,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盡管可能像朱熹那樣欣賞荷蕢者聽音知意的高明,卻也懊惱于荷蕢者順世知止的言說唐突地打破了孔子沉靜的思考,甚至逼著孔子不得不說出“果哉”的感嘆。孔子是有憂思的,憂患意識更是儒家思想的一個深刻內里,劉東先生將其概括為“一種本體的‘憂”,也可稱作無名之憂、自律之憂或自尋之憂。對于種種偶然性的擔憂,“對于人生的死生大限,暗自生出無名的悲壯、蒼涼與微茫”,會引導學人不得不去思考這樣一種“困境中的生命意識”,進而為自我的“晚期寫作”給出解決方案——這也許可以看作劉東繼《天邊有一塊烏云》之后要寫《前期與后期》的內在動因。
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劉東一直保持著對《論語》文本的研讀,而心得的紙面落實,直到二0一八年的《天邊有一塊烏云》才初見系統的發攄。至于新近出版的《前期與后期》,更是時時處處在孔子與儒學的思域中展開論說。在這兩本書中,劉東基于自身所尋得的思想史研究的獨特視角,對人文學者的“二度生命”“兩個世界”做出了詮解,憂時傷世,溢于楮墨之間。
劉東常提到《論語》中的兩段故實:其一,是孔子對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生命周期的把握,這是一種基于價值理性的人生進階,而不是對自然生命的客觀歸納;其二,是孔子“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刪述六經的使命承當,這是孔子在人生后期所尋得的身心安頓,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劉東看來,這兩段故實都是和人文學者的“后期”(或稱“晚期”)有關:在學術生命的后期,人文學者會自然有一種與時間競走的意識,“只要有晚期,他都有這個緊迫感”。對于劉東而言,《前期與后期》是他在進入“后期寫作”之后,山中看山,從而做出的對人文學者生命周期的省思。“我們循著這種角度,既可以見出在‘生命周期中紛至的困擾、固有的節奏和獨到的徹悟,也可以領略分屬于不同人生階段的特定心氣、風格和語調。”(《前期與后期》,2頁)
在儒家關于生命周期的理解中,悅樂精神和憂患意識可以說是聯袂并轡的。于是,我們既同感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百年俱是可憐人”的深深喟嘆,也景慕于“不知老之將至”“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意氣縱橫。在《前期與后期》中,劉東思考的是“仁者”在“泰山其頹”之前的生命安頓。他創造性地解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古話,指出對一位人文學者而言,其中的“天”,很重要的一個維度便是“一個人能享有多少‘天年”。人生天地之間,在天邊有一塊烏云的不確定性之下,奮袂自強,抵抗流年,自具一種拔山蓋世的浩然之氣。而若真要寫出像馬一浮“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那樣的詩句,則更需要理性的剛毅與堅卓,“不啻把‘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學精神,化作了一種個人的尊嚴與抗爭”(《前期與后期》,41頁)。
在《真想讀一點馬一浮》(《浮世繪》,一九九七年)中,劉東談到前期的陳寅恪不過“清俊書生”,而后期的陳寅恪肖像之矜重、孤憤,“簡直就是中夏文明整個命運的寫照”。可以說,至少在二十年以前,劉東便開始思考“前期與后期”這個問題了。而到了二00五年的“知天命”之年,劉東則于年末放慢腳步,回顧了彼時彼地所處的“盛年”:“如果我們把人生比作歌劇,那么自己眼下正在經歷的這個盛年,也就正好比人生的詠嘆之年。”(《這一年,我的詠嘆之年》)在這一年,是他清楚地意識到生命限制的年歲,也是一個最接近于超越自我極限的年歲。二0一二年,在《未竟的后期:(歐游心影錄)之后的梁啟超》一文中,劉東指出梁啟超“后期”自我變法、退而著書的重要內因,便是“追溯到自幼就潛伏在他心中的、來自孔子生平的強大暗示”。四年前,在《引子與回旋》中,劉東更是在與訪客的談話中有過一段“六十述懷”:“六十歲的他有一種‘晚期寫作的緊迫感,也有一種‘拔劍四顧心茫然的失落。”(《不能任由中國文化凋敝下去》)循著對“后期”問題的一貫思考,二0一八年,《天邊有一塊烏云》著成。劉東在書中說:“既然轉瞬間也已到了‘晚期寫作的階段,自己的這次充滿緊迫感的寫作,就絕不是為了什么與時俱進的‘創新,恰恰相反,倒是為了退回到孔子當年的語境中,以便同情地理解他原有的問題意識。”至于今年新版的《前期與后期》,則直面“充滿挑戰與變數的晚期”,重新去體認了“三不朽”的文化傳統,聲倡學人應具備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做足準備、高歌猛進、發揮出畢生積聚的學術功力,從而涵養一個創造性的“后期”(《前期與后期》,169頁)。
許多人會認為,就像古語所說的“人書俱老”那樣,“后期寫作”也許具有瓜熟蒂落的自如自在。可實際上,劉東在書中指出,“后期寫作”恰恰也是充滿了病痛、危機與不確定性,而人文學者正是要在這樣一朵烏云的不確定性之下,擔荷起弘揚傳統與價值的使命感。這讓人自然地聯想到薩義德的《論晚期風格》,乃至更早的阿多諾的《貝多芬的晚期風格》。阿多諾曾指出,人文藝術晚期風格的成熟,并不像果實基于生命韻律的甜美成熟,反而,它是具有“褶皺”的,甚至是“毀滅性”的;更進一步,那是作者對于平庸的時代精神的憎恨和鄙棄。黃德海于此概括說,這就是過去中國士人所講的“苦詞未圓熟”(《知識結構變更或衰年變法》)。薩義德所論述的晚期風格,主要還是跡近“以偏概全”的西方世界的“晚期”:晚(lateless),并非指暮年(senility),因為生涯的中期,就會有“晚期風格的影子或種子”;更多的,是指一種“不適時”甚至是“不合時宜”(untimely)——這種“不合時宜”與之前的作品構成一種“本質有異的風格”。是故,劉東并未將薩義德意義上的“晚期”取來作為本書運思的范導。本書認可的是,貝多芬式的“義無反顧”“我行我素”的緊迫感,這種面對“天邊烏云”的緊迫感對后世的啟發作用都是深遠的,無論西東。
由此,我們也可發現人文學者“后期寫作”的另一重特性,那就是“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后期寫作未必是與現世的人對話,其筆觸直指綿遠的未來,誠如陳寅恪所謂“托末契于后生”“后世相知有別傳”。后期寫作,不再是為了贊美,甚至也已不再為了認同,就像本書評價貝多芬的最后高峰那樣:“它不僅不再打算取悅大家的耳朵,也不再愿意具有明澈的表象了。”(《前期與后期》,83頁)作為比較,劉東提到了李商隱的《錦瑟》——一首有著非花非霧、說不清道不明的憂患意識的詩作。
那么,當如何才能辨察“前期”與“后期”看似清晰實則模糊的邊界呢?在《前期與后期》中,劉東認為,理解一位人文學者的方法是“沿著他特定的生命軌跡,找到劃定其‘前期與后期的那個分界點”(《前期與后期》,14頁)。本書曾提及中國傳統士人的“衰年變法”現象,如果我們對這四個字詳加思繹的話,也許可以體會到,“衰年變法”之說,對人文學者的前期、后期作品并未下軒輊之判,前期可以風神俊朗,后期可以澹泊高遠;前期寫作可以自得天機,后期寫作可以老到渾成;前期與后期也可以一以貫之,誠如章學誠所言:“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文史通義·博約中》)一位人文學者的前期、后期之界,有時與時代變局有著密切的聯系,就像陳寅恪那樣,陸鍵東的一部《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已然界畫出了陳寅恪轉向后期寫作的二十年。陳寅恪在晚年數次引用項蓮生的牢騷之語:“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的“后期”,于時世看似無益,實則是內心慎重思考后的果決實踐。這種基于內在理路而生發出的對“前期”“后期”判定的清明智慧,中西皆不乏其例。本書枚舉了柏拉圖《對話錄》、海德格爾、朱子晚年定論等例,認為在是否應該有一個后期的問題上,關鍵是需要“跟從自己內心的感覺,并表現出作為思想者的真誠與膽略”(《前期與后期》,56頁)。如果循此加以延展與擴充的話,我們甚至可以說,在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心理中,對“后期”邊界的探尋,實際蔚為風氣:少作不存、五十以前不著書、折節讀書之說,自然屢見載籍;述而不作、得意忘言,不在寫作的“無窮盲動”中,弄丟了正在寫作的這個“自我”,皆是歷代士人以“不被決定”的堅毅精神來守護學術生命的行止(《未被決定的“例外”》)。當然,還可補“嫁娶既畢,敕斷家事”一語。這句話尤其可以見出,古代士人站在儒家倫常與釋道修為的邊沿上,對另一種為己之學“后期”深造的自覺期待。盧照鄰在《附馬都尉喬君集序》中轉述了喬師望“婚嫁已畢,欲就金丹”的志愿,實際也內聚了一層“齊家”與“敕斷家事”不可調和的張力。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劉東曾數次談到美國攀巖大師亞歷克斯·霍諾德的紀錄片《徒手攀巖》(Free Solo),后期寫作,又何嘗不是去攀爬一座“壁立千仞”的酋長峰?就像盧卡契,為自己生命晚期擬定了三卷本《審美特性》的宏大寫作計劃;但在寫完第一卷后,他又轉向了更為高遠的《倫理學》。梅洛·龐蒂的語言學論著深受索緒爾的影響,在晚年的后期寫作中,他思考的核心層面卻又回歸到早年所深思的索緒爾“差異意義”理論之中。在某種意義上,后期寫作堪稱是個人心史意義上的尤利西斯之旅——在曲折險阻之中一往無前。后期寫作,無論是音樂還是文辭,往往會浸入一種始于悲壯、收于悲憫的寬容感,前者如貝多芬式的激越與自由,后者如施特勞斯式的翛然與中和。我讀《前期與后期》,也從中獲得了這樣的閱讀體驗。
在知天命的前一年,黃宗羲在《喜鄒文江至得沈眉生消息》一詩中寫道:“書到老來方可著,交從亂后不多人。”上聯典型且到位地寫出了中國古儒的“生命節奏”,黃宗羲也以自身為示范,讓后學一窺什么是漸老漸熟的“生命打開”。劉東初見此詩時,唏噓良久,于是請書家抄錄,裱掛書桌之側,霜晨月夕,與之晤對。
(《前期與后期》,劉東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二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