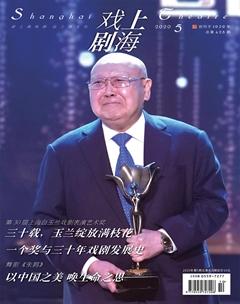以中國之美 喚生命之思
潘凱玲

民族舞劇《朱鹮》自2014年首演至今,已超過250場演出,屢獲嘉獎,屢受好評。作品始終傳達著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理念,帶著中國美學特點踏足國內外,啟示世人對生命抱有愛與敬畏。2020年8月,在上海大劇院22周年落成紀念活動中,上海歌舞團攜舞劇《朱鹮》再度上演。最先經歷一場疫情的中國,此時對生命的關照更深入人心,這支親切的“生命之舞”再度上演更引發了人們深思與感慨。
一、“物化”的生命符號與當代闡釋
無論《朱鹮》演過多少場次,走過多少舞臺,總能給觀眾留下一個感受:美!這種美不僅在特別的舞姿、優美的色彩或浪漫的情誼,還在那內在的生命表達,將生命的理想符號化,化在那舉手投足之間,撥動著觀眾的心弦。而這生命的符號蘊含的是中國的美學,又以當代視角闡釋中國自古以來天人合一的哲思。
徐復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提出,中國藝術精神的主體即莊子的道的精神。倘若直接宣稱這個以當代人視角講述的穿越古今的故事深受莊子的“道”家哲學思想影響,未免太過牽強。但不得不說,《朱鹮》審美指向所包含自然界、社會、生存空間、藝術化的人生及體悟等等,都可以從中國美學的血脈中窺見莊子“物化”論的古今影響。
1.形神兼備,物我合一
“翩翩兮朱鷺,來泛春塘棲綠樹。羽毛如剪色如染,遠飛欲下雙翅斂。”唐代詩人張籍在《樂府雜曲·鼓吹曲詞·朱鷺》曲詞中對朱鹮(朱鷺)的外貌與動態描寫,折射出中國古人對這種“吉祥之鳥”的欣賞與觀望。舞劇中對朱鹮的形象塑造充分吸收了詞中的情境,化于舞動之中。而作為全劇重中之重的角色,朱鹮的美感體現又不限于此。莊子學說的一個特點是不以“形”為基準,而應“離形達神”。舞蹈的特殊表現力使人“成為”朱鹮時就已經“離形”,而為達朱鹮的“神”又擬其“形”進以達“神”,形神兼備的朱鹮之美在全劇的上篇中就綻放得淋漓盡致。
色彩上,她們身著潔白的體羽,裙尾綴著一抹偏黃的粉色,腳掌綴著鮮艷的赤紅色,與樸素的灰衣樵夫形成鮮明的色差,是那般圣潔純美。造型上,她們一側臂膀展開,手搭額前,一手環于腰間,挺拔身姿,經典又高貴的姿態令人賞心悅目。構圖上,鹮群不乏整齊的“一”字隊形、變化著不同方向的“V”字隊形等線性構圖與迂回的路徑,在浪漫的雙人舞中也不時擺出人與鹮的對稱造型。動態上,“朱鹮”們頭部快捷顫動,體羽抖動,雙腳之間互相摩擦,半腳掌上行進的小碎步,膝蓋高高拎起、腳掌穩穩落地的步伐……這一切始于對真實朱鹮的自然模仿,進而化為富有生命活力的舞蹈動作語言,才能有白羽展開的翩翩飛舞,有泛春塘時的媚態慢行,有斂收翅膀的輕盈步態,還有欣喜時的頭部顫動……
朱鹮的靈動在與人的近距離互動中盡顯生命力量、化作生命的符號。它既指向一個珍貴鳥類族群的生息,又標志著大自然一切具有靈性的生命。除了朱鹮的形態之美,上篇還有一處美就在于描寫古時候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之態。為凸顯這份和諧美感,劇中更是將大自然的使者——朱鹮與人之間創設了“人仙之戀”的千古浪漫情節。那份愛意在雙人舞中娓娓道來,在賦予朱鹮以神性的同時,又在發展至人鹮群體雙人舞的高潮中升華為人與鹮的物我無間、天人合一的境地。那貫穿全劇的一片鹮羽,是人與鹮邂逅的信物,代表著他們美好的曾經。
也許,正是因為朱鹮作為全劇最光鮮亮麗的核心角色,讓劇中那素色的“人類”形象顯得有所淡化。但細想其中,“人”在這部劇中與朱鹮的互動可謂十分密切且頻繁,而全劇的情感邏輯也是建立于“樵夫”“保護者”這個穿越古今和年齡的“人”的情感走向而鋪設。之所以帶來一種“人”的形象淡化,原因有三:一是劇中“人”與觀眾——現實“人”的視角極其接近,虛擬“人”帶著現實“人”穿越古今,看到朱鹮的命運變化時的內心感受高度一致。二是當觀者站在劇中角色的視角時,是更容易“忘我”的,觀者能感受到其內心的情感變化時,就容易弱化對其形象本身的關注。三是編者為“帶入感”設置的虛擬“人”與現實“人”的共性,而淡化了這一虛擬“人”的個性,男主人公唯一區別于舞臺上“身份模糊”的其他“人類”的個性就在于他始終保有對朱鹮的特殊情感和聯系。盡管如此,形象的淡化感并不能減輕他的重要性,能真正把那份對朱鹮的關注和愛帶入的正是以這樣一個能拉近人與朱鹮距離的特殊角色。
2.哀而不怨,立象以盡意
若沒有上篇朱鹮那極致的美和與人浪漫的愛,又怎會有下篇那沉重的痛和深切的悔呢?當觀眾還沉醉在那神話般的愛情邂逅中期待人與朱鹮再續前緣時,下篇卻揭開了沉重陰暗的畫面,一步一步將那份美好連同人心一并撕碎。
對現實的拷問,可以是某種控訴,可以是某種吶喊,而“朱鹮”卻以生命的隕落來警示世人,引發反思。下篇中的塑造哀而不怨,立象以盡意。真實世界的朱鹮到寒冷冬季,也是準備繁育的時節,會由體內黑色的分泌物隨羽毛梳理染于上半身,直到繁育期結束。但在舞劇中,那工業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給朱鹮們帶來生存威脅的語境下,這上身羽毛的灰黑色賦予了更多當代語義:它不只代表著嚴峻的棲息環境帶來的寒冷,還是在朱鹮面對環境逼迫、生存威脅、繁衍不能,卻無能為力而“心生寒冷”的外化符號。
不僅如此,朱鹮們此時身姿不再挺拔,步伐不再靈巧,飛翔不再富有活力。努力尋找故人的“鹮仙”在惡劣環境中褪去了尾巴的一抹粉色,潔白的身體變成了灰色,在令人窒息的環境中奄奄一息,掙扎著尋找那個故人——保護者。朱鹮們賴以生存的森林已經壓縮到一片陰暗的樹叢里,狹小環境無情地一一奪去她們原本高貴的生命,無助的朱鹮們在生命的威脅面前眼看伙伴一個又一個死去,那只原本靈活淘氣的小朱鹮再遇故人時已殘缺不全,盡管步伐艱難,她仍然嘗試與保護者嬉弄玩耍,死神卻再次無情地奪去這鮮活的小生命,讓它活活死在“人”的懷里。一段寒冷凄美的獨舞之后,鹮仙已是隔著玻璃的標本,這一切成為幾乎無法挽回的事實。
從審美效果上看,《朱鹮》的劇情安排或許還有不足,還有更能引起深刻共鳴的表達方式。如在開篇第一幕中,將農耕場景與朱鹮的出場場景各自獨立,或許能夠凸顯朱鹮作為圣鳥的光環,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拉開了人與朱鹮的距離。倘若能像于平教授說的那樣,如果在人類的勞作場景中不時有朱鹮掠過,而人類又在勞作中體現出與朱鹮的親昵,其實也是隨后“人”與“鹮”之情的必要鋪墊。這樣既避免了第一場的單調,又在視覺上更帶入神與物游、天人合一的意境。再如結尾處,若將老年保護者對朱鹮復活、生靈復蘇的美好想象再折回到他在博物館中看著那靜靜的標本,這最后幻想的破滅所帶來的無盡遺憾更會讓人痛徹心扉。盡管如此,全劇的結尾仍然選擇符合中國傳統審美的近似圓滿的結局,在那“標本”呈現中激發出遺憾與心碎的同時卻不拘泥于此,而是在主人公想象的復蘇世界里,將更多珍惜之情和美好期待延續。最后的畫面中,朱鹮高舉空中又開始步步前行,青少年們那份仰望,象征著未來珍惜世間生命的美好憧憬。幕后語講述真實世界朱鹮的保護與復蘇,以樂觀現實鼓舞人心。
曾有人將《朱鹮》比作“中國的《天鵝湖》”,無疑是因為形式美感上有著浪漫主義氣質的共性,以及兩部劇同是以神話了鳥類與人類的結緣這一相似感的影響。尤其在上篇,著重描寫了鹮仙與樵夫的愛情片段,將人與自然的和諧美好落于一段引人注目的愛情邂逅,并以一片白羽毛作為“信物”勾連前世今生,以及那類似于“四小天鵝”的“六小朱鹮”。然而,但凡對兩部作品有著更深入了解的觀眾都明白,無論從作品內涵、主題立意、審美取向,還是形象的塑造,二者都并不存在可比性。主演朱潔靜在訪談中說道:“我發現它(朱鹮)比我能夠認識到的孔雀和天鵝有更多可挖的人文含義和現實意義。”盡管《朱鹮》在形式上有著浪漫主義氣質,但它展現的還是中國的美學精神和當代思考。
二、傳播生命理想,期盼世人永銘記
上海歌舞團團長陳飛華對于《朱鹮》作品的初衷和期待,是懷揣一份社會責任感的,他在訪談中說:“2010年上海世博會日本館的主題就是朱鹮,參觀了半個小時,給我一個很強烈的沖擊……地球的生命實際上是共通的,《朱鹮》這樣一種選題有現實意義的關照。”盡管如此,藝術的創作依然不能直白地打著保護環境的口號或某種直面的諷刺,而是選擇以美的方式,激起人性中對美好事物的愛意,又以悲劇的方式激發出人對美好逝去的惋惜,從而促使人們更深切地對生命以愛和珍惜。這一切藝術理想,化在作品中的舉手投足之間,化在生命的靈動中,以藝術的真實牽動觀眾的心靈。
感化人的內心,才能促使人們自發地尋找因果關系,將珍惜生命與現實中的環保理念相聯系。這也就自然而然激發觀眾在觀看《朱鹮》后產生投身環保事業的沖動。尤其在日本——這個把朱鹮視為“皇室圣鳥”,對它有著更特殊情感的國度,《朱鹮》無疑激起了他們的重重回憶和無限情懷。也正是因為這份“朱鹮”情懷,這份對生命的愛與珍惜,它甚至是帶著東方的美學、東方的記憶,和那自古以來“人間大愛”的東方共同理想,喚醒了中日的共同話題,使得朱鹮在2014于日本斬獲眾多舞劇迷的同時,使當時中日僵持至冰點的關系初次得以“溶解”。
嚴格地說,受到日本觀眾的認可還不能稱作受到西方的認可。要知道,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就古時的農耕文明來說,日本與中國本就同根同源,而朱鹮這一生物角色本就融合了中日文化的血脈。但這份人與自然的現實命運不僅是中國的現實題材,對于今天的世界,對于整個地球來說都是現實問題,是人類要共同面對的。因此,《朱鹮》不再只是一些人口中所謂的“小小舞臺劇”。近看,它選材“東方寶石”形象,為它譜寫生命之舞,講好一個共同的東方故事,是一份中日友好對話的答卷。往遠看,它還提出了人與自然關系的世界共同話題,是一份人類與自然世界同生共死的情懷,體現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命運共同體的中國精神與胸懷。
從最初到日本巡演那一場融冰之旅,到踏足美國備受歡迎,《朱鹮》切實實現了“講好中國故事”。事實上,講中國故事是形式,是手段,不是根本目的,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講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故事,為的是展現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審美,傳達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哲學。《朱鹮》用藝術感化世界,呼吁全人類對世間生命的珍惜與愛護,它不僅僅是受到世界認可的藝術作品,還是中國文化、中國精神的傳播者,更是保護人類家園的呼吁者和“形象大使”。
盡管《朱鹮》的結構還有待改進,盡管它的表現方式還有不足,但在當下人們迫切需要這樣一個生命主題的藝術作品回歸舞臺時,是不是有缺點已經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尤其經歷了疫情之災,《朱鹮》的演員們此時也無不帶著更深的情懷、更投入地演繹這場“生命之舞”。主演王佳俊說:“很開心疫情好轉之后,我們演出的第一個舞劇就是《朱鹮》,我有一種強烈的情感想告訴大家:地球不止屬于人類,是屬于地球上所有生物的。”
或許經歷這場疫情,更多人開始反思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乃至人對于大自然應抱有的感恩與敬重。這場疫情無疑是受傷的大自然在掙扎中給全人類帶來的一次教訓。愿人類能在這場災難過后,為了曾經的失去,將這份愛銘記于心,對世間每一份生命永久地珍惜。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1] 張立敏,張蘇,張飄月. 莊子物化論的當代價值——從藝術精神視角讀解《莊子》[J].中國道教. 2020(01):56-61
[2]于平. 生命的哀歌,生態的盼——大型民族舞劇《朱鹮》觀后[J]. 舞蹈.2017(08):26-28
[3]朱良志 中國藝術的生命精神[M] 安徽文藝出版社 2020:237
[4]梁戈邏. 渺萬里層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誰去——觀舞劇《朱鹮》有感[J].上海藝術評論.2016(04):2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