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安全:被撕裂的全球社會
榮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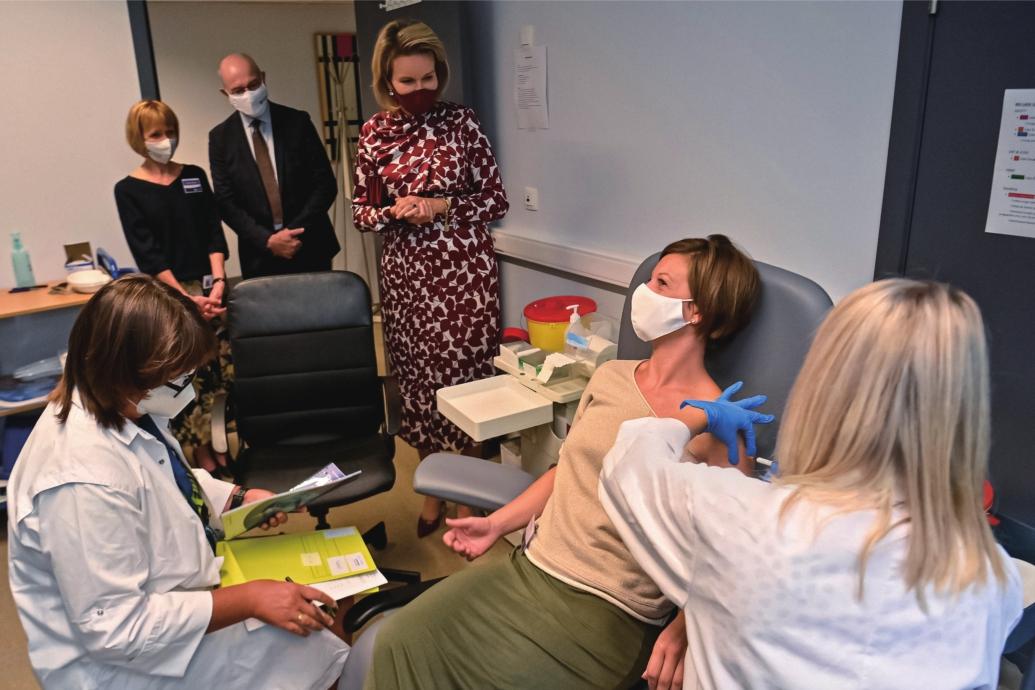
在遍及美國的街頭示威活動中,“疫苗造成死亡”的標語隨處可見。可以說,這是COVID-19大流行之際,西方社會普遍面臨的緊迫挑戰:帶有數字化特征的抗議運動,傳播了更進一步的偏見,動員了錯誤的力量,召喚起了更多的“排外”情緒。
對疫苗的恐懼其來有自,這些深藏于歷史和心靈里的懷疑,往往在每一次大流行病的暴發期,以各種或隱晦或直白的表達傳遞出來。看起來,在現代社會中,有一些問題僅憑科學答案并不能讓人們滿意。
疫苗黑幕?
至少16世紀以來,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就已經有故意感染天花水泡中的物質以促進產生自然免疫力的做法。18世紀初,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的一個非洲奴隸那里學到了這個辦法,企圖在美國大力推廣。盡管這種做法能降低疫病的死亡率,但馬瑟成了被時人大加嘲笑的對象。
疫苗接種在18世紀末由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推廣。詹納發現了接種牛痘的重大意義—既可以降低接種“人痘”的風險,又可以達到對天花免疫的效果。接種牛痘的技術相當成功,他把牛痘接種在自己兒子身上,算得上是免疫接種的第一個成功案例。不過,反對者氣勢洶洶,不僅罵詹納道德敗壞,還認為這是“對傳統秩序進行外國式攻擊”。
在一幅創作于1802年的英國漫畫里,畫家顯然判斷使用牛痘接種天花疫苗會產生奇怪的副作用—接種者的耳朵、鼻孔、嘴巴和身體,都紛紛鉆出一只只憨態可掬的微型牛。
和兩個世紀前一樣,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疫苗。十幾年前,不少英國人拒絕接種MMR疫苗,接種減少后,麻疹、腮腺炎和風疹的患病數量快速上升,于2012年達到高峰,光是麻疹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就有2000多例。《柳葉刀》3月份的一篇文章指出,有26%的法國人聲稱不會選擇接種COVID-19疫苗。另一篇5月份的文章指出,有14%的美國成人拒絕接種COVID-19疫苗。
不過,和兩個世紀前不一樣的是,近年的反疫苗運動不是因為對科學一無所知,而是因為對科學一知半解。
2016年的紀錄片《疫苗黑幕:從隱瞞到災難》揭發了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疫苗丑聞”。2014年,生物學家布萊恩·胡克(Brian Hooker)發表了對2004年CDC一項研究數據的重新分析,稱該機構隱瞞了一項發現,即非洲裔美國男孩在36個月大之前接受MMR(麻疹、腮腺炎、風疹)疫苗接種,增加了罹患自閉癥譜系障礙的可能性。同時,胡克提供了與CDC科學家威廉·湯普森(該研究的作者之一)對話的秘密錄音,以支持自己的論點。
該片引發了愈演愈烈的反疫苗運動,疫苗的副作用、不良反應成為“原罪”,不少人亦為此拒絕接種疫苗。生理學家和科學作家喬納森·伯曼(Jonathan Berman)通過對這一問題的持續研究跟進,表示影片中胡克的分析方法存在嚴重的缺陷,他不斷撰文希望為疫苗“正名”,由此,一場反“反疫苗運動”也開展了起來。
過去的10年里,已經有很多專業與可讀性兼具的科普書籍出版,來解釋疫苗的科學原理及其必要性。比如保羅·奧菲特的《死亡選擇》(2010)、記者塞斯·努欽的《病毒恐慌》(2011)、醫生大衛·伊薩克的《擊敗死亡的掌握》(2019)、彼得·霍特茲的《疫苗沒有引發自閉癥》(即將出版)。據悉人類學家海蒂·拉爾森也在今年加入了科普大軍,對反疫苗運動進行大力反駁。
疫苗是安全的。從結果上看,有很多扎實的數字可以證明。
不過,這些反駁“疫苗有害”的聲浪,似乎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從歐洲到北美,疫苗導致其他疾病、死亡的故事長了翅膀一樣四處流傳,盡管疫苗接種的歷史是一部現代科學進步史,但同時也是社會陰謀論的最佳溫床。疫苗的反對者并沒有全盤否定科學,而是認真地選擇了大量存在錯誤和偏見的信息,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繭房”。
嚴格監管
疫苗是安全的。
從結果上看,有很多扎實的數字可以證明。
根據美國CDC的評估,在20年的時間里,疫苗使超過2100萬病人免于住院治療,73.2名兒童免于死亡。
同時,因疫苗出現問題而索賠的現象比例很低。美國“國家疫苗傷害補償計劃”已經發起了30年,向美國人提供了數十億劑疫苗。在此期間,大約有2萬人提出了索賠。迄今為止,在已評估的1.8萬項聲明中,大約有三分之二被駁回,因為證據表明疫苗沒有造成索賠人所稱的“傷害”。
大約有6600項索賠得到了賠償。如果該計劃找不到足夠證據證明疫苗造成任何傷害,據負責官員透露,只要索賠人的醫療信息、癥狀產生的時機與官方名單上的描述相符,他們通常會給人們賠償。
近年來,許多索賠都與流感疫苗有關。流感疫苗幾乎占了目前下發的所有疫苗劑量的一半。從2006年到2017年,也就是“國家疫苗傷害補償計劃”目前有數據可查的時期,已經分發了超過15億劑流感疫苗。在此期間,提出的傷害索賠不到3500件,每百萬劑大約有2件索賠。

這些主張索賠的情況,許多與疫苗本身的質量無關,而是與肩部疼痛有關。因為成年人常常要在肩膀和上臂進行注射,因此一些物理性的疼痛和不適,往往被誤認為疫苗所致。好在公共衛生官員也正在組織更完善的衛生服務培訓,盡量減少接種者的不適。
和兩個世紀前不一樣的是,近年的反疫苗運動不是因為對科學一無所知,而是因為對科學一知半解。
從程序上看,擁有嚴格的、跟蹤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監管程序和臨床試驗,疫苗已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醫療產品之一。
疫苗開發和生產中的監管因素相當嚴格,包括使用具有明確特征的、具有明確來源的均質原材料,以及包括細胞在內的可接受質量;對生產過程進行充分驗證,以證明同樣的條件對于不同的生產批次是可重現的;證明生產一致性,達到監管部門的要求;對目標人群中產品的作用進行充分的售前和售后監控。
臨床測試在確定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起著關鍵作用。無論中外,三期臨床一般耗時最長,耗資最大。這是疫苗獲批上市前最后階段的試驗,也是最重要的試驗階段,接種疫苗的試驗組還要和沒有接種疫苗的試驗組直接進行比較。也有一些疫苗可以不進行臨床試驗,但極其稀少。像被CDC認定為A類病菌(危害性最高級別)的炭疽桿菌,不可能在人身上進行試驗,所以FDA對該疫苗豁免臨床試驗。當然一般民眾也無需接種此類疫苗,美國也主要是用于戰略儲備。
在批準后的階段,疫苗的安全性會被持續監測。美國FDA要求所有的疫苗生產商在每個批次的疫苗上市之前要提交樣品,并且,疫苗生產商還要將他們對疫苗安全性、效力和純度的檢測結果同時提交給FDA。
今年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疫苗的第一批臨床試驗已于3月份啟動,目前已經開展了20余項試驗,諸如阿斯利康(AstraZeneca)、摩德納(Moderna)、諾華(Novavax)和輝瑞(Pfizer)等醫藥公司開始分享樂觀的早期結果:到目前為止,它們僅檢測到志愿者身上有輕度或中度癥狀,而沒有嚴重的副作用。志愿者還產生了冠狀病毒抗體,在某些情況下,前者的抗體比染病后恢復的人產生的抗體還要多。
但是,早期結果的樂觀,未必代表著三期試驗結果的樂觀。
因為三期試驗需要長期的、大型的隨機對照,疫苗或安慰劑會發放給成千上萬的人,并等待他們在現實世界中和病毒“迎頭相撞”,還要再觀察他們每個人表現出來的復雜各異的反應。
可以說,經歷過這些一波三折的連續考驗,上市的疫苗才能保證安全。
警惕“提速”
然而,和一部分反疫苗運動參與者的擔憂一樣,在經濟停擺、社會困頓等火燒眉毛的情況下,有些疫苗可能在沒通過三期試驗的情況下就被匆忙上市。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8月上旬宣布俄羅斯已經批準了一種冠狀病毒疫苗上市,不少疫苗專家對此感到擔憂。俄羅斯并未提供新疫苗已經通過大規模臨床試驗的證據,并試圖跳過三期試驗直接投放。關鍵是,和給病人使用實驗藥物不同,疫苗的對象是無數個健康人,所以,疫苗必須保持非常高的安全標準,否則,樣本量如此巨大的情況下,什么樣的罕見副作用都會出現。
6月的時候,俄羅斯聯邦衛生部Gamaleya流行病學和微生物研究所注冊了一項名為Gam-COVID-Vac Lyo疫苗的聯合一期和二期試驗。研究人員計劃對38名志愿者進行測試。
和一部分反疫苗運動參與者的擔憂一樣,在經濟停擺、社會困頓等火燒眉毛的情況下,有些疫苗可能在沒通過三期試驗的情況下就被匆忙上市。
俄羅斯當局稱,這種疫苗是由帶有冠狀病毒基因的腺病毒制成的,類似于阿斯利康和強生公司在其疫苗中使用的基因。腺病毒疫苗采用的是新技術:世界首個腺病毒疫苗剛剛于6月獲批用于預防埃博拉病毒。
隨后俄羅斯官員聲稱疫苗將迅速投入生產。普京的宣布相當于宣告了疫苗的“面世”。但是,該研究所從未發布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試驗數據。俄羅斯衛生部長米哈伊爾·穆拉什科說:“所有志愿者都產生了高滴度的抗COVID-19抗體。同時,他們都沒有嚴重的免疫并發癥。”
紐約市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的病毒學家約翰·摩爾這樣評價:“普京沒有疫苗,他只是在發表政治聲明。”
政治決策“入侵”科學領域,并強迫疫苗遵守政治性的規定,而不是醫學安全意義上的標準,相當危險。一方面,其有很大的概率影響健康人的身體健康,并造成更為嚴重和難以預料的醫學后果;一方面,其會促使人們更加不信任“疫苗”的安全性,從而無法用有效的醫學手段保護自己。
換句話說,疫苗的上市時間不是不能“縮短”,但它應該在安全加速的意義上操作,而不是由于政治性的目的被直接忽略。比如監管機構提前準備好每批疫苗的試驗數據結果,以便生產者更快拿到數據,調整方案,縮短不同階段試驗之間的時間。
更復雜的是,就算有些步驟可以“提速”,但掣肘的因素還是沒法略過。直到今天,研究人員還沒有完全徹底搞清楚SARS-CoV-2如何繞開人類的免疫系統、使人類生病。除此之外,疫苗生產商正在測試幾乎所有可用于COVID-19疫苗的技術,一些舊技術似乎可用,但其中有一部分從未被批準用于人類的任何疾病。
免疫接種是21世紀20年代“社會矛盾”的最有力體現之一。在這里,我們既能看到固守偏見的人們如何以科學之名反對科學,也能看到數字社交媒體如何持續強化偏見,也能看到一種類似面對“電車難題”的集體性選擇,又能看到政府權威的滑落和失效,還能發現集體的碎片化如何使公共利益分崩離析。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到底是疫苗撕裂了我們的社會,還是社會本來已經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