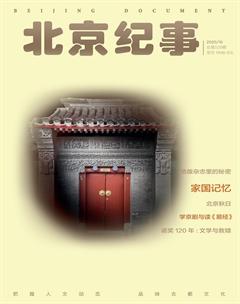通州的新城往事
劉維嘉

我的家鄉——通州,已經有2200多年的歷史,且遠近聞名。
像我這樣一直生活在通州古城的人有很多,我們扎根于古城的城墻腳下,與大運河、通州塔息息相通、日日相伴。
如今的家鄉,正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已過花甲之年的我,時不時地總會想起諸多至今難忘的事情。也許,不少老通州人也和我一樣,還記著這些吧。
難忘的電影院
過去年間,縣城有通縣禮堂、通縣電影院、工人俱樂部、新通劇場和東方影劇院。
通縣禮堂(1993年7月重建落成后改名為通州會堂)位于新華大街北側多福巷36號,是縣里舉行大型會議的場所,這里不定期演節目和放電影。
通縣電影院位于西海子公園東側,日偽時期是私人戲院,通縣解放后曾經是冀東十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禮堂,1950年初改建為電影院(曾經歷過翻建和功能改造)至今。老百姓習慣把通縣電影院稱呼為西海子電影院。工人俱樂部位于通縣體育場西側,由通縣總工會管理。新通劇場位于新華大街21號,設有觀眾席1060個,有池座和廊座,既能演戲也能放電影。建于1988年的東方影劇院位于車站路14號,在東方化工廠職工家屬院西側。

通州會堂
通縣電影院、工人俱樂部、新通劇場這3家電影院門前的墻壁上都有巨幅電影宣傳海報,是由美工站在腳手架上,一筆又一筆畫的。后來,通縣電影管理站(1981年更名為通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在閘橋東南角的墻上也設置了巨幅電影宣傳海報并定期更換。
這3家電影院最初放映的是黑白電影,后來有了彩色電影,電影銀幕也由小銀幕換成了寬銀幕。從早到晚,每天放映的電影都不重樣。有了新電影,3家電影院門前會排起買票的長隊。新電影在這3家電影院按順序先后放映,時常是這家電影院剛剛放映完新電影,負責跑片的工作人員馬上拿著電影拷貝,騎自行車送到下一個電影院。
買電影票很方便,這3家電影院門口都有賣票的窗口。為了方便居民購票,通縣電影管理站在閘橋東南角的位置設置了售票亭,老百姓可以就近買到3家電影院的票。過了幾年,售票亭搬到了通州百貨商場東門外。
通縣電影管理站還把3家電影院每月放映的電影用彩色大字報紙印成單子,定期發到機關、學校、工廠、醫院。這些單位把組織職工看電影作為職工福利之一,經常組織職工看電影,特別是有了新電影。此外,中小學也常組織學生觀看電影。中小學生買的都是學生票,每張票5分錢,而成人票是1毛5分錢。
我在縣五金廠工作期間,廠里每月都發電影票,每次廠里發電影票,已經搞好對象的年輕人,常找老職工要票。老職工也常常把電影票留給他們,如果電影票的座位號不挨著,他們再找人換成座位挨著的,不論男女,都把和對象一起看電影當成了最幸福、最甜蜜的事情。一張普通的電影票,不知促成了多少人喜結良緣。
走街串巷的百貨車
在通縣南北大街和胡同里,人們經常看到一位年齡在50歲上下,個頭不太高的男售貨員推著百貨車,搖著撥浪鼓賣百貨。
百貨車是用一輛雙輪車改裝的,車身很長很寬,車的上面平放著木頭做的貨柜,貨柜分成好些格子,小格子上面蓋著折疊玻璃小門,里面分別放著針頭線腦、鉛筆文具、煙袋和煙袋嘴、線襪鞋墊、繡花線和子母扣、松緊帶和女孩子跳繩用的橡皮筋。大格子里放著棉布被單、秋衣秋褲。車上還有搪瓷臉盆、暖壺、球鞋和現在已經看不到的黑面條絨布懶漢鞋。在貨柜中間部位的兩側固定著木頭豎桿,上面有橫桿,橫桿上掛著雞毛撣子、腰帶,東西可不少。

磨剪子搶菜刀(鐵快板)
這位售貨員的臉上總是掛著熱情、和藹的微笑。遇到胡同里的熟人就打打招呼。
他經常推著百貨車從回民胡同西口進來,走不遠,就把車停在較寬敞的路邊,拿起撥浪鼓有節奏地搖起來。人們在院子深處一聽到熟悉的撥浪鼓音,就知道賣百貨的來了,最先從院子里跑出來的是小孩子們。大姑娘小媳婦來到車前,一般都是買一些頭卡子、繡花針、繡花線、雪花膏什么的。老太太一般買一些頂針、扣子、針線。抽煙的人有的買煙嘴,但更多的是買卷煙紙和打火石。在百貨車前,總是圍滿了人,有買東西的,也有和他聊天的。小孩子們常常圍著百貨車轉來轉去,嬉戲打鬧。
遇到沒人來買東西的時候,他就收起撥浪鼓,推起百貨車,一邊和旁邊的人點頭打招呼,一邊邁著穩健的腳步向胡同里面走去,撥浪鼓的聲音隨著他的身影一起漸漸走向胡同的深處。
有一天傍晚,我去西海子電影院看電影,當我穿過鼓樓走不遠,看到了那輛熟悉的百貨車。百貨車停在路東一家小百貨店門前,那個賣百貨的人和一個頭發花白、高個兒的男售貨員正在從百貨車上往店里搬貨物。這家百貨店門臉不大,商店玻璃上寫著醒目的“國營”等字。通縣三中、靳家胡同小學、貢院小學、司空分署街小學的學生常到這個百貨店買鉛筆和作業本等文具。常站柜臺的就是那個高個兒的售貨員。
1981年1月,我參加了政協通縣第五屆委員會會議。在會上,我見到了那個賣百貨的高個兒售貨員,這才知道他叫王敬亭。據記載,王敬亭自1959年10月至1990年5月,曾經歷任政協北京市通州區第三屆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北京市通縣第四、五、六、七屆委員會副主席。20世紀80年代曾擔任民建通縣支部主任。
搖鈴收垃圾的馬車
20世紀60年代,縣城居民的生活垃圾都是每天集中清運,生活垃圾主要是爐灰。常來回民胡同收垃圾的是一輛橡膠轱轆馬車,馬車車廂的槽幫有一尺多高,趕大車的是個40歲左右的壯漢子。駕轅的騾子腦門上拴著紅布條,騾子的脖子下系著拴有紅布條的小鈴鐺,馬車往前走的時候,騾子脖子下邊的小鈴鐺會發出有節奏的叮當聲。
趕大車的壯漢子來胡同里清運垃圾,從不吆喝,而是用木柄手搖銅鈴鐺的搖晃聲招呼人們來倒垃圾。木柄手搖銅鈴由手柄、銅鈴和擊錘三部分組成。木柄與銅鈴鐺之間拴著紅布,搖晃起來能發出很大的聲響,胡同里的人家一聽到鈴鐺聲,都紛紛端著裝垃圾的盆或木箱子來倒垃圾。住在大雜院的人們常端著垃圾盆或垃圾木箱,早早來到大門口,等著運垃圾的。

掏糞工(來自網絡)
那時候居民的生活垃圾比較單一,比如家里的碎玻璃、玻璃瓶子、豬牛羊骨頭攢起來,集中賣到東關的廢品收購站;家里吃冬瓜,冬瓜皮、冬瓜子晾曬干了,司空分署街東口對面有收購店收購;家里種了蓖麻,蓖麻子能到北大街的收購店賣錢,還能得到食用油票。居民喜歡在空地養雞、兔子,摘下的菜葉子、菜幫子、菜根都用來喂雞喂兔,雞糞、兔子糞都用來給院里種的轉日蓮、蔬菜上肥。這些也許都是生活垃圾比較單一的因由吧。
辛勤的掏糞工
過去,縣城里的大糞都是掏糞工定期來掏,每撥兒來五六個人。起初的掏糞車是橡膠轱轆馬車,馬車上邊固定著長方形木質大糞罐,大糞罐上刷的綠漆已經褪色,上邊有直徑一尺多的倒糞口,尾部下方有出糞口,用木頭塞子堵著。掏糞工去胡同掏大糞時,都把大糞桶放到糞車上,跟在車后邊走。到了掏糞的地方,他們背起大糞桶去掏糞,出來的時候,車把式把一塊寬木板斜搭在車上,掏糞工背著大糞桶從木板登上大糞車,把大糞倒進大糞罐內。后來,大糞車換成了汽車,汽車上有橢圓形鐵質大糞罐。掏糞工去掏大糞時,都站在大糞罐靠前的兩側。大糞桶和大糞勺等必備的掏糞工具分別放在大糞罐后方兩側。這種大糞車不用登梯爬高了,掏糞工把裝滿大糞的大糞桶放到車后的搖臂上,再抓起搖把,把大糞桶提起來,大糞就倒進了大糞罐。再后來,大糞車變成用橡膠管子抽糞,有效減輕了掏糞工的勞動強度。
在沒有抽糞汽車之前,掏糞工都用大糞桶掏糞。大糞桶有一米多高,圓錐形狀,桶口大,桶底小,上粗下細,從上到下箍著五六道鐵箍。掏糞工都身穿勞動布工作服,肩膀戴著厚厚的圓墊子。
掏大糞是個體力活,大糞桶裝滿糞便后有100多斤重。掏糞的工具有兩種:一個是橡膠糞勺,用來掏糞便;一個是小吊桶,用于舀大糞湯。到了冬天,還要帶上長把鐵勺子和扁鏟,扁鏟安在長長的木棍上,用于鏟茅坑里結冰的大糞,然后再用鐵勺子?出來,裝入大糞桶。掏糞工在掏大糞時彎曲著雙腿,熟練地把裝滿大糞的糞桶背上肩膀,再背起沉重的大糞桶慢慢站起來走向停在胡同的大糞車。他們一路上身體往前傾著,邁著沉穩的腳步,大糞湯也在糞桶里晃蕩著,經常濺到地上,也濺到他們的身上。
回民胡同有好幾個大雜院,38號大雜院住的人最多,有十幾戶人家。院子最后一排房的后面有個公用廁所,從大門口到廁所來回要走100多米,上下十幾個臺階。掏糞工每次來掏大糞忙活完,還要安排人拿著鐵锨和笤帚回到院子里,用鐵锨從甬道邊上鏟土,沿著甬道把灑在地上的大糞湯進行覆蓋,然后用笤帚打掃干凈,把那些臟土搓到鐵锨上,倒入大糞桶里帶走,這才和工友們一起乘車,到下一處繼續忙活。就這樣,他們每天走街串巷,默默地重復著這樣的勞作,用一人臟換來萬家凈。
掏糞工都是通縣清潔隊的職工,單位在趙登禹大街北邊路東。曾經涌現出清潔隊長張起旺這位北京市勞動模范,還有不少受到縣里表彰的人。張起旺曾在通縣禮堂參加通縣勞動模范表彰大會并登臺作過報告。
這些都是根植在老通州人記憶深處的人文標志,更是通州古城歲月的記憶、時代的痕跡和歷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