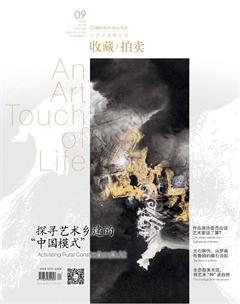卷起流動與開放的浪潮
林紫鳴



激浪派(Fluxus)誕生于動蕩的20世紀60年代,興盛于70年代,這場運動與美國的波普藝術和極簡主義、歐洲的照相寫實主義在時間線上重合,但是它的內涵顯得更加復雜,因為它不止于藝術形式的表達,還涉及了集體創作的可能性,以藝術概念的革新和文化融合帶來一場跨越地理與文化隔閡的浪潮。反藝術,不拘一格
拉丁文詞語“Fluxus”是英文“Flux”的字根,意為“流動、溢出”。這名稱是由立陶宛出生的美國當代藝術家喬治·馬修納斯(Geage MQciunos)提出。他主張激浪派是為了“在藝術中卷起革命的浪潮,去推動生活藝術、反藝術”。他認為,所有人都能創造藝術,而非只是評論家、業余藝術愛好者與專業人士的專利。
激浪派的藝術家們使用各種手段結合和創作材料,提倡“自己動手”去創作,他們經常上演隨機表演,并使用手頭上的任何材料制作藝術品。激浪派是流動的,開放的,與觀眾合作的,主張樸素和反商業主義。“偶然”在激浪派的作品中起著重要作用,另外,幽默也是重要的元素。
盡管在概念上,激浪派是回應并延續了達達主義的精神,但是,比起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激浪派更加強調集體協作的可能性。因此,激浪派沒有個具體的風格特征,更加準確來說,激浪派并不是個“藝術流派”,而是一場跨地理、跨文化、跨領域的精神性集體協作的活動——他們當中有藝術家、經濟學家、化學家、音樂家和舞蹈家;他們來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亞洲、歐洲和北美;他們藝術創作形式是不被規限的,音樂會、節慶、戲劇、表演以及動作等都能成為激浪派的藝術行為。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使激浪派的風格種類多元且開放,它亦揭示著藝術家是如何在那樣一個動蕩的環境中產生對話,并開創出一條新的脈絡。
開創者喬治·馬修納斯和約翰凱奇
激浪派的誕生與兩個人密切相關,他們是互為補充的關系。將時間的指針撥回到1952年8月29日,美國作曲家約翰·凱奇在紐約馬弗力克音樂廳里舉辦個人新曲鋼琴演奏會,并發布了他最為實驗和破格的嘗試((4分33秒》(433”)。《4分33秒》是音樂史上最大膽、最破格的嘗試,因為它是一首完全無聲的樂曲,是約翰·凱奇對實驗音樂的探索,也是環境音樂(Ambierft)作品的開始。
《4分33秒》并不是指約翰·凱奇在臺上靜坐的4分33秒,而是他在后臺設置的錄音將這4分33秒之內,錄下了臺下所有的聲音而構成了不同凡響的《4分33秒》,他解釋道:“無論我們在哪里,我們聽到的都是噪音。我們常常忽視它,因為它會擾亂我們。但當沉默寂靜時,我們發現它的迷人。”
與觀眾的互動是《4分33秒》尤為重要的一環:4分33秒的這段時間內,觀眾的聽力在這個安靜的環境將會變得異常敏銳,而他們發出的所有聲響都將會被記錄,成為作品的一部分。
約翰·凱奇的這個創造性的舉動深深影響了喬治·馬修納斯。馬修納斯(George MociunQs)被認為是激浪派的開創者。馬修納斯的主要角色是一個組織者、活動者。事實上,在激浪派被馬修納斯命名和組織起來之前,“激浪派”式的組織已在小群,但全球性藝術家和作曲家中展開。
事實上,其時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在藝術界里稱霸一方,激浪派運動的出現正是藝術家們開始背棄抽象表現主義的關鍵時刻。受作曲家約翰·凱奇19571959年間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的教學影響,一批先鋒藝術家開始自己的藝術創作,他們開始探索如偶發(chQnce opreofions)、日常生活的審美,以及一種新的藝術主體性(subieclMly)。
超越和突破
白南準
白南準生于韓國首爾,1950年因戰爭隨家人到日本,并到東京大學學習音樂史、藝術史和哲學。由于深受德國音樂家勛伯格的影響,他于1956年赴德國慕尼黑大學就讀,并在這一時期結識美國前衛藝術家約翰·凱奇和激浪派的創始人之一馬修納斯。
1959年開始,白南準在德國以作曲家和影像藝術家的身份從事演藝工作。他深受約翰·凱奇和杜尚的影響,并持續創作與約翰凱奇相關的藝術作品。白南準第一次向約翰·凱奇致敬是1960年,他在舞臺上首先演奏了肖邦的作品,表現出明顯的厭惡感,然后跳入一架敞開的鋼琴中,之后他走進觀眾席,拿著剪刀走到約翰·凱奇面前,剪掉了他的領帶——昭示著白南準不僅對約翰凱奇充滿敬意,他還有超越約翰·凱奇的野心。對于白南準來說,這個“剪領帶”的行為還有自我獨立的意味。
1963年,白南準在德國烏波塔帕納斯藝廊舉辦首個藝術展:“電子音樂
電子電視”電視機成為了他標志性的藝術載體,這種形式也讓他在藝術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禪之電視》《電視時鐘》《磁鐵電視》《電視椅》都是白南準在創作初期以電視作為主體媒介的裝置作品。在他的展覽中,電視機像是被隨意擱置在地板上的,沒有方向和秩序感,電視屏幕卻在播出同樣的節目。因為屏幕上的圖像被壓縮成平行線狀,畫面不同步,所以處于運動之中的圖像總是飄忽不定,似乎有一種溢出屏幕的感覺。當時,白南準已經掌握了相關的電子技術,開始應用水平電磁波振動、垂直電磁波振動與同步脈沖的聲波來改變、影響圖像。
白南準并沒有像約翰·凱奇一樣主要集中在進行音樂創作,他把目光投向了新媒體藝術當中。他將約翰·凱奇對音樂的架構上的創新精神滲透到自我的藝術創造中,他的作品融合了傳統音樂所能帶來的聲音效果和加入了動態的視覺效果,并逐步以電視機作為媒介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對電視機中的部件進行改造、結構和重新組合。以前瞻性的創作去啟發人們思考電子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白南準是第一個探索媒介實際性質的人,著眼于電子產品必須提供的潛力。
女性主義的興起
作為一個開放的多元的團體,激浪派內里有許多女性藝術家,并在各種媒體和不同內容中貢獻作品。她們的作品通常是與女性的性別身份有關,對其進行試驗性和表演性的工作,從而創造強大的女性存在感。這種創作的內核一直存在于激浪派的內部:小野洋子的《切片》探索了衣服之于身體的內涵。1964年,小野洋子在卡耐基誦廳第一次表演了她最為出名的行為藝術作品《切片》:她坐在臺上,身邊放著一把剪刀,隨機挑選觀眾上去一點一點剪掉她的衣服,直到她完全赤裸。很多人或許會好奇,這樣做算什么行為藝術?有什么意義?其實小野洋子的行為,并非只是讓人剪下衣服而已,還有著一個關鍵任務,就是剪下她衣服的人,必須把剪下的碎片送給最親愛的人,剪下衣服是人性最黑暗的時刻,但送給最親愛的人,又是人性中最純真的時刻,兩者的碰撞,也正是一場赤裸裸的人性挑戰。
觀念的更新
可以看到,激浪派的誕生是由于戰后幻滅有關的問題,這是發達國家中許多人所經歷的。這種幻滅本身就表明了使他們更加關注類似佛教、禪宗偶然性。激浪派的組成一部分來自達達主義和杜尚的影響,另外一方面是對于當代社會的不安的意識。實際上,激浪派某種程度上對應于西方和日本藝術之間的主要區別,并在聯合的過程中產生了融合。
激浪派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消除了藝術與生活之問的界限,這是戰后藝術中非常重要的趨勢。約瑟夫博伊斯的作品和著作說明了這一點,他說:“每個人都是藝術家。”激浪派的創作方法多數是日常的“經濟”方法,同樣,這與日本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強烈對應,即在日常行為和物品之間構建的藝術價值以及對節儉的審美欣賞,藝術與日常生活之物緊密相連。在呈現上,接受不完整的呈現,注重創作概念和過程,主張微妙而隱晦的表達。
永恒的浪潮
激浪派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前衛性集體和組織,至今仍在繼續。而作為激浪派凝結的結晶,在國家都有激浪派的回顧展覽,例如2015年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的“小野洋子:一個女人的表演,1960-1971”;2018年在上海吳美術館的“見者的書信:約瑟夫·博伊斯×白南準”展覽;2019年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開展的“白南準回顧展”……這些展覽無一不在印證,激浪派在如今的當代藝術環境中,仍然有許多值得借鑒和啟發的意義。
(編輯/雷煥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