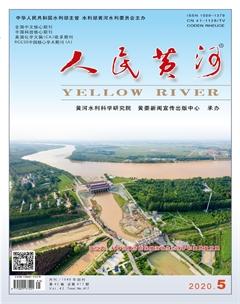黃土高原地區(qū)淤地壩“淤滿”情況及防治策略
惠波 惠露 郭玉梅
摘 要:淤地壩是黃土高原地區(qū)水土保持主要工程措施之一。基于2009年黃土高原淤地壩安全大檢查數(shù)據(jù)和2011年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數(shù)據(jù)對淤地壩“淤滿”情況的分析表明,20世紀90年代及以前修建的淤地壩,大多數(shù)已超過淤積年限,部分淤地壩已“淤滿”。淤地壩“淤滿”后,攔沙作用降到最低,但是淤積的壩地相當于水平梯田,客觀上還能起到一定的減蝕和攔蓄徑流泥沙作用;未設(shè)置溢洪道的“淤滿”淤地壩,遇超標準洪水時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但單場暴雨洪水不會造成攔蓄泥沙(壩地)被“零存整取”。對于“淤滿”的大中型淤地壩,可采取增設(shè)溢洪道、排洪渠、壩體鋪蓋防護材料等措施進行綜合治理,確保淤地壩減蝕作用的持續(xù)發(fā)揮和壩地的持續(xù)有效利用;對于“淤滿”的小型淤地壩,可比照小型水庫報廢、銷號等方法,實行動態(tài)管理,在政策上探索報廢退出機制,對報廢的淤地壩按照基本農(nóng)田進行管理。
關(guān)鍵詞:淤地壩;淤滿;淤積年限;淤積庫容;防治策略;黃土高原地區(qū)
中圖分類號:S157.3+1;TV882.1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0-1379.2020.05.021
Abstract:Warping dam is one of the main engineering measures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area. Based on the safety inspection data of warping dams on the Loess Plateau in 2009 and the first na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survey data in 2011, the analysis of “fully filled” warping dams shows that most of warping dams built in the 1990s and before have exceeded the siltation years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fully filled. After warping dam is fully filled, the silt retaining effect is reduced to the lowest level, but the dammed land is equivalent to the horizontal terrace, which can objectively reduce erosion and retain runoff and sediment; for the “fully filled” warping dam without spillway, there is a serious safety hazard in case of over standard flood, but the single rainstorm flood will not cause the silt retaining (dammed land) to be deposited gradually and washed away totally. For the large and medium-sized “fully filled” warping dams, measures such as adding spillway, flood discharge channel and dam body covering protective material can be taken for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so as to ensur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ro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warping dams and the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dammed land; for the medium and small-sized “fully filled” warping dams, dynamic management can be carried out by comparing with the scrapping and number cancellation methods of small reservoirs, exploring the scrapping exit mechanism in policy and managing the scrapped warping dams according to the basic farmland.
Key words: warping dam; fully filled; siltation years; siltation storage capacity; control strategy; Loess Plateau area
淤地壩是黃土高原地區(qū)水土保持主要工程措施之一,是黃土高原地區(qū)人民群眾對水土流失治理的原創(chuàng)性貢獻,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功效,是一種獨具特色、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攔泥淤地、減少入黃泥沙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其以顯著的生態(tài)、經(jīng)濟、社會效益受到當?shù)厝罕姟⑺2块T乃至國家的重視。習(xí)近平總書記2015年在陜西省延川縣梁家河調(diào)研時指出[1]:淤地壩是流域綜合治理的一種有效形式,既可以增加耕地面積、提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能力,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要因地制宜推行。
20世紀90年代及以前修建的淤地壩,大多數(shù)已超過淤積年限,有相當一部分淤地壩已“淤滿”,即淤積量達到或超過設(shè)計淤積庫容(攔泥庫容),也可以說淤積高程達到或超過設(shè)計淤積高程(攔泥高程),屬于“超期服役”。淤地壩“淤滿”后,逐漸出現(xiàn)老化、破損等現(xiàn)象,成為病壩或險壩,喪失繼續(xù)攔泥和緩洪、滯洪的能力,遇超標準洪水時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此前涉及淤積量超過設(shè)計淤積庫容的研究較少[2],筆者對黃土高原地區(qū)淤地壩“淤滿”情況進行了調(diào)查分析,本文對“淤滿”淤地壩防治策略進行探討,以期為黃土高原地區(qū)淤地壩建設(shè)管理、長效發(fā)揮淤地壩功能提供參考。
1 淤地壩“淤滿”情況及存在問題
1.1 淤地壩“淤滿”的概念
依據(jù)《水土保持工程設(shè)計規(guī)范》(GB 51018—2014)、《水土保持治溝骨干工程技術(shù)規(guī)范》(SL 289—2003)的規(guī)定,庫容為100萬~500萬m3的大(1)型淤地壩設(shè)計淤積年限為20~30 a,50萬~100萬m3的大(2)型淤地壩設(shè)計淤積年限為10~20 a,10萬~50萬m3的中型淤地壩設(shè)計淤積年限為5~10 a,小于10萬m3的小型淤地壩設(shè)計淤積年限為5 a。淤地壩達到或超過淤積年限對應(yīng)著淤積量達到或超過設(shè)計淤積庫容,但是近年來,由于黃土高原地區(qū)植被覆蓋率明顯提高、各項水土保持措施使得產(chǎn)流產(chǎn)沙量明顯減少,因此許多淤地壩存在實際淤積年限大于設(shè)計淤積年限且尚未“淤滿”的情況。
淤地壩設(shè)計淤積庫容反映了淤地壩攔沙能力,一般通過懸移質(zhì)輸沙量和推移質(zhì)輸沙量來確定,這2個量一般根據(jù)當?shù)剌斏衬?shù)經(jīng)驗公式來計算,由于輸沙模數(shù)是經(jīng)驗值,因此設(shè)計淤積庫容也是經(jīng)驗值。淤地壩總庫容由攔泥庫容(設(shè)計淤積庫容)和滯洪庫容組成,其中攔泥庫容是理論上可淤積的最大庫容。如圖1所示:有溢洪道的淤地壩,當淤積量等于攔泥庫容即淤積高程達到溢洪道底坎高程后,來水來沙將通過溢洪道被排到淤地壩下游,不再具有攔沙作用,屬于基本“淤滿”(圖1(a));無溢洪道的淤地壩,當淤積量等于攔泥庫容(對應(yīng)著設(shè)計淤積高程)即基本“淤滿”后,還會繼續(xù)淤高,淤積泥沙逐步占用滯洪庫容,使原設(shè)計滯洪庫容減小,極限狀況就是淤積面與壩頂齊平,即完全“淤滿”(圖1(b)),這種情況的淤地壩幾乎喪失繼續(xù)攔泥和緩洪、滯洪的能力,成為病壩或險壩,存在安全隱患。
圖1 淤地壩“淤滿”狀況示意
1.2 淤地壩“淤滿”情況
黃土高原地區(qū)現(xiàn)有淤地壩大多建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受當時技術(shù)、經(jīng)濟條件所限,建設(shè)標準低,目前已達到或超過設(shè)計淤積年限,屬于“淤滿”淤地壩。據(jù)統(tǒng)計,截至2015年,潼關(guān)以上黃河中上游地區(qū)30%的骨干壩、69%的中型淤地壩、90%的小型淤地壩建成于1980年以前[3]。據(jù)陜西省水土保持志[4]
:20世紀70年代,陜西省壩地淤積速度比較快,年均新增壩地3 053 hm2; 1980—1993年,年均新增壩地面積下降至1 133 hm2,壩地淤積速度明顯變緩。2000年以來,黃土高原地區(qū)坡面植被明顯好轉(zhuǎn),各項水土保持措施使得坡面、溝道產(chǎn)沙量顯著減少,新建小流域壩系中的大部分淤地壩實際淤積年限已大于當初的設(shè)計淤積年限,但是很多未“淤滿”,據(jù)調(diào)查,絕大多數(shù)屬于空庫運行。
1.2.1 基于黃土高原淤地壩安全大檢查數(shù)據(jù)的“淤滿”情況分析
為摸清黃土高原地區(qū)淤地壩建設(shè)現(xiàn)狀,排查安全隱患,制定有針對性的除險加固方案和措施,2009年水利部組織開展了黃土高原淤地壩安全大檢查,這次安全大檢查,對黃土高原地區(qū)已建成的各類淤地壩基本做到了“四清楚”,即基本情況清楚、病險情況清楚、采取措施清楚、安全責(zé)任清楚。檢查資料(數(shù)據(jù))表明,截至2008年年底黃土高原地區(qū)有淤地壩91 088座,其中骨干壩5 503座、中小型淤地壩85 585座。劉曉燕等[5]依據(jù)淤地壩安全大檢查數(shù)據(jù),對潼關(guān)以上黃河中上游地區(qū)5 284座骨干壩和10 673座中型壩的淤積量進行分析,結(jié)果表明:有1 550座骨干壩和6 622座中型壩的已淤積庫容達到或超過設(shè)計淤積庫容且淤積面未與壩頂齊平,屬于基本“淤滿”,分別占選取骨干壩數(shù)量的29%、選取中型壩數(shù)量的62%;完全“淤滿”的骨干壩和中型壩分別為456座和3 400座,分別占選取骨干壩數(shù)量的9%、選取中型壩數(shù)量的32%;基本“淤滿”和完全“淤滿”的淤地壩主要分布在陜北的榆林地區(qū)和延安地區(qū)。據(jù)統(tǒng)計,1980年以前建成的小型淤地壩
由于淤積庫容小、攔沙能力弱,因此在2009年黃土高原淤地壩安全大檢查時已基本“淤滿”,或完全“淤滿”。
1.2.2 基于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數(shù)據(jù)的“淤滿”情況分析
據(jù)2011年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6],黃土高原地區(qū)有淤地壩58 446座,其中骨干壩5 655座,中小型淤地壩52 791座。與2009年黃土高原淤地壩安全大檢查結(jié)果(數(shù)據(jù))相比,淤地壩數(shù)量由2009年的9.1萬座減少至2011年的5.8萬座,其中骨干壩數(shù)量略有增加(增加152座)、中小型淤地壩數(shù)量明顯減少(減少32 794座,占中小型淤地壩總數(shù)的38%)。經(jīng)初步了解和分析,開展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時,各級水土保持部門統(tǒng)計時未考慮總庫容小于1萬m3的特小型淤地壩(因其庫容小、攔沙壽命短,所以早已“淤滿”)和已經(jīng)“淤滿”的中小型淤地壩[5-7],小型淤地壩“淤滿”后被中型淤地壩逐漸“吞并”,中型淤地壩“淤滿”后被大型淤地壩逐漸“吞并”,即下壩淤積淹沒上壩,也可以稱為“淤積淹沒效應(yīng)”。“淤積淹沒效應(yīng)”的存在,使黃土高原地區(qū)中小型淤地壩數(shù)量處于動態(tài)變化中,直至達到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如綏德縣韭園溝一級支溝王茂溝小流域從1953年開始修建淤地壩,到1960年形成壩系,壩系經(jīng)過了初建、改(擴)建、調(diào)整和穩(wěn)定4個階段,伴隨著淤地壩潰壩修復(fù)和“淤積淹沒效應(yīng)”,到2000年淤地壩數(shù)量從最多時期的45座減少至23座,壩系逐漸達到穩(wěn)定狀態(tài)[8]。
1.3 “淤滿”淤地壩的攔沙減蝕作用
淤地壩建成后直接攔截了上游溝道及坡面輸移下來的大量泥沙,使得淤積面不斷抬高,原來侵蝕最為嚴重的溝谷和溝床逐漸被泥沙淤埋,改變了壩控范圍內(nèi)的坡度組成,縮短了谷坡的坡長,使流域溝道形狀由原來侵蝕較劇烈的V形逐漸演變成侵蝕強度相對較輕的U形[8],改變了壩控范圍內(nèi)的土地利用類型,淤積面下的土壤侵蝕被徹底控制;淤積面以上,壩地兩側(cè)溝谷和溝坡(峁邊線以下部分)土體的滑動面減少,土體抗滑穩(wěn)定性增強[7],重力侵蝕發(fā)生的概率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溝頭延伸、溝谷深切及溝岸坍塌、擴張,直至淤地壩“淤滿”,提高了侵蝕基準面,溝道縱比降減小,水流行進速度變緩、挾沙能力降低,壩控范圍內(nèi)的土壤侵蝕模數(shù)顯著降低,淤地壩的攔沙減蝕作用發(fā)揮到極致。雖然完全“淤滿”后,淤地壩的攔沙作用降到最低,但是淤積面(壩地)相當于水平梯田,客觀上還能起到一定的減蝕和攔蓄徑流泥沙的效果,具有很好的徑流泥沙調(diào)控作用,所以淤地壩(壩地)減蝕作用將會持續(xù)發(fā)揮。據(jù)《清澗縣志》記載,有淤地壩“鼻祖”之稱的子洲縣裴家灣黃土洼天然淤地壩是因山體發(fā)生滑塌將主溝道掩埋而形成的“悶葫蘆”淤地壩,距今已450 a之久,對洪水泥沙全攔全蓄,現(xiàn)已淤成1 000多畝(約66.7 hm2)壩地,如果按照當?shù)氐那治g模數(shù)計算,該淤地壩攔沙量早已達到設(shè)計淤積庫容,遠遠超過設(shè)計淤積年限,但是實際上并未真正“淤滿”,至今攔沙減蝕作用仍然發(fā)揮得很充分,至于未“淤滿”的原因,目前仍沒有明確的結(jié)論,據(jù)當?shù)卮迕裾f,淤積面增高增大的同時,聚湫(壩墚) 也隨之同步增高。
1.4 未設(shè)置溢洪道的“淤滿”淤地壩安全隱患
2009年黃土高原淤地壩安全大檢查中,將淤地壩安全分為5級,其中將防洪能力不足,壩體、放水建筑物和溢洪道工程完好,但達到或超過設(shè)計淤積高程的淤地壩定義為四類壩,這類淤地壩需要及時進行加高或配套溢洪道等排洪設(shè)施建設(shè)。隨后,各地有計劃地分期分批對存在安全隱患的病險淤地壩進行除險加固,在消除病險淤地壩安全隱患和保障淤地壩安全運用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2010年水利部印發(fā)的《關(guān)于進一步加強淤地壩等水土保持攔擋工程建設(shè)管理和安全運行的若干意見》(水保〔2010〕455號),對淤地壩工程建設(shè)管理和安全運用提出明確要求,其中對淤積面已達到或超過設(shè)計淤積高程,并投入正常生產(chǎn)運用的淤地壩,不再安排加高工程建設(shè)。為確保淤地壩安全運用和安全度汛,2015年4月水利部辦公廳印發(fā)了《關(guān)于開展中型以上病險淤地壩認定和除險加固初步設(shè)計工作的通知》(辦水保〔2015〕90號),其中《黃土高原地區(qū)中型以上病險淤地壩認定暫行辦法》中沒有將未設(shè)置溢洪道的中型以上淤地壩“淤滿”情況作為病險問題進行認定,使得已經(jīng)“淤滿”的大中型淤地壩未納入《黃土高原地區(qū)中型以上病險淤地壩除險加固工程實施方案》,所以存在一定的隱患。“淤滿”后的淤地壩壩體外坡會形成比較陡的邊坡,發(fā)生暴雨洪水時,小流域洪水漫頂時會沖刷、淘刷壩體,小沖溝逐步演變成大沖溝,溯源侵蝕至沿洪水通道主槽極狹窄的帶狀范圍內(nèi)。由于黃土高原地區(qū)暴雨洪水歷時較短,不同粒徑土壤自然分選沉積,淤積土壤密實度較大,因此一般單場暴雨洪水不存在壩地淤沙被“零存整取”,但是隨著暴雨洪水的一次次沖刷,如果不加以維修保護,壩區(qū)內(nèi)仍保留的淤積量(即壩地)將會逐漸被沖失殆盡,重新演變成大型侵蝕溝。如陜西省吳旗縣印峁子骨干壩,壩高31.5 m,淤地40 hm2,因“淤滿”已失去滯洪能力,1992年在超標準洪水襲擊下,將壩體沖開一個缺口,因資金困難而沒及時維修,到1994年壩體已沖毀一大半,損失壩地13.3 hm2,百萬立方米泥沙進入下游河道,幾十年治理成果付諸東流。
2 淤地壩“淤滿”防治策略
2.1 增設(shè)排洪設(shè)施
一是增設(shè)溢洪道或泄洪洞。“淤滿”或基本“淤滿”的大中型淤地壩工程,防洪能力達不到原設(shè)計防洪標準,失去了“上攔下保”的作用,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淤積量不斷增加,滯洪庫容逐年減小,抵抗洪水的能力逐漸減弱,一旦發(fā)生大暴雨洪水,可能發(fā)生漫頂進而沖毀壩體、造成垮壩的情況,若對下游村莊、學(xué)校、工礦、城鎮(zhèn)等重要設(shè)施有影響的大中型淤地壩發(fā)生漫頂,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因此應(yīng)根據(jù)地形條件增設(shè)溢洪道,采用漿砌石溢洪道或者鋼筋混凝土溢洪道,對原土質(zhì)溢洪道進行襯砌或改建,提高抗洪減災(zāi)能力和安全等級。對無地形條件增設(shè)溢洪道的淤地壩,可以增設(shè)泄洪洞等,但必須進行嚴格和充分的論證,確保淤地壩功能發(fā)揮和安全運行。如山西省興縣郝家山2號骨干壩于1989年建成,壩高23.5 m,總庫容131萬m3,其中攔泥庫容84.5萬m3,截至2009年黃土高原淤地壩安全大檢查時,淤積高程已達到設(shè)計淤積高程,淤成壩地10 hm2,排水豎井已經(jīng)倒塌,壩內(nèi)蓄水難以排出,若遇到大暴雨洪水,壩體有毀壞的可能,并殃及壩下游1 km處的郝家山村568人和13 hm2良田的安全。為此,2010年山西省水利廳利用中央投資和地方配套資金對其進行除險加固,修復(fù)了豎井,加固了壩體,增設(shè)了溢洪道,提高了該壩的抗洪減災(zāi)能力和安全等級,保障了下游群眾生命財產(chǎn)安全。
二是增設(shè)排洪渠。對于“淤滿”的大中型淤地壩,為了確保壩地有效利用,依據(jù)實際情況,可在上游淤積面陰坡一側(cè)或陰陽坡兩側(cè)布設(shè)排洪渠;溝道兩岸坡有較大徑流沖溝或壩肩處有沖溝導(dǎo)致壩體沖刷嚴重的淤地壩,根據(jù)實際需要,可增設(shè)壩面排洪渠或岸坡排洪渠,在壩體外邊坡布設(shè)截水溝和排水溝。截水溝可減少徑流對坡面的沖刷,排水溝將坡面徑流排入下游溝道,增強支溝和主溝的連通性,提高流域從溝頭至溝口排洪過流能力。如:山西省汾西縣對康河溝、西河溝、馬溝等流域“淤滿”的大中型淤地壩在壩地靠陰坡一側(cè)布設(shè)排洪渠,使壩地防澇保收,積累了豐富的壩地生產(chǎn)經(jīng)驗;山西省石樓縣的東石羊壩,前身為東石羊水庫,始建于1979年,壩高25.5 m,設(shè)計總庫容290萬m3,主要用于灌溉下游農(nóng)田,由于上游水土流失嚴重,到1988年已淤積庫容200萬m3,超過了設(shè)計淤積庫容,淤成壩地25.3 hm2,水庫失去原有調(diào)蓄功能,改按淤地壩運行(納入了淤地壩管理范圍),于1991年在淤泥面上開挖排洪渠,使壩地得以利用,并有效防止了壩地鹽堿化;陜西省子洲縣2017年春季在岔巴溝流域的馬家溝溝口壩地內(nèi)修建了一條寬2.5 m、深0.5 m的排洪渠,在當年“7·26”暴雨洪水中雖然起了一定的排洪作用,但受排洪能力的限制,壩地玉米依然倒伏嚴重。實踐表明,保障壩地高效利用的基礎(chǔ)是建設(shè)與水土保持措施相配套的地表徑流排泄通道。
三是鋪蓋防護材料對壩體進行有效防護。新型復(fù)合材料PET具有拉伸強度高、抗老化、透水保土等優(yōu)點[9],土工格柵具有高強度、耐腐蝕性、耐久性及提高壩體穩(wěn)定性等優(yōu)點[10-11],可將新型復(fù)合材料PET或土工格柵鋪設(shè)在淤地壩壩體表面的一定范圍內(nèi),對壩頂、壩坡進行保護,穩(wěn)定壩身結(jié)構(gòu),防止和延緩壩體被沖刷、淘刷破壞,防止形成侵蝕溝。
四是采取工程措施與植物措施相結(jié)合的綜合治理。采用工程措施的同時,還應(yīng)布設(shè)植物措施,在下游壩坡種植適生灌草(密植檸條、紫穗槐等耐干旱作物),提高邊坡植被覆蓋度。黃土高原地區(qū)必須治溝和治坡同時進行,以坡溝系統(tǒng)來說,在“淤滿”淤地壩的壩控范圍內(nèi),從峁頂、峁坡、溝坡到壩地依次修建集雨工程、坡改梯(或者水平溝、水平階、魚鱗坑等)、種植適生林灌草、布設(shè)排洪渠,調(diào)蓄徑流,保證“淤滿”壩地持續(xù)有效利用(耕種)。如陜西省綏德縣辛店溝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園有鴨峁溝和小石溝2個壩系(共18座淤地壩)、大型集雨工程3處、蓄水池4座、溝頭防護多處及植物措施,其中有林地91.91 hm2、人工草地17.43 hm2、梯田4.43 hm2、壩地5.33 hm2,是水土保持措施配置的典型,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2.2 探索“淤滿”中小型淤地壩報廢機制
對于基本“淤滿”的中小型淤地壩,淤積面已達到設(shè)計淤積高程,有的“超期服役”使淤積面(壩地)與壩頂幾乎齊平,已沒有滯洪庫容,在減蝕效益方面相當于水平梯田,客觀上還能起到一定的攔蓄泥沙作用,達到了最初設(shè)計的目的,發(fā)揮了當初設(shè)計的大部分作用,已完全沒有必要再進行加高,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可實行動態(tài)管理,探索報廢退出機制,實行報廢處理[12],對報廢的淤地壩按照基本農(nóng)田進行管理。如內(nèi)蒙古鄂爾多斯市截至2016年有壩控面積不足1 km2、總庫容在1萬m3以下的特小型淤地壩542座,這些淤地壩于1968年至2010年間建成,目前均達到設(shè)計淤積年限,大多數(shù)“淤滿”,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比照小型水庫報廢、銷號等方法,鄂爾多斯市水利局已將其中的2座淤地壩作為報廢、銷號試點,正在探索和研究制定小型淤地壩報廢管理辦法。
3 結(jié) 語
(1)從壩系角度來說,淤地壩存在“淤積淹沒效應(yīng)”,1960—1979年黃土高原地區(qū)淤地壩淤積速度較快,1980—1999年淤積速度明顯變緩,2000年以來絕大多數(shù)淤地壩“空庫”運行。
2)淤地壩完全“淤滿”后,其攔沙作用降到最低,但是淤積的壩地相當于水平梯田,客觀上還能起到一定的減蝕和攔蓄徑流泥沙作用。
(3)未設(shè)置溢洪道“淤滿”的淤地壩,單場暴雨洪水不會造成攔蓄泥沙(壩地)被“零存整取”。
(4)對于“淤滿”的大中型淤地壩,可采取增設(shè)溢洪道、排洪渠、壩體鋪蓋防護材料等措施進行綜合治理,確保淤地壩減蝕作用的持續(xù)發(fā)揮和壩地的持續(xù)有效利用;對于“淤滿”的小型淤地壩,可比照小型水庫報廢、銷號等方法,實行動態(tài)管理,在政策上探索報廢退出機制,對報廢的淤地壩按照基本農(nóng)田進行管理。
參考文獻:
[1] 霍小光.習(xí)近平春節(jié)前夕赴陜西看望慰問廣大干部群眾 向全國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祝祖國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N].人民日報,2015-02-17(1).
[2] 高海東,賈蓮蓮,龐國偉,等.淤地壩“淤滿”后的水沙效應(yīng)及防控對策[J].中國水土保持科學(xué),2017,15(2):140-145.
[3] 劉曉燕,高云飛,馬三保,等.黃土高原淤地壩的減沙作用及其時效性[J].水利學(xué)報,2018,49(2):145-155.
[4] 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陜西省志:水土保持志[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254-255.
[5] 劉曉燕,高云飛,王富貴.黃土高原仍有攔沙能力的淤地壩數(shù)量及分布[J].人民黃河,2017,29(4):1-5.
[6]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公報[Z].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13:8.
[7] 李景宗,劉立斌.近期黃河潼關(guān)以上地區(qū)淤地壩攔沙量初步分析[J].人民黃河,2018,40(1):1-6.
[8] 惠波.黃土高原小流域淤地壩系淤積特征及其生態(tài)效應(yīng)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學(xué),2015:17-25.
[9] 于沭,陳祖煜,楊小川,等.淤地壩柔性溢洪道泄流模型試驗研究[J].水利學(xué)報,2019,50(5):612-620.
[10] 趙紅,趙忠偉,陳振華.淤地壩筑壩規(guī)劃新技術(shù)應(yīng)用的探討[J]. 水科學(xué)與工程技術(shù),2008(5):71-73.
[11] 李廣良.加筋土工格柵土壩填筑方法[J].山西水利科技,2014(1):23-24.
[12] 惠波,王志雄,惠露,等.關(guān)于黃土高原地區(qū)淤地壩降等、銷號、報廢的思考[J].中國水土保持,2018(11):1-2.
【責(zé)任編輯 張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