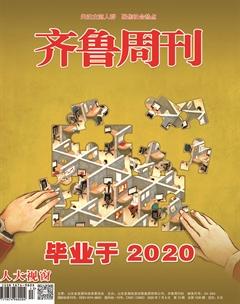張二棍:人間的一場過客
張二棍,本名張常春,1982年生于山西。獲《詩刊》年度青年詩人獎、華文青年詩人獎、李杜青年詩人獎、《詩歌周刊》年度詩人等。曾參加第31屆青春詩會,2017年度首都師范大學駐校詩人。現為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
一生中的一個夜晚
那夜,我執一支
墨水殆盡的鋼筆,反復摩擦著
一張白紙。我至今記得
那沙沙的,沙沙的聲音
那筆尖,旁若無人的狂歡
那謝絕了任何語言同行的盛大旅行
那再也無法抵達的渺遠,與驕傲
那沙沙的聲音,在夜空中,回旋著
直到窗外,曙光涌來,鳥鳴如笛
我猜,是一只知更
它肯定不知道,我已經
度過了自己所有的夜晚
誰也不可能知道,在一夜的
沙沙聲中,我已經敗光了
他們的一生
太陽落山了
無山可落時
就落水,落地平線
落棚戶區,落垃圾堆
我還見過。它靜靜落在
火葬場的煙囪后面
落日真謙遜啊
它從不對你我的人間
挑三揀四
穿墻術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孩子
摁著自己的頭,往墻上磕
我見過。在縣醫院
咚,咚,咚
他母親說,讓他磕吧
似乎墻疼了
他就不疼了
似乎疼痛,可以穿墻而過
我不知道他腦袋里裝著
什么病。也不知道一面墻
吸納了多少苦痛
才變得如此蒼白
就像那個背過身去的
母親。后來,她把孩子摟住
仿佛一面顫抖的墻
伸出了手
黃土高原風成說
那么說,我的故鄉
是一場,接一場的大風
刮來的。那么說
是鋪天蓋地的大風
帶著一粒粒沙子,黃土
燕子銜泥般,堆砌成
山西,代縣,段景村
那么說,在某一場無名的大風中
先人們,拖兒帶女跋涉著
他們手拉著手,一臉汗漬,和泥土
像是大風創世的一部分
這么說,他們最后埋在土里
也等同于消逝在風中
這么說,我是風
留在這里的孩子
——我住在這人間的哪里
也不過是一場客居
無需用過多語言來評判二棍的詩,分行的文字一下子生長出魔力,讀了,即生成一種評判。隱忍、悲憫、虔敬……許多對二棍詩歌解讀的文字中會出現這些詞匯。他的詩,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場域,如雙手緊緊撕扯大地,如雪崩時雜亂的紛紛揚揚。
一人獨行,物我皆宜。好似世界只剩“我”與相對應的一切,二者不分大小,不分長幼。窗外的知更鳥、落日、大風吹來的故鄉,帶有某種特定的色澤,蘊含了一種巧妙的生存哲學。他的詩,有蘇軾的味道,又偏向杜甫,在冰冷中建構溫度,在坍圮的人間豎起人性的旗幟。
4首詩,選自詩集《入林記》,剛獲得趙樹理文學獎,授獎詞如是說:“在蒼涼中有溫暖、平淡中含悲憫,語言粗礪,質地堅硬,其中有無數讓人動容的靈思。”曾是地質隊員的二棍,似乎距離大地更近一些,他能撲下身子,聽到轟隆隆的鳥鳴。
——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