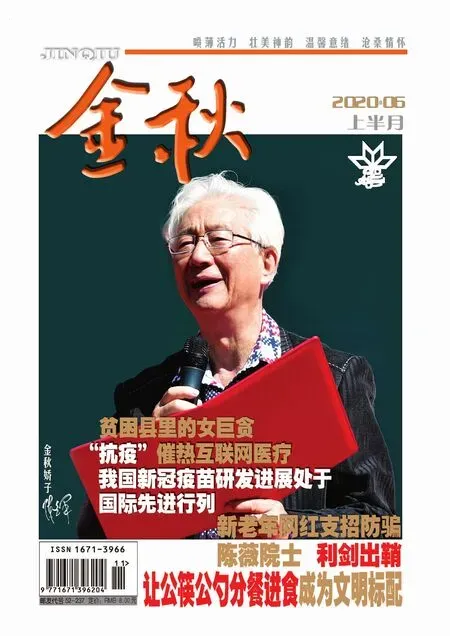“明君”張聞天
文/銀笙

從棗園那塊牌匾說起
1 9 6 1年我去延安上學不久,因接受革命傳統教育,學校組織我們參觀棗園革命舊址。第一次走進領袖住處,我記得特別清楚,毛主席院落右邊不遠處就是敬愛的周總理住處。參加工作后多次陪人參觀,我都按最早的印象去講解。
記不清八十年代哪一次陪人參觀,周總理窯洞前多了塊牌匾,寫的是“張聞天舊居”。這是怎么回事?只有4孔窯洞,難道每人只住兩孔?問講解員,他們只說總理多在重慶,只是回來時短期住在這里。看來一二十年的解說只是移花接木,其實那4孔窯洞都是張聞天的住處,從此我腦子里有了一個大問號,可惜那些年不便追根問底,直到參與到數字紅色延安制作,才系統了解了根根梢梢。
張聞天(長期用化名洛甫)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蘇省南匯縣的殷實農戶家庭。五四運動爆發后,投身于學生運動,并開始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評介外國文學名著,后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東京、美國舊金山學習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并任助教、翻譯,同時兼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報道員。
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夏,共產國際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他被指定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隨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1934年10月參加長征。
遵義會議挑起歷史重擔
紅軍離開蘇區,軍事上仍由“最高三人團”即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和博古、周恩來負責。被排除出領導機構的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跟隨中央隊行動。毛澤東因惡性瘧疾走不動路,王稼祥也因敵機炸傷,兩人坐著擔架行軍。只有張聞天騎著馬前后照應,成了小小的“中央隊三人團”。一路走一路談,對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目前的軍事指揮有了更多共同認識,張聞天和他過去在中央工作中犯過的“左”傾錯誤一步步決裂了。他和王稼祥、毛澤東決心糾正李德、博古錯誤的領導,將紅軍引向正確的方向。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后,張聞天首先起來作了反對“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反報告”。這個反報告實際是他們三人商量并以毛澤東觀點為主形成的。因張聞天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兼4人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立即得到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同志支持。根據他的反報告,他為中央政治局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并獲得通過。在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協助周恩來指揮紅軍。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挑起歷史重擔。張聞天在延安寫的《反省筆記》(1943年12月16日)中寫道:“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鄧小平于1979年8月25日《在張聞天同志追悼會上致悼詞》中也證實說,1935年1月,在我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同志“被推選為總書記。”他還在《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斗力的黨》(1965年6月14日同亞洲一位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說:“毛澤東同志那時候沒有當總書記,博古的總書記當然當不成了,但還是由曾經站在王明路線一邊的洛甫當總書記。”(《鄧小平文選》第1卷,1994年版,第339頁)
解決“陜北肅反”功不可沒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決“陜北肅反”問題。長期以來,毛澤東主持解決“陜北肅反”的說法廣為流傳和盛行,而張聞天在解決這件事情上發揮的作用卻被有意無意忽略和淡忘。
當中央紅軍于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張聞天和毛澤東打聽劉志丹,不料卻聽說劉已被逮捕關押在瓦窯堡,而且紅26軍營以上干部有幾百人被逮,有些已被錯殺。黨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訊,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張、毛到甘泉下寺灣后,直接聽取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匯報,知道真相一致表態:“陜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要快放劉志丹!”因毛澤東領軍去部署直羅鎮戰役,張聞天立即派王首道先去瓦窯堡接管陜甘邊區保衛局擔任局長,把事態控制下來,還成立五人小組在博古指導下負責審查錯誤肅反事件,很快釋放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同志。不到一個月,在張聞天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指出陜甘晉省委“在肅反斗爭中犯了小資產階級‘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11月底,張聞天主持為劉志丹等平反的活動分子會議,錯誤得到迅速糾正,挽救了陜北黨和紅軍根據地,為黨中央在陜北落腳創造了重要內部條件。
毛澤東為張聞天當“紅娘”
遵義會議后,作為總書記的張聞天和“大帥”毛澤東互相信任、密切配合,使紅軍度過一次次艱險。特別是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的危急時刻,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團結一致,使黨和紅軍脫離了生死攸關的險境。
并肩戰斗讓他和毛澤東結下戰友情誼。長征路上,毛澤東就為他的婚姻積極籌劃。毛看擔任中央隊秘書長的劉英不錯,有意促成這段婚事,給劉英介紹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劉英說:“我不要結婚,我怕生孩子。你看賀子珍,懷孕了還在行軍,生孩子也放在老鄉家里,這個樣子怎么行呢?”毛澤東笑道,那也沒有什么了不得的嘛。他扭頭念起前些日子行軍時寫給張聞天的打油詩:“洛甫洛甫真英豪,不會騎馬會摔跤……”劉英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畢竟有些難為情,趕緊走了。后來,溫文爾雅的張聞天在炭火上煮醪糟給劉英吃,鼓足勇氣挑明說:“我們的關系是不是進一步呀?”因張聞天是她敬愛的總書記,她根本沒往“戀愛”上想。離去路上回憶起與張聞天交往的一樁樁往事,覺得他不僅可敬,也可親可愛,也就慢慢慢慢加深了感情。紅軍落腳到瓦窯堡,在鄧穎超、博古、羅邁等同志撮合下,他倆終于喜結連理。從直羅鎮打完勝仗的毛澤東一進窯洞就嚷道:“你們要請客!結婚不請客不承認、不算數!”碰到這種玩笑場合,聞天口訥,劉英卻潑辣:“拿什么請啊?又沒錢又沒東西!”毛還是不放松:“我倒是真心給你們賀喜來了,還寫了首打油詩呢。風流天子李三郎,不愛江山愛美人。當今洛甫作皇帝,又愛江山又愛美人。”這首詩除慶賀外,還將張聞天的民主作風夸了一番,算是補了“鬧新房”的一課。
從內戰到抗戰的戰略轉變
1935年夏季,日本侵略華北的行動急劇升級,中華民族的危機達到空前深重的地步。張聞天思考著如何實現停止內戰,進而轉變為直接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1935年11月13日,他主持西北中央局會議,明確提出實現戰略轉變的任務和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當毛澤東和周恩來回到瓦窯堡后,張聞天即于12月17日在他和劉英住的窯洞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瓦窯堡中央政治局會議。受政治局委托,張聞天起草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統稱《瓦窯堡會議決議》)。為傳達會議精神,12月27日,黨中央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著名報告,在全黨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紅軍到達陜北后,張聞天就重視聯合東北軍的工作,并在黨的文件中明確“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愿在共同抗日三條件下同一切抗日反蔣的部隊訂立作戰協定”,“愿意更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11月20日至24日,直羅鎮戰役勝利后,張聞天于26日致電前線的毛澤東,提出對所俘東北軍軍官優待政策:“為了擴大我們抗日反蔣的影響與同盟者,此次所俘東北軍軍官中(師長亦在內)應給以優待,曉以抗日反蔣大義后大都釋放。同時表示,紅軍不但不殺白軍士兵,而且也不殺軍官,以進一步瓦解白軍上層。”正是這一政策的實行,東北軍與黨中央才建立了直接聯系。
1936年4月9日晚,從瓦窯堡趕到延安的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城內天主教堂徹夜長談,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識。4月中旬,因受蔣介石指揮,東北軍一部向瓦窯堡和安塞進攻,導致工廠、醫院一片廢墟,毛澤東和黨中央審時度勢,果斷決定撤離瓦窯堡,于7月11日到達保安。11月21日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勝利結束長征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西安事變”中極其重要的歷史作用
1936年12月12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即“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在制定和平解決事變方針問題上經歷了一個短期的曲折變化過程,前后變化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
事變爆發之初,在1 3日黨中央召開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多數人意見是主張“除蔣”“審蔣”。反映這次會議初步方針的公開文件是12月15日發表的《紅軍將領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電文發布不久,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全面考察和周恩來赴西安后爭取和平努力的嘗試,迅速改變了原來不成熟的方針。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的發言作出這樣的分析:“張學良這次行動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揭破妥協派”這個表述,就是指明這個行動是對蔣介石為代表的妥協派在抗日問題上妥協動搖的一次揭露和打擊,不但準確概括了事變發動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測到事變積極意義方面可能發展的前途。他在發言中提出“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這一獨到見解,“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一具有總綱性的結語,實際為我黨制定正確的方針指出了根本方向。當時留在保安的兩個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和張聞天一起運籌帷幄作出和平調解事變的最終決策。
就在張學良送蔣回南京被扣后西北局勢發展到最緊張的時刻,也就是東北軍著名愛國將領王以哲被害前夕,張聞天親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來現場商定大計。張聞天是1937年1月25日從延安動身,27日抵達西安的。當天晚上就發生了少數激烈分子到周恩來住所請愿的事件。博古后來回憶道,“洛甫同志來了,正是很尖銳的時候,很險惡的時候。”面對險惡形勢,他返回紅軍在云陽總部,以個人名義致電毛和周、博提出重要建議:軍事上紅軍主力向渭北方向撤離,政治上以朱、毛對這一行動發表談話,主張和平統一團結御侮,堅決反對新的內戰,表示紅軍愿服從南京中央政府指導。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帶來劃時代的歷史性轉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跨入新階段。張聞天恪守總書記職責,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密切配合,做出了杰出貢獻。
主管宣傳和教育工作
1937年1月,黨中央和紅軍進駐延安后,張聞天就把他的精力放在宣傳和干部教育工作上來。
自遵義會議推選張聞天擔任黨中央總書記后,他總覺得自己不完全適合領袖地位,主動三次“讓賢”:1935年4月紅軍長征渡過北盤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到白區工作,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毛澤東等不同意改派了陳云。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為表示團結,他又主動提出將自己職務讓出來,被毛澤東勸止。1938年秋天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前,共產國際確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但職務并未明確。于是,張聞天又在會議期間誠懇提出,應推舉毛澤東為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對張聞天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黨中央總書記繼續由你擔任吧。”會后,張聞天卻“主動讓賢”,將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中央政治局會議地點也由他過去的窯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六屆六中全會“讓賢”后,因他兼任中宣部長,宣傳和干部教育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1937年4月,《解放》周刊創刊,他任主編。《解放》是中共中央公開發行的政治理論機關刊物。起初為周刊,后為不定期刊,是張聞天投入精力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刊物。到1941年8月終刊共出版134期,發表他的文章24篇,他編寫了《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是用馬列主義觀點編寫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的開創之作。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名著也都首先在這里發表,隨即由解放社出版單行本。張聞天在創刊號上發表的《迎接對日直接抗戰偉大時期的到來》及后來的《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長篇論文,再次從敵我雙方力量出發,辯證地闡明了中日戰爭的持久性。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也吸收了他的觀點。1939年5月17日在中央書記處討論宣傳部工作時,張聞天報告說:《解放》的出版是“中宣部最大的工作”,“傳播了中央主張”,共辦了七十余期,發行七十余萬份,有幾處翻印,比過去大革命時期的《向導》更廣。此外出版書籍七十余種,對全國宣傳工作有很大意義。毛澤東贊揚說:“洛甫報告很好。”并認為“理論刊物的編印延安是空前的”。
1939年10月創刊的《共產黨人》是按照毛澤東《發刊詞》的意圖辦的一個全國性黨內刊物。從1939年10月到1941年8月共出了19期。傳達了中央及中央有關部門黨的建設的指示、決議39篇;傳播了建黨工作的經驗;特別重視黨的政策和策略的宣傳;指導了干部教育工作。主任編輯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回憶說:“我是編輯,負責編輯出版的實際工作。工作人員有陶希晉,后來又有馬洪。洛甫是主編,每期稿件編好,都送他審定。”張聞天撰寫了多篇文章,毛澤東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首先在該刊發表,其中包括張聞天寫的第一章第三節“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
張聞天在干部教育方面也傾注了心血。1938年5月5日,延安馬列學院正式開學,他兼任院長。學院設在與楊家嶺隔河相望的蘭家坪,緊鄰中宣部和他住的窯洞。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所攻讀馬列主義比較正規的最高學府,三年多時間受過教育的學員八九百人,提高了全黨的理論水平。1939年他組織了《資本論》學習小組,王首道、吳亮平、艾思奇、鄧力群等十多人不論寒暑隔周在他的窯洞花半天時間學習討論,直把第一卷25章全部學完。黨的理論建設、干部教育、宣傳鼓動、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他盡心盡力,成績卓著,建樹良多,不愧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和教育家。
張聞天一向敬重毛澤東,卻又從不盲目,有獨立見解并愿意不斷探索。脫離負責崗位后,他自感缺少實際經驗,于是去搞農村調查,隨后提出一個將來如何使農民富裕的生產方式設想。當時的環境使這一設想不能實現,不過幾十年后再看這一見解,人們卻不能不佩服張聞天的遠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張聞天等所作的錯誤結論。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隆重追悼張聞天。198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胡耀邦發表講話,張聞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澤東一起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黨的杰出領導人的行列,給了張聞天應有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