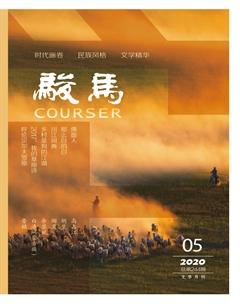鄉村是狗的江湖
余顯斌
1
鄉村,是狗們最后一片江湖,是狗們保持真性情的最后一片土地。
這兒空曠、遼遠,狗們在這兒才顯得野,顯得狂放不羈。它們在青青的草地上奔跑著、撕咬著,有時齜著牙很兇狠;有時又互相貼著頭頸,顯得很友善;有時漫步而行,又表現得很隨意,好像一個農人,走在自己的田頭地腳,走在自己的門前墻邊一般。
麥田、草坪,甚至河沿,都是它們活動的天然場所,是它們出沒的地方。
總之,人不理解它們,它們也不需要人理解。它們自行其樂,賽跑,決斗,甚至在風高月黑的夜晚狂吠幾聲,追兔獵狐,自行其是,沒有什么拘束,也沒有什么壓抑。
行走在都市的時候,看見一只只狗被鏈子拴著,跟著它們主人跑著,打著滾討好,或者依偎在主人的懷里哼唧著,我就想,這還是狗嗎?還是我小時在鄉村所見的那種灑脫隨意的狗嗎?根本不是,城里的狗溫順如兔子一般,早已沒有了狗性和狗的氣節。尤其有的人,自己收拾得一團糟,頭發鳥窠一般,偏要帶著一只寵物狗,如從灶洞里牽出一個灶王爺一般,五花六道的,我就有一種悲哀、一種痛苦,就格外懷念起鄉村的狗,懷念起那些無拘無束的狗了。
有一句名言說得好:“巴掌大的臉都管理不好,還談什么詩和遠方。”很多人自己都沒將自己打理好,偏要去喂一只寵物狗,邋里邋遢的,帶到一個地方,狗就翹著一只后腿,在墻根下,在花壇邊,甚或在馬路上,滋出一股尿,流淌出一灘糞便,不唯玷污環境,也是對狗的尊嚴的踐踏。
做一只寵物狗,是狗的悲哀。
做一只鄉村狗,才自由,才有尊嚴,可以逍遙來去,我行我素,就如一個腰插長劍的游俠,一旦動身,腳下就是無盡的土地,供它們自由馳騁,供它們隨意行走。它們有時可以跑到山上,在野雞鳴叫時,如偵察高手一般,貼著地面,一寸寸地靠近,突然發動襲擊,保不準就逮住一頓大餐,大快朵頤。當然,更多的時候,則是咬一嘴毛,望著驚叫著飛向遠處的野雞,汪汪叫兩聲,轉身瀟灑離開,拿得起放得下,很有氣派。有時,它們會徑直走過小路,直視著遠方的地平線,直視著天空和大地相接的地方,對沿路的人家住戶,四處啄食的雞,還有狗食望都不望一眼,一副目標遠大心無旁騖的樣子,讓人見了陡生敬意。
它們是去赴一個浪漫的約會,還是去江湖爭霸,誰知道呢?
長時間流浪,四處漂泊行走,它們難免會感到孤單,有時也會停下遠行的腳步,看著一群狗打架,或是瘋玩,就會伸長脖子,長長地叫幾聲,對方一旦回應,它們馬上跳躍著,翹著尾巴沖進去,和這些狗瘋玩起來,一點兒也不生分。
狗和狗沒有生疏感,一見如故。
有時,它們會跟當地的狗一起去對方的狗窩,或者去狗的主人家做客。更多的時候,玩得差不多了,它們望望西斜的太陽,覺得前路還遠,目標還在遠方,不能因為這兒的狗好客,就產生“此間樂”的想法。它們就會和這些狗作別,走幾步,回頭叫幾聲,然后一徑里走向遠方,走向落日天邊,走成一個黑點,粘在天地的盡頭,漸漸消失不見了。
2
我家大黑就曾領回過這樣一只流浪狗。那是一個下午,大黑得意洋洋地跑回來,圍著我奶轉著,扯著我奶的衣服,讓她出去。我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來了,外面就蹲著一只白狗,吐著舌頭,是大黑帶回來的一位陌生朋友。
我奶摸著大黑的頭笑罵:“作精捏怪的!”
我奶就走回去,拿了狗食倒在盆里,大黑竟不吃,蹲在一邊,文質彬彬地看著那只外來狗吃,很謙讓很淑女的樣子。那只狗久闖世界,自然大方,一點兒也不扭捏作態,毫無小家子氣,呱唧呱唧地吃起來,吃飽后,大黑才走過去,自行開飯。
這只狗在我家客居三天。三天里,大黑帶著它走遍我們的村子,那只狗仿佛一個游客,大黑仿佛導游一般,盡職盡責,毫不怠慢。它們閑暇了,就相互抵著頭,相互舔著毛,還在草坪上賽跑,總之,關系融洽,相見恨晚。
三天后,那只白狗搖著尾巴上路,邁著輕快的步子,向著朝陽升起的地方跑去,跑向心目中的江湖。
我奶說,當時大黑還去送了,還對著遠去的狗影叫了幾聲,那只狗也回頭叫了幾聲。
我奶說時,大黑在旁邊,黑黑的眼睛如珍珠一樣,得意洋洋地甩著尾巴,一副沒把自己當外人的樣子。
鄉村有狗,就如江湖有了俠客,有了來往的馬蹄和月夜的簫音,就少了一份寂寞,多了一份熱鬧,多了一份生機。特別是在夜晚,門一關,只有一地蟲鳴,如一顆顆露珠一樣,很靜的。這時,“柴門聞犬吠”,幾聲狗吠汪汪傳來,把夜攪拌開,攪拌活泛了,如春水一樣,一波波擴展向遠方;甚至將月光也犁開了,犁出無邊的波紋。夢中,有狗叫的聲音,人的心就踏實,睡夢也香甜,因為有狗叫的地方沒有賊,就沒有邪惡的影子出沒。
鄉村的狗們不是懶漢,它們好打抱不平,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絲毫不會退縮,不會含糊的。有時,稍有響動,一只狗叫,一群接著叫,此起彼伏,猶如大合唱一樣,有的長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細,有的沙啞聲如拍哈密瓜有的洪亮如銅鑼,再大膽的小偷或壞人,這時都得捧著膽子,安安生生躲在家里,或者躲在被窩里。
鄉村的狗活出了狗的氣節、狗的格調,它們很多時候會遭遇生活的艱難和窘迫,但絕不像城里的狗依賴他人、飯來張口,如錦衣玉食的少爺少奶奶一樣。
有段時間,我家的雞老丟。
我奶急了,就到處找,房檐后,山洞里,河溝邊,都不見影子。后來,我奶沿著一路雞毛找到一個壩洞中,看到一窩毛烘烘的狗崽子,胖乎乎的,正偎著一只黑狗,哼哼唧唧睡得十分愜意,一個個小鼻尖一翹一翹的。
洞中一地雞毛,有白的有黑的還有灰色的。
我奶長嘆一口氣,這只當媽的野狗生了孩子沒奶水,就跑出來偷了自己的雞。以后,我奶每天拿些剩飯送到洞中,放在那兒,然后轉身走了。
小狗滿月后,我奶回家,這只黑狗帶著一群兒女跟在后面,浩浩蕩蕩,來到我家,登堂入室,安家落戶。后來,這些胖乎乎的小狗一只只送人,黑狗停止了流浪,留下來給我奶做伴,經常跟在我奶后面,就如保鏢一般,寸步不離。這,就是我家的大黑。
如果狗也有江湖,大黑當年就是一個女俠,笑傲江湖,踏遍千山;住進我家,也算是金盆洗手、歸隱山林了。
3
鄉村的狗久走江湖,看慣人情冷暖,從不狗眼看人,也不狗仗人勢,相反很講俠氣,很有義氣。
我小時隨奶奶下河,一次,看見一尾小魚在水面游動,如柳葉一樣很可愛,就伸手一抓,魚沒抓住,人卻“噗通”一聲掉進水中,咕嘟咕嘟喝著水。我奶跳著腳大叫救命,可河邊無人,四處也沒有人影。就在我奶急得渾身發軟時,“嗵”的一聲,大黑閃電一樣跑來,跳下了水,不一會兒,就扯著我的脖領上了岸。我奶說,自己當年收留黑狗,竟救了自己孫子的一條命。
我奶說:“狗啊,比人厚道。”
那時,太陽暖暖地照著小村,照著遠處的山近處的水,暖風吹來陣陣花香,還夾雜著飛揚的花瓣。春天老了,鳥鳴老了,我奶也老了,她說話時嘴不關風,口水拉得老長老長的,亮晶晶的。旁邊,大黑臥在那兒打著鼾聲,它已風華不再,不復當年行走江湖快捷練達的樣子了,已經老得走路都左右搖擺了。
我奶咳嗽著說:“它是你的恩人,我走了,你要對它好。”
我擦著鼻涕,站在春天的陽光下,輕輕點了一下頭。
我奶叮囑說:“記得倒食,別餓著它。”
我忙吸著鼻涕,說曉得。
我不知道我奶準備去哪兒,要叮囑我這些話。我也不知道她為什么不帶上我,不帶著大黑。
我奶走時是個下午,那時太陽仍暖暖地照著村子,照著我奶,我奶睡在椅子上就再也沒有醒來,口水仍拉得老長老長的,亮晶晶的。大黑就叫,聲音沙啞著,如破風箱一樣一忽閃一忽閃的。然后我們就出來,就發現我奶沒有了呼吸。
我奶活著時說:“把我埋在山坡上啊,那兒暖和。”
我奶就被埋在山坡上那片向陽的地方,那兒真的暖暖的,暮春的時候,草色綿延如毯子一樣一直扯向遠處,上面是一朵朵的花兒,如一顆顆星星,也如一顆顆露珠。
4
我奶死后,大黑就蔫了,整天勾頭耷腦的打不起精神了,更不見了當年行走江湖的風采。它每天早晨離開,傍晚回來,整天蹲在我奶的墳旁,在那兒睡覺,醒了,就扯著嗓子叫幾聲,聲音不再響亮如鐘,而是沙啞破碎,如一地的碎玻璃渣子。它的毛越來越亂了,東一塊西一塊的,如掉毛的毛毯一樣。
給大黑倒食的任務,就落在我和我娘的身上。它吃飯的時候,不再呱唧呱唧響了,有時吃吃,還低著頭站站。吃完后,它就走了,一聲不吭地走向山坡,走向那叢林,蹲在我奶的墳旁,如一尊雕塑一樣,不時抬起頭叫兩聲。更多的時候是睡著了,低垂著頭。
那天吃飯時不見大黑回來,天快黑了也不見大黑回來,我們就找到我奶的墳旁,暮色蒼茫中,大黑直直地蹲在那兒,一動不動。我扯著嗓門兒喊:“大黑。”大黑不應,一動不動地坐著。
我和娘走過去,我一推大黑,大黑倒下了。
大黑早已沒有了呼吸,已經死去多時了。
鄉村江湖沒有了大黑,是多么寂寞啊。鄉村江湖沒有了大黑的叫聲,夜晚該是多么瘆人啊。如果當年那只白狗再回來尋找不到大黑,也一定會很憂傷的。
我們埋葬了大黑,就埋葬在我奶的墳前。
不久,我就走了,走向學校,走向遙遠的城市,也一天天遠離了狗的江湖,一天天遠離了大黑的江湖。
大黑的那片江湖,永遠天寬地闊、炊煙裊裊,在等著我回去。
責任編輯 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