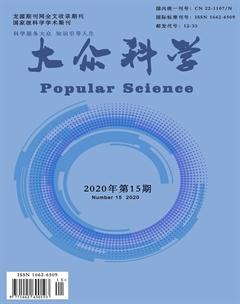重塑信仰與理性的現實意義
朱志宇
摘 要:信仰與理性是哲學上的一對姊妹,相互交織纏繞,構成了哲學史炫麗多彩的歷史風景。但因矛盾導致的沖突和危機也日益顯現出來,尤其是當代極端的解構主義哲學思潮的涌現,更讓二者無所適從。恰逢其時,對信仰與理性的探討更有現實的意義。但必須改變前人的思辯思路,轉移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才能看到嶄新的思路。
關鍵詞:信仰;理性; 重構
信仰和理性是西方哲學家們探討、思辨及其追求的“雙峰”。一切哲學問題,可由此展開;一切矛盾、危機和沖突可由此流露;一切追求與探索,可由此收攝。
趙敦華先生后期的“大哲學”之說,對此探討頗多,尤其是載于《哲學研究》(1944年第11期)的《超越后現代性:神圣文化和世俗文化相結合的一種可能性》一文,今日看來仍不失有很大的啟示意義。而文章中總結的西方傳統文化的特質及后現代文化的現象,無不讓哲學研究愛好者們眼觀現實、心靈沉思。現我們不妨重溫此文提出既同又異的哲學思考,分“回顧說”、“差異說”和“接著說”來粗略解讀一下。
一、回顧說
“西方文化傳統并不是一個單一的傳統,而是不同民族和時代傳統的集合。比如,它包括拉丁民族、盎魯薩—薩克遜民族和北歐日耳曼民族的傳統,也包括希臘文化、中世紀基督教、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這些劃時代的傳統。”[1]這一總結當然是世所公認的。
(一)前現代性的神圣文化
談到前現代性時期,指的是“古代和中世紀文化特性,而這個時期的傳統可以形象看作是三個民族精神的整合。即希臘哲學的理性精神,希伯萊的宗教精神和羅馬的法治精神,這三者不能全部被歸結為宗教,但卻歸屬于神圣文化”[4]。
趙敦華先生敏銳地捕捉到:“若無神圣的名義,基督教之愛是不能推行的。”[6]因為耶穌提倡:一是熱愛上帝;二是愛人如己。其愛義是無差別、無條件的。不但愛自己的鄰居,而且要愛罪人、仇人與己相同。這也只有依靠宗教信仰,甚至是罪罰與救贖的力量才能推廣貫徹下去。
(二)現代時期的世俗文化
西方的現代啟蒙運動是始于18世紀。但15至16世紀已有了啟蒙運動的苗頭,正由宗教神學向理性主義時期過渡與轉變,至17世紀英國科學和哲學的發展其現代性有了較為明顯的表征。
啟蒙運動的綱領是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笛卡爾成為現代哲學之父,他的哲學的第一原則是:“我思故我在”。把我的“存在”和“本質”歸結為“我思”。正如趙敦華先生所說的,形成了與以往《圣經》宣揚的上帝是唯一的神圣主體,其主體無所不包、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形成兩個不同方向的反差。這與中世紀“我是我所是”的形而上學的基本信條是根本對立的,即笛卡爾講的“我思故我是”,有認識論意義上的“自我”代替了神圣主體,從而產生價值體系上的變化。人道主義用“人”代替“神”作為最高價值,開啟了由人的理性戰勝非理性、無理性和反理性的先河。
(三)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哲學極端化。
以尼采為代表的一類以徹底排拒的方式反對神圣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價值觀取向。在宣布了“上帝死了”以后繼而宣布“人”的死亡。后繼者更是排拒一切價值觀,以無中心、無差別、無本質的游戲方式對待原有的規范道德;用否定、批判、破壞的手法沖擊神圣文化和現代價值體系,呈現了現代主義的極端化,從而希望回歸到流動的、混飩的、無約束的狀態。
二、 差異說
把希臘哲學、希伯來宗教精神及羅馬法的法治精神混合在一起說成是神圣文化的基礎,若以狹隘的基督教徒觀念來看,他們是會大為反對的。就像早期教父德爾圖良(Tertullian),把哲學斥為“人和魔鬼”的學說。以其所代表的忠實崇信的一類信徒,因其排斥“異端”學說的孤立性,并不妨礙作者倡議三個民族精神的整合說。
若從中世紀向下探索,則即使是作者強調的現代性世俗文化,其主流的仍是對基督教中上帝信仰的種種論證和申說,其中包括笛卡爾、萊布尼茨、貝克萊,康德、謝林以至黑格爾等等。縱然含有許多啟蒙主義的現代光芒,但也只是對中世紀上至教皇,下至神甫不擇手段聚斂財富,腐化墮落的生活,甚至將宗教命令變成了殺人的殘忍工具而進行的理性批判,無非是從其他角度再次建立信仰高度,純潔教義而已。
不管科學技術發展到什么程度,也不論其他的藝術形式發展到什么階段,人們的信仰要求是不能中斷的,這不僅僅是形而上學的研究的任務,而真正是絕大多數人的精神內在需求。譬如康德被休謨的懷疑論及盧梭的哲學口號驚醒后,直接由天文物理學研究轉向對絕對自由、靈魂不死及上帝存在這三大命題的深入探討就代表了許多人的心聲,而哲學體系的成不成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假如神圣文化這個假設能夠成立,則時間跨度可以講是西方有了哲學以來,一直到后現代時期以前,所有由信仰及理性交織形成的文化體系。后現代主義恰恰就是對此以前的價值體系所進行的懷疑、批判、否定和破壞。“絕對推翻一切辯證法、一切神學、一切目的論和本體論”的口號也是建立在這樣的人文基礎上才喊出來的。
事物的發展就是如此辯證和矛盾,不破不立。小破小立,大破大立。后現代哲學家的大破精神來源于以前的那些文化病狀,在這一點上也不能將后現代主義思潮歸結為是完全開錯了藥方。雖然傳統的信仰及理性都面臨著危機,至今沒有人為此找到更好的哲學出路,但不能因為這樣的結果而指責他們和完全否定他們。也許大破的精神是必要的,其實在這樣的危機重重的哲學背后,更可能會牽引出理性與信仰能完全一致,而沒有任何矛盾和疑惑的真理性哲學來。倘若如此,這未嘗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是再換一個角度,有必要對基督教及基督教哲學的神圣性作一次認真的考察。作者于文中提到:“宗教雖然是神圣文化的起點和基礎,但并不是神圣文化的全部。” 這句話是否包含以下三層意思:一是宗教必然是神圣文化;二是宗教既然是神圣文化,其起點和基礎是由其決定,宗教為神圣文化內核之當然;三是除宗教外,還有其他的神圣成分,即作者所講的希臘哲學的理性精神及羅馬的法治精神。除此第三條外,我們尤其愿意對第一條和第二條的宗教的神圣性做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看看可否得到其基督教非但不是什么神圣的,反而應是世俗性的說明。
展開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的歷史,你會發現是一部充滿著關于信仰與理性關系問題的爭論的歷史,里面充滿著矛盾、疑惑、斗爭和調和的說辭。
基督教宣揚的是“原罪說”。保羅的解釋是:上帝創造人時,人本來是善良的。但亞當的罪過從根本上毀滅了人,以至于從此以后人再也沒有能力擺脫罪孽了。僅此一事,理性就會追問,既然上帝造人是本著自己的形像造的,而上帝又是全能全知全善的,那所造的人也一定是善良的,如保羅開始理解的那樣,人一開始不可能是“原罪型”的,罪惡只可能是后天形成的,故人性本善。那么,亞當的惡是從何而來?難道也是上帝所造?否則惡的源頭在哪里?如果說是魔鬼撒旦的誘惑,那么這個魔鬼又是誰造的?依照《圣經》,這個世界的一切不都是上帝所造嗎?如果有些東西不是上帝所造,那么即使存在這個上帝,上帝也就不可能是全能的了;三是依照原罪說,人的罪孽是一場無法擺脫的厄運,而人在根本上就不可能不干壞事,這就無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也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種原罪說與自由的理性,一開始就陷入了矛盾的對立之中。
后來奧古斯丁接過保羅原罪說的棒子,雖然曾一度懷疑在上帝無與倫比的權利中,人的自由無法存在這一巨大的矛盾,但他終究跨越不過上帝絕對的權力界限,俯首承認是“上帝安排著,上帝決定著,而上帝的安排又是神秘的,上帝的決定無法探究。”? 尤為典型的是神學家德爾圖良絕對將信仰與理性對立起來,他大聲疾呼:“我們在有了耶穌基督之后不再需要奇異的爭辯,在欣賞了福音書之后不再需要探索。” 并說“上帝之子死了,這是完全可信的,因為這是荒謬的。他被埋葬又復活了,這是確定的事實,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荒謬”和“不可能”是理性對信仰的否定判斷。但正基于這種荒謬和不可能性,提出:“基督教關于耶穌死而復生的教義并不因此而喪失真理性。理性的排斥反倒顯出信仰的確定。因為信仰與理性是正相反對的。”
十九世紀基督教思想家克爾凱廓爾同樣出于對理性主義的不滿和反抗,提出“荒謬是衡量信仰的尺度” 的思想。并且指出:“信仰本身充滿著矛盾。比如,上帝既是神又是人,個人的存在既是有限的,又趨向于無限的上帝。理性不能解釋這些矛盾。因此,荒謬感始終伴隨著信仰。荒謬感并不削弱、損害信仰,因為信仰是個人面對上帝做出的選擇,荒謬感越是強烈,而越能按照上帝的命令做出抉擇,恰恰表明了信仰的堅定與強烈。在此意義上,荒謬感是信仰強度的標準。被荒謬所衡量的信仰包含著最確定的真理。” 我們說,這些思想家們的確荒謬。強行為上帝存在而進行荒謬的辯護,其實也是一種病態的思辯,似乎在用一種強制的理性來掘斥合理的理性,顯示著詭辯的邏輯。如果這些詭辯都能夠成立,那么世界上發生任何罪惡行為都可算是為了維護信仰的真理性,若依此邏輯,后現代主義的解構、游戲及破壞也應是上帝真理的一部分,那就不存在什么極端性的問題了。
到十二世紀,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雖沒有這么極端,但仍然主張信仰高于理性,理性服從于信仰。雖說“神學和哲學都是關于上帝的同一真理,但論證這一真理的途徑不同,神學以天啟為前提,哲學則用理性證明自身的前提。但不管天啟還是理性,都有同一來源,天啟來自上帝的恩典,理性是上帝賦予人類的自然能力。信仰與理性的關系實質上是恩典和自然相輔相成的關系。” 從而可見信仰永遠居于主人地位,理性的從屬性只是用來證明上帝存在的工具。
現代托馬斯主義者馬利坦(J·Makitain)按照信仰與理性關系,構造了一個“知識的等級”,“理性范圍的包括實驗科學、自然哲學知識和形而上學這樣一個由低到高的等級。在理性知識之上還有超理性的知識,即信仰領域,也包括神學、神秘經驗和天福境觀(beatifc vision)這樣一個由低到高的等級。” 二者關系及高低等級在馬利坦這一目了然。這可以說是西方宗教和哲學的主流觀念。
啟蒙主義以后,雖然呼吁理性的聲音越來越強,理性主義者從宗教的背后站到了前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精神,對宗教的愚昧無知性予以了堅決的批判,但主流哲學家們在骨子里還是為了上帝存在的信仰而不遺余力的進行理性辯護和證明。這從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乃至康德、黑格爾的哲學特質可以得到說明 。其中康德是一位代表人物,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似乎將信仰與理性劃清了界限,但其對理性神學的批判的目的只是限制理性,從而給信仰留下了地盤。而哲學著作中艱深晦澀的思辨推理似乎是用純粹理性構筑了科學這座大廈何以能夠成立,但用理性不可知的“物自體”的公設其實是為上帝存在的證明預備其空間,再通過自己設計的“實踐理性”將絕對自由、靈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這些魂魄請進來,完成了自己的哲學體系。
馮達庵大阿阇黎在《佛法要論·佛教真面目》序言里講:“吾人所能感見之事無窮無盡,括其要不出精神、物質兩界。由精神演成無量眾生;由物質演成無邊世界。根本究從何來?此古今學者勞心焦思終不能解決之兩大問題。有強作解釋者:或以神話點染之,普通宗教家之手段也;或以意識推測之,普通哲學家之眼光也。高下雖殊,總于真理不相應。然宗教點染,有時也根據特殊事跡,惜無義理以調和之;哲學推測,有時也符合局部正道,惜無實習方法證明之。故對研究者之要求,皆不能如量應付。根本問題,遂成為人類最大之謎矣。”但謎有可解之法,卻要真修實習之道。佛教雖被世人俗稱為三大宗教之一,其實從根本上研究,與西方基督教之世俗性絕不相同:①基督教崇拜一神即“上帝”。佛教無崇拜之神;②基督教尚原罪說。佛教眾生本來佛性;③基督教中神與人永存差別。佛教眾生平等;④基督教罰與贖為上帝之強制力。佛教自由信仰,自愿習道;⑤基督教只認己教為正教,其他皆為異端。佛教含融一切世出世法,又不取不舍不破一切世出世法等等。在此不能廣加分別。但有必要將佛教的特質作一簡要分析,以此不同角度提供未來哲學中的信仰與理性的選擇方向。
(一)佛教既不是有神論者,也不是無神論者。佛法追求的是無上般若智慧,以此智慧能斷一切煩惱,其中包括生死煩惱。而其智慧有本有智慧和修生智慧之分。本有智慧是指所有眾生都有如此自性智慧,此智又稱根本智,只是無明業力覆蓋不現而已。修生智慧是指按佛教指引的方法,聞思修習,將無明業障清除,來顯現其根本智慧,此又稱為后得智。如同礦里雖有黃金,如果不經冶煉,也難以真正得到金子一樣。這里追求的智慧,人人本有,從此義上講,沒有眾生與佛的差別,是生佛平等的。因此,無一切迷信之說。佛教中談到的天神地神等,也只是與人一樣,是六道眾生之一類,只是不同的生命狀態而已,同樣是有生死和其他煩惱的凡夫。故基督教中的上帝與中國儒道講的天帝都是沒有脫離六道生死的眾生,說基督教之非神圣性,而是世俗化宗教,依據在此。由此可知,佛教沒有崇拜神靈之說,也沒有什么絕對命令的限制,也不存在人與神永遠隔河相望,而難以平等。既然是信仰的眾生人人本有的自性即佛性,并且能依靠理性智慧的方式獲得,那么佛教的平等觀、理性觀、自由觀就可以清晰顯現出來。
(二)佛法講的“緣起性空”的道理,是蘊含于人人所能見到了知的世間事物之中的,并無什么神秘之處。若極簡單地概括佛法的全部,則這“緣起性空”說可以囊括殆盡,無一遺漏。緣起觀是專講世間因果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單一原因而成,而是由不同因緣和合而成。比如豆子生成豆芽,要有種子因,又有陽光、水土和人工等各種的增上因,中間還不能毀爛,這是相續因。故佛法中講四種因緣:親因緣,所緣緣,增上緣,等無間緣。四緣聚則興,四緣散則滅。世間一切法都呈成、住、壞、空四相,就是因為緣生緣滅造成的,這是人人都能曉得的道理。但其難點在于,雖知一切法由因緣生滅,卻不知因緣生法而法無自性的甚深道理。若諸法有自己的本性存在,則諸事就不能變化,也就沒有生生滅滅的現象了。
(三)佛法中講的緣起即性空、性空即緣起,不是指兩個世界,即此岸和彼岸。這與基督教的人間和天國不同。而是說在眾生沒有去除執著時,產生的顛倒妄見,會將世間一切執為實有,產生迷惑。比如有我有他,有生有死。從此愛則欲取,憎則遠離,所有煩惱應運而生,成愚癡無慧的眾生相狀。當修行智慧顯現時,同樣的世界,因心清凈能離一切煩惱。凡夫所受煩惱為此岸,智者所證快樂為彼岸。
第四,佛教常言理理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何謂也?這是理解佛學及自然界的一大樞紐,自然界中表現的物質和精神現象皆是識的作用。上段講過眾生除人們日常了解的眼、耳、鼻、舌、身、意之六識外,尚有微細二識即第七末那識和第八阿賴耶識。而第八阿賴耶識又稱諸識之王,俗稱神識。能藏一切善惡諸法之種子,故又稱含藏識、種子識等,相當于西方哲學或宗教中講的靈魂。但其含義不同,西方所謂的靈魂是不變的,而阿賴耶識卻剎那變化,因為佛學中所說的一切有為法都在變化之中,沒有恒存的事物。第七末那識是對第八識的相分的認識,因為第八識剎那變化,而第七識又要清楚認識,則對任何變化都要審量思議,則第七識會把持第八識恒審恒思而不放舍,于是就形成了自我長存一樣的感覺。導致有人我之分,主體與客體也對境角立。因對立故,所有一切的矛盾由此而生。這又反過來染污前六識和第八識。若破第七末那識的恒審執著,則一切對立狀況必然消失。七識因不執著而清靜成智,轉成平等性智,一切法相可平等齊現。第八阿賴耶識因第七識破執著后也轉清凈成大圓鏡智,以前識中含藏所有的種子皆成一切種性,能與大圓鏡智中隨緣平等顯現出來。第六識因第七識之清凈也顯清凈,能智照妙觀一切法相,故又稱為妙觀察智。前五識隨后三識清凈而清凈,能于色、聲、香、味、觸任意隨緣操縱,利益一切眾生。故佛經言:“心轉物即如來,物役心即凡夫。”而前五識轉識成智又稱成所作智。由上略述佛法之大概,但可知佛法是真平等,由平等性智呈現一切法相故;是真包容,由大圓鏡智含融一切法故;絕對真理,由妙觀察智照見一切法理故;是真自由,由智心能轉一切物體故;是真智慧,由四智成一切種智故;是真慈悲,因利益一切眾生故;真道德,自由趣道而得一切大自在故。因此佛法涵蓋包容科學、哲學、藝術、宗教等等一切學問而無對立矛盾,且能超越世間種種有為之法,并予以指導之。佛法不崇拜任何一神或多神,但崇信老師給予的真理而自求解脫一切煩惱,故佛法的信仰是徹底的“尊師重道”。其信仰與理性的完全融合為佛法的不二之學,其學、其義、其理與西方文化之對話最具有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趙敦華:《西方哲學的中國式解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479頁,第4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