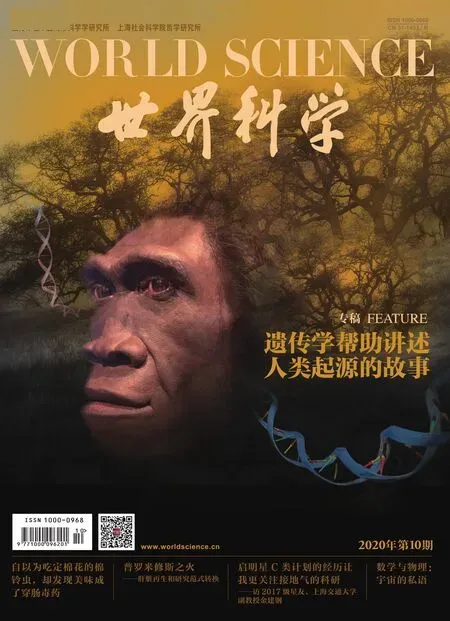普羅米修斯之火
——肝臟再生和研究范式轉換
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他用黏土創造了人類,并且違抗宙斯的命令,盜火給了人類,最后使得自己在高加索山脈上接受宙斯的懲罰:每天惡鷹會來啄食普羅米修斯的肝臟,而他的肝臟又會在夜晚重新生長出來。為了人類能擁有光明和溫暖,他必須日復一日地忍受這種痛苦。這個神話刻畫了普羅米修斯為人類獻身的英雄主義,普羅米修斯之火也成了引導人類進步的象征。有意思的是,這個神話還描述了一個生命的奇跡,即肝臟的強大再生能力。
肝臟是體內最重要的器官之一,發揮著代謝、分泌、解毒等多種生理功能。肝臟從大體上來看,是一個相對均質的組織。從具體的構建細節來看,肝臟是由一個一個的肝小葉作為基本功能結構單元構成的。肝小葉可以大致想象成一個多邊形的結構,中心區域是中央靜脈;幾個頂點是匯管區存在的地方,匯管區內有肝動脈,門靜脈和膽管。肝細胞和膽管上皮細胞是構成肝臟的主要細胞類型,前者是肝臟內最重要的功能細胞,占肝臟總重量的約80%。肝細胞從中央靜脈排列成索狀,一直到匯管區。動脈和門靜脈的血液經過肝索間內皮細胞形成的肝竇中流入中央靜脈。肝細胞和肝細胞之間會形成膽小管的亞細胞結構,肝細胞分泌的膽汁流入膽小管,通過互相間連接的膽小管,最后匯入由膽管上皮細胞構成的膽管中。肝臟中還有一些免疫細胞、星型細胞等,分布于血管內皮細胞周圍或者肝竇間隙中。
哺乳動物的大多數組織器官都缺乏再生完整器官的能力,但肝臟是個例外。在極端情況下,肝臟被切除高達70%后,殘余的肝組織仍然可以在2周左右的時間內再生出整個肝臟器官來(盡管其外觀的大體結構并不能被再生出來)。在其他一些急性化學性損傷過程中,肝臟也往往能夠非常好地再生損傷組織。但當受到持續性損傷時,比如慢性病毒感染、脂肪性肝炎、長期藥物肝損傷等,肝臟的再生修復能力會遭到破壞,常會出現肝纖維化等病理狀態,嚴重時會導致肝硬化和肝衰竭,危及病人的生命。
肝臟是再生研究的熱點器官
由于肝臟的強大再生能力,并且肝臟再生與相當多的肝臟病理變化相關,因此肝臟一直是再生研究領域中深受關注的器官。肝臟再生過程有相當多非常有意思的科學問題,比如:再生過程的誘導因素是什么,而組織完成再生后,整個過程又是如何被恰到好處地終止;再生過程的血管和膽管重建問題;免疫細胞對肝臟再生的作用;衰老狀態下,再生能力下降的原因等等。但在這些問題中,一個核心的關注點是,肝細胞作為最重要的功能細胞,是如何被再生出來的,其細胞來源是什么,涉及哪些調控的因子?
20世紀中后期,對肝臟再生的研究主要是形態學描述,比如利用光學顯微鏡和電子顯微鏡,進行組織結構和細胞形態方面的觀察。研究者主要采用肝臟切除模型來研究肝臟再生。在這個過程中,觀察到在很短時間內,肝細胞就出現了內質網變形、線粒體減少等變化;在肝臟切除大約24小時左右,肝細胞出現了細胞分裂象,提示肝細胞正在發生增殖。隨著同位素標記和核酸標記技術的發展,人們可以真正跟蹤肝細胞增殖過程中細胞遺傳物質——脫氧核糖核酸(DNA)的復制,從而可以了解肝臟再生的細胞來源。利用嚙齒類動物模型,研究者發現在肝臟切除后16小時左右,肝細胞開始出現DNA的復制,大約在24~36小時達到高峰;當再生完成時,所有肝細胞發生了一次或者兩次增殖。基于這些研究,領域內普遍認為,在肝臟再生過程中,肝細胞的自我復制是再生的主要細胞來源。
在對肝臟切除再生過程的一系列研究中,利用生物化學的分離純化和檢測手段,人們還發現了一系列在再生過程中有誘導生長作用的因子和激素類物質,比如上皮細胞生長因子(EGF)、肝細胞生長因子(HGF)、甲狀腺素、去甲腎上腺素等。這些因子的單獨使用,在體內和體外實驗都可以看到對肝細胞增殖有部分的誘導作用。不過那個時代的研究缺乏遺傳學動物模型,因此這些因子體內的確切作用機制,不是非常明朗。有意思的是,對肝臟再生過程進行組織學分析,可以觀察到不同形態大小的肝細胞,而體外培養這些肝細胞時,似乎也看到它們的增殖能力不盡相同。也由此提出肝臟內不同肝細胞可能增殖能力不同,對再生的貢獻大小不同的假說。
尋找肝臟干細胞
在胚胎發育中,大家發現了胚胎肝臟干細胞的存在,其發育來源于胚胎早期形成的內胚層組織。在肝臟形成過程,這些干細胞可以進一步分化為兩類不同的上皮細胞——肝細胞和膽管細胞。20世紀90年代,隨著實體組織中成體干細胞概念的逐步形成,肝臟再生領域中也有人提出成體肝臟中是否存在肝臟干細胞。這些成體肝臟中的干細胞可以在損傷后貢獻到肝細胞的再生,以及膽管細胞的再生。因此,研究者們參照其他器官,特別是血液組織造血干細胞的研究方案,利用在細胞表面特異表達的分子,分離純化可能的成體肝臟干細胞。這個研究的過程參考了胚胎發育時期肝臟干細胞的表面特異分子。
最后的結果是,大家發現了近十種不同的表面分子,這些表面特異分子可以標記互相間重疊程度或大或小的若干類群細胞。利用譜系追蹤技術,不同實驗室在各自研究的損傷模型中,發現這些細胞似乎都能貢獻到肝臟再生中去。利用肝細胞移植技術,大家還發現這些細胞多多少少也都可以在移植后再生。但是,很難想象成熟肝臟中存在這么復雜的干細胞體系。因此,成體肝臟干細胞是否存在,讓研究人員產生了極大的困惑。
另一方面,在肝切除模型中,早期有人對肝臟嘗試了連續的切除和再生研究。發現可以進行多達12次連續的肝臟切除和再生。在20世紀90年代,大家也逐步建立了肝細胞移植的模型,基本思路是構建一些功能缺陷肝臟動物模型,移植野生型動物的肝細胞后,這些野生型的肝細胞可以在肝臟中定植和擴增。利用這些肝細胞移植模型,大家發現肝細胞可以長期連續移植。通過相應的計算,估計肝細胞可以擴增30多次,也就是大約10億倍左右。基于這些發現,有人提出了肝細胞可能并不是終末分化細胞,其本身是否就是單能干細胞(unipotent stem cell)的假說。基于這個假說,一直尋找的肝臟干細胞可能就是成熟肝細胞;不過,這個假說也指出,這樣的單能肝臟干細胞很可能就無法貢獻到膽管細胞了。
盡管成體肝臟干細胞的尋找并不順利,或者說讓人非常有挫敗感,但在對肝臟干細胞的探索過程中,還是涌現了大量的新數據和新假說。比如,利用移植技術,基本否定了成體組織內存在多潛能干細胞的概念;也否定了血液細胞可以轉換為肝細胞的假說。另一方面,利用這些新發現和新技術,推動了一些成果的臨床轉化研究。比如,研究者們發現了胚胎肝干細胞的培養方法,提出了肝細胞移植治療的概念,建立了肝細胞移植的動物模型。此外,也開始初步嘗試生物人工肝的大動物和臨床研究。但是,由于肝細胞培養和分化的技術難題,而臨床治療所需的細胞數量極大,因此,這些技術都沒有真正實現臨床的治療應用。
肝細胞屬性轉換研究的興起

21世紀以來,隨著細胞譜系遺傳標記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研究者們可以更為精準地跟蹤細胞在體內的譜系變化。到2010年前后,利用了一系列高度復雜和精準的遺傳標記方法,若干個實驗室陸續確認再生過程中的肝細胞都是來自原有的肝細胞,從而基本否定了肝臟干細胞的存在。在同一個時期內,隨著獲諾貝爾獎的誘導性多能干細胞(iPSC)技術的建立,以及中國、美國等學者成功實現了將成纖維細胞體外轉變為其他類型功能細胞,不同細胞屬性間可以發生轉換(包括細胞去分化和細胞轉分化)這個概念得到廣泛認可。與此同時,一些關于體內損傷再生過程的細胞屬性轉換的研究也開始出現,主要是在腸道、胰島等上皮組織中發現細胞屬性轉換對組織損傷修復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有研究者開始考慮肝臟是否也存在通過細胞屬性轉換方式實現損傷后的組織再生。因此,利用遺傳標記方式,對損傷后肝臟再生過程進行詳細的研究分析。研究者發現肝細胞在某些急性損傷后,的確會發生去分化,獲得胚胎肝臟干細胞的某些特征;并且這些細胞在損傷后修復過程中,可以再次分化為肝細胞和膽管上皮細胞。這些經由肝細胞“去分化-再分化”的再生方式可以貢獻到30%以上的肝組織再生。由于這個去分化過程十分短暫的,因此,用傳統方法無法很好地捕捉到。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很長一段時間,研究者看到了多種所謂的“肝臟干細胞”——很可能大家標記的細胞處于去分化過程的不同階段。更為有意思的是,中國和英國的科學家利用細胞譜系標記技術率先證明,在肝細胞增殖受到抑制的條件下,肝細胞的再生可以由膽管細胞而來。在嚴重的長期損傷下,大約50%以上的再生肝細胞是來自于膽管細胞。雖然膽管細胞形成肝細胞的過程到底是直接轉分化,還是去分化后再分化,抑或其本身就具有兼性干細胞的特質,仍然有爭論,但是這個發現,給肝臟再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模式。
肝細胞是實現細胞移植治療的關鍵細胞。雖然肝細胞在體內具有強大的增殖能力,但是在體外培養擴增,一直到最近幾年都沒有完全解決,這也是造成臨床肝細胞移植治療遲遲沒有重大進展的原因之一。上述這些細胞屬性轉換現象的發現和概念的建立,特別是去分化的概念提示大家,是否可以將分化的肝細胞先進行去分化為肝臟干細胞后,再實現體外擴增肝細胞。因此,中國、荷蘭、日本和韓國的學者利用這一假說,率先克服了成體肝細胞無法在體外培養擴增的技術難題,實現了肝細胞的體外獲得,為肝細胞移植治療等提供了扎實的技術支撐。
從這些研究歷史可以看到于2010年前后,中國學者開始逐步加入到全球肝臟再生研究的第一梯隊中,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本土原創貢獻。這完全是因為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對科研投入的加大,才能使新一代的本土研究者能夠有機會在相關領域內做出中國人的貢獻。可以預期,我國的科技人員未來會在各個前沿基礎和應用研究領域獲得更多出色的原創成果,也期待相關研究成果能夠早日實現產業化和臨床應用的突破,為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健康謀福祉。
新技術促進肝臟再生研究
從上述對肝臟再生研究的回顧,我們大致可以看到知識發展的某些規律性。新發現的產生,常常伴隨一些無法解釋的現象,一些未被解答的科學問題。利用時代發展中全新的技術方法,結合本領域或者其他領域一些尚未被完全證實的新概念范式,逐步產生了一些新的發現。而新的發現必然帶來新的認知、新的突破和新的應用(這些新認知、新突破、新應用,有些是可以預測的,有些是無法預測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困惑、新的不解,這又推動研究者繼續探索新的方向和領域,肝臟再生也是如此。
肝小葉是肝臟的基本功能結構單元,長期以來,大家知道從匯管區到中央靜脈,肝細胞的代謝表達譜不同。在肝細胞移植過程不同區域肝細胞移植后,可以形成所有的肝細胞,因此這種不同被認為是微環境誘導的差異,并沒有聯系到肝臟再生中去。隨著譜系追蹤技術不斷深入,研究者們可以更好地標記不同區域的肝細胞。這時,大家發現肝臟不同部位的肝細胞似乎貢獻到再生中的能力不同。近來,隨著單細胞測序技術的引入,帶來了大量的數據,從而使得數據源頭驅動、結合生物學機制研究的范式,也在肝臟再生研究領域成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和體系。2015年前后,單細胞表達譜測序技術開始逐步成為實驗室的常規技術。與此同時,有不少研究者對肝臟不同部位的肝細胞,不同損傷狀態下的肝細胞進行了單細胞測序,發現的確肝臟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均質的組織,實質上在不同組織區域,存在著很大的表達差異。因此,這就對肝臟的再生提出了全新的挑戰,這些空間位置不同,表達譜不同的細胞,在再生中是如何作用,是否都發生一樣的變化?在再生過程中,又是如何重新形成的?在特定病理條件下,如何重塑微環境?如何合理精準地動員這些細胞貢獻到再生,并且避免肝臟疤痕(纖維化)的形成?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和了解,很可能把我們對肝臟再生帶入到一個全新的領域,非常值得期待。
肝臟再生的普羅米修斯之火
回溯過去半個多世紀肝臟再生的歷史,在探索未知的前沿,是一條充滿荊棘的光榮之路,艱辛曲折然而意義深遠。我們對自然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我們現有的技術和工具;技術和工具的局限性,使得很多探索無法深入并企及細節,相關的結論和由此構建的理論框架也就必然會在某些方面存在困難。框架性理論的構建一方面指導了我們更高效地對未知的探索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常常會使我們對新的認知造成局限。所以那些全新的技術體系,那些反復出現、無法解釋的現象,不管是新的還是舊的,成為那些活躍在第一線的先鋒們的關注點。只有那些勇于打破成規的行動者和真正深刻的思考者,如同普羅米修斯給人類帶來火種,才會給整個領域一次又一次地帶來全新的觀察和顛覆性的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