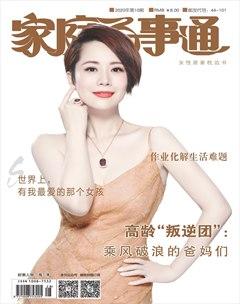不再厭惡自己,女性才能獲得自由
陶瓷兔子愛麗絲
一位女友跟我講了她前段時(shí)間經(jīng)歷的一場(chǎng)年度內(nèi)心大戲,是關(guān)于要不要生孩子的。她有個(gè)談了四年的男朋友,比她小五歲,還在國(guó)外讀書。她本來(lái)打算陪父母過了年就飛去跟男友團(tuán)聚,沒想到卻被疫情困在了家里。從那一天起,“早點(diǎn)要孩子”就成了她家的單曲循環(huán)。催生的主力軍是她媽媽,每天早午晚飯時(shí),都要軟硬兼施對(duì)她實(shí)施各種洗腦。
“女人本來(lái)就老得快,再加上他還比你小,你不趕快生個(gè)孩子把他拴住,等你人老珠黃了,人家也嫌棄你了,你到哪兒哭去?”“有什么工作是非你不可的?我當(dāng)年不也是因?yàn)橛辛四憔头艞壛斯ぷ鲉幔磕阌X得我活得沒價(jià)值?”“我就問你,你不要小孩,等你老了誰(shuí)管你?”以及最后的撒手锏:“我說(shuō)這些還不都是為你好嗎?啊?”
那聲“啊”整日環(huán)繞在她耳邊,仿佛一個(gè)她永遠(yuǎn)攻不下來(lái)的山頭。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她頭一次做了噩夢(mèng),在夢(mèng)里,她成了一個(gè)白發(fā)蒼蒼的老婆婆,孤家寡人地躺在漏水的房子里,廚房里只有一個(gè)饅頭。“要不就生個(gè)小孩吧。”她跟男朋友通電話的時(shí)候把這個(gè)夢(mèng)講給他聽,他在電話那頭樂不可支:“你孤家寡人?你沒飯吃?我認(rèn)識(shí)的所有人都可能,只有你不可能。你是我認(rèn)識(shí)的生命力最旺盛的人,才不會(huì)把自己弄得那么慘。”
你不是這樣的人。她說(shuō),她是在那一刻忽然明白了為什么媽媽說(shuō)的聽上去都對(duì),但她就是覺得很煩的原因。她男朋友很愛她,她的工作干得很好,她有經(jīng)營(yíng)得很好的生活圈,是個(gè)靠自己也能活得很好的人。可在她媽媽眼里,她作為個(gè)體的獨(dú)特性是不存在的。她不過是無(wú)數(shù)女人中的一個(gè),工作無(wú)聊前途灰暗,要靠孩子才能維系男人的青睞,要靠血緣才能擺脫孤獨(dú)終老的命運(yùn)。她愛她,卻要先貶低她;她為了她好給出的建議,卻要先抹殺她的價(jià)值。
日本作家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一書中寫道:“母親的不如意,與自己無(wú)法改變現(xiàn)狀的無(wú)力感混為一體。她一邊詛咒自己的人生,一邊又將同樣的人生強(qiáng)加給女兒,引來(lái)女兒的憎惡。”厭女并不僅僅是字面上“討厭女人”的意思。對(duì)女人而言,它是女人對(duì)自我的厭惡。這種無(wú)助感經(jīng)過投射,又被千百倍地放大到了同性身上。而來(lái)自同性之間的惡意,才是大多數(shù)傷害的來(lái)源。
我認(rèn)識(shí)一個(gè)做美妝博主的女孩,她說(shuō)她常常在微博留言中被網(wǎng)友罵成篩子。她告訴我,最讓她覺得難過的其實(shí)并不是罵她這個(gè)行為本身,而是當(dāng)她點(diǎn)進(jìn)那些不堪入目的評(píng)論時(shí),發(fā)現(xiàn)至少有70%都來(lái)自女性用戶。她們說(shuō)出來(lái)的那些話,也正是她們反對(duì)的“父權(quán)”和“男性審美”,她們一邊掙扎,一邊把同樣的繩索套在自己的同伴身上。這也是目睹女性相輕最讓人難過的原因。
法國(guó)作家波伏娃說(shuō):“女人的不幸在于被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著。她不被要求奮發(fā)向上,只被鼓勵(lì)滑下去到達(dá)極樂。當(dāng)她發(fā)覺自己被海市蜃樓愚弄時(shí),已經(jīng)為時(shí)太晚,她的力量在失敗的冒險(xiǎn)中已被耗盡。”但女人是天生就懶,就笨,就好騙的嗎?身為女性最大的悲劇之一,就是幾乎所有的誘惑都是以保護(hù)為名,且來(lái)自你身邊最親密的人。媽媽告訴你“女孩要有點(diǎn)女孩的樣子”;姐姐跟你說(shuō)“要留長(zhǎng)發(fā),用香水,涂口紅,才會(huì)有男生追求”;閨蜜說(shuō)“你該減肥了,男生都喜歡白瘦幼”;已婚的朋友勸你“嫁個(gè)有錢人,能少努力好多年”。
如同上野千鶴子寫的那段話:這個(gè)社會(huì)對(duì)女人的歧視是從詞匯的定義上就開始的,例如“太強(qiáng)悍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等。而女人一旦接受了男性規(guī)范化的定義,她就會(huì)放大自己不那么“女人”的地方,于是對(duì)自己產(chǎn)生嫌棄。她們又把這種嫌棄投射給了自己的同伴,這就是“厭女社會(huì)”的根源。
沒有孤零零的自由,也沒有任何人能夠獨(dú)善其身。女性真正能獲得自由的時(shí)刻,就是每個(gè)人不再厭惡自己之時(shí)。
(資源支持:微信公眾號(hào)“天天成長(zhǎng)研習(xí)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