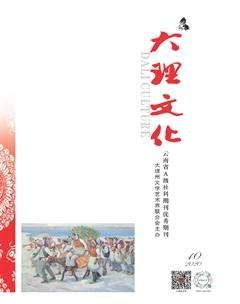滇西,一條名叫漾濞的江



1
最初的時(shí)候,這條江還沒(méi)有被冠以“漾濞”的名字,村莊的人們直接就叫它“江”,彝語(yǔ)讀音“剔比厄”。把一條江稱之為“江”,就像是父母親叫自己的孩子“兒子”或是“閨女”那樣。
江在山下,村莊在山上。從村莊下到江邊,走得快的人半個(gè)小時(shí),背著背子或是趕著牛的人要五十分鐘到一個(gè)小時(shí)。這樣的一段路算不上遠(yuǎn)。夏天,我們常常把牛趕到江邊放牧,然后,每天幾個(gè)小時(shí)在這江邊以及江水里玩耍。
江邊的沙岸上蘆葦茂盛,江灣里柳樹(shù)成排。我們把牛趕到江岸上的蘆葦灘里,或者是半山腰上,之后,一頭扎進(jìn)水里。江水清澈,江面平緩寬闊,站在江的這邊看對(duì)岸的人完全看不清,只大體看得出男女。若是大聲呼喊,喊聲在到達(dá)對(duì)岸之前已被風(fēng)和江聲帶走了大半,去到對(duì)岸時(shí),想必只剩下了模糊的尾音。
我們?cè)诮叺囊惶鞎r(shí)間是這樣度過(guò)的:大多數(shù)時(shí)候,以一叢蘆葦、一棵柳樹(shù)、一個(gè)老樹(shù)樁或者是一塊大石頭為標(biāo)志,劃定一段水域,喊“預(yù)備——起”,從起點(diǎn)跳下水,然后比誰(shuí)最先游到指定的終點(diǎn)。每天重復(fù)這樣的游戲,大家對(duì)經(jīng)常劃定的那段水域都很熟悉,能熟練繞開(kāi)水里的大石以及倒在水底的柳樹(shù)樁,比賽的冠軍也往往就在那固定的一兩個(gè)人中間較量,甚至,在固定的那幾個(gè)人中間,每次比賽的名次大體也是固定的,但大家仍然要一次一次地跳下水,一次一次地重新驗(yàn)證。
有時(shí)候也會(huì)出意外。比如打波的時(shí)候腳不小心碰到了石頭,或是被水里的樹(shù)樁掛到,又或者,被水底無(wú)法預(yù)料的碎玻璃瓶劃傷。最危險(xiǎn)的是漲過(guò)大水之后,水道和水流都發(fā)生了變化,有些原本平緩的地方有了暗漩,暗漩在表面不容易看出,下了水一旦碰上,極容易出危險(xiǎn)。
而更多的時(shí)候,比賽是順利的,可預(yù)期的。一群光鴨子,排成排站在起點(diǎn)上,做好入水的準(zhǔn)備。隨著“裁判”一聲“預(yù)備——起”,撲通入水,幾分鐘后,在作為終點(diǎn)的柳樹(shù)或者蘆葦叢旁陸續(xù)上岸。
這種比賽有時(shí)候也單獨(dú)在高手之間較量。這種較量往往劃定的水域更長(zhǎng),水情更復(fù)雜,風(fēng)險(xiǎn)也更大,若是被大人們看見(jiàn),那是絕對(duì)要挨罵的。比賽的過(guò)程中,參賽高手各自的支持者們?cè)诎渡蠟槠鋮群爸佑凸膭牛奥曔^(guò)江。不用說(shuō),在這種高手較量中勝出的“王者”,其風(fēng)光也絕非一般孩子可比。
終于,在水里玩累了,大家爬到沙岸上,躺在沙地里曬太陽(yáng),稱為曬沙。太陽(yáng)下的沙地特別燙,直接躺上去往往受不住。曬沙最好的辦法是先刨一個(gè)長(zhǎng)形的淺坑,人躺進(jìn)去,用手一點(diǎn)點(diǎn)把沙蓋到身上,最后兩只手再插進(jìn)沙里,只露出頭來(lái)。躺在沙里也還有活動(dòng),那就是講故事或者猜謎語(yǔ),這時(shí)候,會(huì)講故事和會(huì)猜謎語(yǔ)的人又有了另一番風(fēng)光。大約是因?yàn)樘上聛?lái)的緣故,這時(shí)候天總是特別高,云在天上不斷變幻成馬,青蛙,魚(yú),船,兔子,羊群,沉思的老爺爺。身邊茂密的蘆葦被風(fēng)吹得沙沙響,視線里,不遠(yuǎn)處的那棵紅椿樹(shù)高上了云天。
快樂(lè)的時(shí)光總是溜得特別快,很快又是日影西斜。在穿上衣服之前,最后再到江里沖一回,然后上岸,穿衣穿鞋,開(kāi)始“阿黃”“阿黑”“小白”地大聲呼喚各自的牛,把牛找齊,在夕陽(yáng)中一路上坡趕回家去。
也有不那么快樂(lè)的時(shí)候。江邊的沙壩地里,小貴家種了一大片莊稼,小貴爹在山腳搭了一個(gè)窩棚守沙壩。放牛的孩子若是不小心讓牛吃了莊稼,遇上小貴爹還好,把牛趕開(kāi),再囑咐幾句讓你把牛看好。若是不巧碰上小貴媽來(lái),事就大了,她除了當(dāng)場(chǎng)狠罵你一頓,回去還會(huì)一直罵到門(mén)上去,讓家里賠她糧食,這放牛的孩子于是便少不得挨大人一頓罵甚至是一頓打。為此,游水曬沙的中間,我們?cè)S多時(shí)候也要去看自家的牛,千萬(wàn)不敢讓牛吃沙壩地里的莊稼,尤其不敢讓小貴媽碰上。
其實(shí),不放牛也還有一件事可以去江邊,那就是撈海草。海草可以喂豬,只要說(shuō)是去江里撈海草,我奶奶往往也能同意我去。江里的海草多得永遠(yuǎn)也撈不盡,柔柔地、一片一片地飄擺在清清的江水里,甚至游水的時(shí)候,不小心還會(huì)被這些海草絆住腳。我們是這樣撈海草的:一到了江邊,先把海草撈上岸來(lái)曬著,玩的中間,記得再把海草翻曬幾次,經(jīng)過(guò)幾個(gè)小時(shí)的時(shí)間,海草上面的水氣已漸漸晾干。晾干了水的海草,一開(kāi)始背上的時(shí)候不覺(jué)得重,尤其是在江邊的那一小段平路上,我們背著籃子,輕快地說(shuō)笑。只是,一等上了坡,那籃子便慢慢重起來(lái)了,一路走,籃子里的海草像是被人偷偷又浸了水,越來(lái)越沉,開(kāi)始的時(shí)候走一段歇一回,慢慢地,歇的次數(shù)越來(lái)越多。天色漸漸暗下來(lái),背上的海草背得人腳抖手軟,村莊在望,卻仿佛遙不可及。心里暗想著,以后再也不去江里撈海草了。可是,等到第二天,有同伴來(lái)約的時(shí)候,把不住又去了。
秋天江上起霧的早晨,是翻爬沙蟲(chóng)的好時(shí)節(jié)。寬闊的江岸上,半潮的沙石間,隨便翻起一塊石頭就有爬沙蟲(chóng)鉆在底下。也弄不清為什么,沒(méi)有石頭的全沙里往往沒(méi)有爬沙蟲(chóng),而非得要是石頭下面的沙里才有,并且,西瓜大到臉盆大的中等石頭下面最多。小的爬沙蟲(chóng)顏色淺褐,越大的顏色越深。長(zhǎng)足個(gè)的爬沙蟲(chóng)大如手指,顏色灰黑,頭甲剛硬,鉗角尖銳,兩排鉗足行動(dòng)迅速而有力,若是經(jīng)驗(yàn)不夠老到的人往往會(huì)被它頭上的鉗角夾到手。而慣于翻爬沙蟲(chóng)的熟手,背一個(gè)窄口的小竹簍,天亮即到江邊,一上午能翻一滿簍。
剛翻回來(lái)的爬沙蟲(chóng)需要在水里養(yǎng)幾天,用油煎吃的時(shí)候才沒(méi)有泥味。煎爬沙蟲(chóng)是一道美味,喝酒的人尤其喜歡拿來(lái)下酒。另外,吃爬沙蟲(chóng)還可以治孩子夜尿,這事說(shuō)不清原理,但確實(shí)有效。村莊的人們還會(huì)把爬沙蟲(chóng)腌成酢,記得是將爬沙蟲(chóng)在開(kāi)水里焯過(guò),洗凈晾干,拌上鹽,拌上細(xì)包谷面,在土罐里一層層壓實(shí),封口腌起來(lái)。腌魚(yú)酢的方法大體也是這樣,只不過(guò)魚(yú)應(yīng)該不能在開(kāi)水里焯過(guò)。
這爬沙蟲(chóng)的去來(lái)一直是一件神秘的事。秋天,江上起霧的時(shí)候,爬沙蟲(chóng)就出現(xiàn)在江岸潮濕的沙石間,并且,今天翻過(guò)的地方,明天同樣還有,可謂是翻之不盡。過(guò)一個(gè)季節(jié),進(jìn)入冬天,爬沙蟲(chóng)就神秘消失了,沒(méi)有留下任何可尋的痕跡,直到第二年的秋天霧起,它們又重新出現(xiàn)在江岸的沙石間。另外,爬沙蟲(chóng)也不是各處都有,有人考證說(shuō),這爬沙蟲(chóng)只在漾濞江流域才有,在別的地方?jīng)]有發(fā)現(xiàn)這種生物生存的痕跡。這事或許不能絕對(duì),但爬沙蟲(chóng)不是哪里都有這是肯定的。
除了有爬沙蟲(chóng),這江岸上還有許多東西,這當(dāng)中有許多是從我們不知道的上游沖下來(lái)的。記得有一回,我嫂子的妹妹阿四在江邊撿到一只大紅色厚底粗高跟拖鞋,顏色紅得跟剛殺出來(lái)的豬血似的,鞋子倒是還好,就是只有一只。四姐人又妖精,有時(shí)候套了那只拖鞋出來(lái),另外一只腳光著,走路的時(shí)候一步高一步矮地,像個(gè)人造的瘸子。
我長(zhǎng)大后才知道,四姐在江岸上撿到紅拖鞋的那個(gè)年代叫八十年代。那個(gè)年代流行穿喇叭褲、花襯衣,流行燙爆炸頭,還流行穿那種紅得像豬血似的厚底粗高跟拖鞋。一個(gè)時(shí)代的流行元素,被江水沖著,沖到了我們村莊下面的江岸上。但那時(shí)候我們不知道。那時(shí)候,我們只知道我們的村莊。
歷史課本教給我們,古代世界最初的文明都在大江大河的流域誕生,并由此不斷擴(kuò)大繁衍。以此告訴我們,江河除了孕育文明,還能不斷傳播文明。
那只20世紀(jì)80代流行的、沖到我們村莊下面江岸上的紅色拖鞋,大約算得上是一種旁證。
2
沿江下來(lái),一路的江岸上有許多沙壩地。屬于我們村莊的沙壩地有兩塊,兩塊沙壩地之間上下相隔大約五里。
我們常游水的那一段大沙壩是小貴家的,耕種的面積大約二三十畝,周?chē)戈惯€有一些沒(méi)有耕種的部分,全部長(zhǎng)滿茂密的蘆葦。這沙壩地里大季種玉米,春末種,秋末收;小季種紅花,收完玉米便跟著翻地種下,年后,綠油油的沙壩地里開(kāi)出無(wú)數(shù)橙紅色的紅花,遠(yuǎn)看去,就像無(wú)數(shù)橙紅色的星星落在那碧綠的紅花地里。
似乎,這沙壩地里也種過(guò)甘蔗,以及別的什么作物,但印象中最多的還是種玉米和紅花。聽(tīng)老人說(shuō)過(guò),這沙壩地是集體時(shí)候就開(kāi)始種的。后來(lái)變成小貴家的,不知道是集體把沙壩地分給了小貴家,還是這沙壩地被集體遺棄,然后讓小貴爹給撿了起來(lái)。這個(gè)問(wèn)題我一直沒(méi)弄清。
小貴爹守沙壩的窩鋪在地頭上,緊倚著山腳,人字形的窩鋪矮矮地,也就門(mén)口還可站人,進(jìn)到里面得彎著腰。窩鋪里一張兩頭用木墩墊起來(lái)的矮鋪,中間一個(gè)火塘,火塘靠里放著布袋和鍋灶什么,布袋黑漆漆的,不用說(shuō),里面放的是小貴爹的口糧——包谷面或者包谷糝。如果這窩鋪里還有一點(diǎn)油,那得放在不能一眼看見(jiàn)的地方,怕丟——村莊里每一個(gè)守地的人都是這樣的。
小貴爹名叫四十五,不用說(shuō),這名字一定是依著他出生時(shí)家里某位老人的壽歲起的。在村莊里有一種傳統(tǒng),就是家里某個(gè)孩子出生時(shí),常依著家里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壽歲給孩子起名,若是太爺太奶、太公太婆還在,自然先依著更長(zhǎng)的。我一位小表兄叫七二,我侄兒叫八一,兩個(gè)人都是依著我奶奶在他們出生時(shí)的壽歲起的名。這樣給孩子起名,有兩頭祈福、祈愿吉祥的用意,祝福老人健康長(zhǎng)壽,祈愿孩子健康成長(zhǎng)。
小貴爹是個(gè)沉默和善的人,走路的時(shí)候總是半弓著腰,弄不清他的腰那時(shí)是真的已經(jīng)弓了,還是因?yàn)樘扉L(zhǎng)日久成了習(xí)慣。模糊記得有一兩回,遇上他在窩鋪里攪了一鍋沒(méi)有油的面糊糊,我們這些孩子來(lái)了,他便舀了讓我們吃,碗不夠,就讓兩三個(gè)人端一碗,一人扒兩口。小貴爹做事認(rèn)真,卻動(dòng)作緩慢,與小貴媽的麻利與火爆形成一種很大的反差,為此總是被小貴媽責(zé)罵,而他總是沉默不語(yǔ),或者就是含糊不清地嘀咕幾句。家里孩子又多,小貴他們姊妹六個(gè),生活不容易。大約也就是因?yàn)楹⒆佣啵≠F家才來(lái)種了這片沙壩地。那時(shí)候,這片沙壩地對(duì)于小貴爹、小貴一家的意義是收獲糧食和紅花。紅花是一種中藥,拿到集市上可以賣(mài)錢(qián)。
那些年,小貴爹窩鋪里的生活是貧瘠的,他在這窩鋪里大多數(shù)時(shí)候的飯食,想來(lái)便是那沒(méi)有油的面糊糊,或者是疙瘩飯。好在面前這江里可以打魚(yú),小貴爹在江邊多年,是打魚(yú)的好手,許多時(shí)候打了魚(yú),就會(huì)帶回在村莊的家里來(lái)。
在小貴爹的沙壩往上,隔一條被雨季的山洪水沖出來(lái)的小干河,還連著一片更小一些的沙壩,大約十多畝,是我一位大爹家種的,同樣一年種兩季,同樣地在上面種玉米和紅花。大爹的窩鋪也在地頭,大爹的窩鋪里除了床、火塘、炊具以外,還有一桿獵槍。大爹除了會(huì)打魚(yú),還會(huì)打獵。我那時(shí)候已經(jīng)能感覺(jué)到,我大爹的窩鋪以及我大爹整個(gè)人的穿著、格調(diào)都比小貴爹要明亮許多,那種感覺(jué)現(xiàn)在回想起來(lái),小貴爹是一個(gè)沉默和勞苦的勞動(dòng)者,而我大爹守這沙壩地像是在度假。
江岸上那棵高上云天的紅椿樹(shù)就在小干河的河頭,一棵樹(shù)連著一段干河溝,把兩片沙壩地分開(kāi),形成一種自然的地界。雨季下大雨的時(shí)候,上面山箐里下來(lái)的洪水涌滿在平日干涸的小河道里,待到了紅椿樹(shù)下時(shí),像掃把那樣忽然散開(kāi),之后,很快匯入了江里。
紅椿樹(shù)還是一個(gè)水位標(biāo)高。“江水都漲到紅椿樹(shù)腳了。”等江水漲到紅椿樹(shù)腳,茫茫洪水早已淹沒(méi)了大半沙壩地,江面寬闊無(wú)際,江聲轟轟隆隆,整個(gè)世界只剩下了一片江聲。那無(wú)際的洪水,仿佛神話里的創(chuàng)世之初,天地一片混沌茫茫。
等洪水終于退去,被洪水漫過(guò)的原本深綠的玉米地被重新還原成一片沙壩,那些原本快要收獲的玉米,只在沙壩邊緣靠山腳的地方留下窄窄的一溜,仿佛打仗打剩下的稀稀拉拉的可憐隊(duì)伍。一季的收獲所剩寥寥。洪水走過(guò)的江岸上散落著被洪水帶來(lái)的舊輪胎、舊膠鞋、破臉盆、碎玻璃瓶子,甚至折了腿的舊床架。岸邊的柳樹(shù)根上以及蘆葦根上纏繞著沖下來(lái)的絲狀縷狀的雜物。那棵高高的紅椿樹(shù),裸露出的嶙峋的根更深更緊地抓住腳下的土地。
即便如此,等到雨季過(guò)去,季節(jié)到了秋末,這沙壩地仍然要被重新犁起來(lái),一一撿去石頭和雜物,一如既往地種下紅花。仿佛是上天對(duì)人們受傷后的一種安撫,經(jīng)歷過(guò)洪水的劫難,來(lái)年春天的沙壩地上,紅花總是長(zhǎng)得特別好,花朵開(kāi)得特別多,就像是誰(shuí)把滿天的星星都撒到了這沙壩地里。
村莊的另一片沙壩地要往下一些,也是十多畝,與小貴家的沙壩地隔著大約五里。這片沙壩地是我親爹守著的。我們那地方,把家里兄妹的岳父母或公婆稱作“親爹”“親媽”,這種稱呼一般也延伸到堂兄妹、表兄妹的配偶的父母。
我親爹是我嫂子的爹。記事以來(lái),我親爹就已經(jīng)一個(gè)人長(zhǎng)住在江邊了。我親爹的窩鋪不在沙壩地頭,而是在隔著山腳公路上面的半山腳上。我親爹的窩鋪與小貴爹以及我大爹的窩鋪意義不同。小貴爹和我大爹的窩鋪是用來(lái)看地,雖然常住,但意義上是臨時(shí)的。我親爹的窩鋪是他的“家”,意義上是長(zhǎng)久的。印象里,那窩鋪搭得比較高,門(mén)口站個(gè)人,頭上還空著一大截,里面的空間也要大得多。站在親爹窩鋪的門(mén)口,面前的一彎江水一覽無(wú)遺。
我親爹種沙壩也與小貴爹和我大爹不同,我親爹種沙壩只供他自己一個(gè)人生活。那沙壩每年下種時(shí),總是我哥哥嫂子去給他犁、種,收的時(shí)候也是我哥哥嫂子去幫著收。我親爹就仿佛是一個(gè)逸士,每天在窩鋪門(mén)口織織魚(yú)網(wǎng),隔三差五觀察著水情下幾網(wǎng),魚(yú)打得多的時(shí)候到不遠(yuǎn)的集市上賣(mài)給飯店。他最苦的活也就是有時(shí)候砍兩背柴到集市上換一斤酒。
——那些年,沙壩就是沙壩,一年兩季種下玉米和紅花,該鋤的時(shí)候辛苦地鋤,該收的時(shí)候辛苦并且高興地收。沙壩的意義就是種植和收獲。小貴爹、我大爹以及我親爹那時(shí)候都沒(méi)想到過(guò),這沙壩地有一天會(huì)變出另外一種意想不到的收成。
記得先是小貴爹走了,大約也就是六十左右吧,兒多父母苦,沒(méi)過(guò)過(guò)什么好日子。后來(lái),我親爹也走了。我親爹搬回到了村莊,本來(lái)分給他的二哥不愿意養(yǎng)他,他早幾年都在江邊,沒(méi)為兒子一家做過(guò)什么,孫兒孫女們對(duì)爺爺也沒(méi)什么感情。親爹回到村里后的大約十年時(shí)光,他的生活全都在我們家頭上,米、面、油、鹽,甚至柴,都很自然地從我們家里拿。我大爹高壽,如今八十多了,我過(guò)年時(shí)回家見(jiàn)著他,精氣神還在。
大爹家早年種的那片沙壩地,種了幾年后好像是棄種了。沙壩地離村莊較遠(yuǎn),需要常年看守不說(shuō),還因?yàn)橛昙緷q水的威脅而常常沒(méi)有保障。我親爹種的那片,等親爹搬回村里后大體也沒(méi)有再種。江邊只有小貴家那片沙壩還一直種著,這當(dāng)中的緣由,或許是小貴家真的需要那片沙壩地,又或者,小貴爹只是為了躲小貴媽的清靜,就愿意守著那片沙壩地也未可知。小貴家六個(gè)姊妹,兩個(gè)姐姐出嫁,家里后來(lái)把那片沙壩地分給了四個(gè)兒子。
是因?yàn)橄掠螢憸娼闲畴娬镜慕ㄔO(shè),這些江邊的沙壩地,變成了電站水庫(kù)的淹沒(méi)區(qū)。小貴家的沙壩地,忽然換來(lái)了大筆的移民賠償。大爹家的沙壩地在電站設(shè)計(jì)方來(lái)實(shí)地測(cè)量的時(shí)候因?yàn)橐呀?jīng)棄種,好像沒(méi)有被確認(rèn),大爹家后來(lái)列入移民搬遷是因?yàn)樗麄兗页邪犹铩N矣H爹的沙壩地當(dāng)時(shí)也沒(méi)有具體確認(rèn),親爹是分給二哥的,二哥那時(shí)不愿贍養(yǎng)父親,也不知道那沙壩能值幾個(gè)錢(qián),對(duì)那沙壩地也便沒(méi)有認(rèn)真爭(zhēng)取所有權(quán)。2000年左右,省水利設(shè)計(jì)院初來(lái)實(shí)地測(cè)量那會(huì)兒,說(shuō)是要在下游建設(shè)的所謂電站,對(duì)于村莊的人們還遙遠(yuǎn)得像個(gè)傳說(shuō)。我嫂子這邊雖然一直負(fù)擔(dān)著我親爹,但她是嫁出來(lái)的女兒,不適合去認(rèn)父親的地,怕哥哥們有意見(jiàn)。那片沙壩地在我親爹之后被村子里另一戶人家種了一小片,那戶人家的那片沙壩也列入了移民搬遷補(bǔ)償。
真是世事難料。小貴他們兄弟四個(gè),個(gè)個(gè)得了移民賠償,蓋了洋房。小貴他大嫂對(duì)人說(shuō):“你看我們這,就跟天上掉下來(lái)似的哈。”小貴他二嫂對(duì)他二哥兇時(shí),小貴他二哥對(duì)媳婦說(shuō):“你以為你能啊,蓋個(gè)洋房,這全靠的是我老爹!”
一條江,就這樣改變了村莊里許多人的命運(yùn)。它以一種不被預(yù)料的方式,將村莊從中間一分,把村莊的人們分成了兩個(gè)部分:有洋房的人家和沒(méi)有洋房的人家。
3
我們達(dá)村一位現(xiàn)今五十出頭的大哥還一直記得江上的朝陽(yáng)橋竣工的日子:1972年2月19日。“那一天,幾乎兩岸的人們都來(lái)看大橋竣工典禮,我們漾濞的,對(duì)面巍山的,人山人海。晚上還放了電影,那時(shí)候,大多數(shù)人都還不知道電影是怎么回事。——那年我還小,記得在上二年級(jí)。”
1972年,那時(shí)還沒(méi)有我。我出生是在大橋建成四年之后。待我稍有記憶時(shí),這橋建成已快十年了。我后來(lái),曾看到我母親有一張照片,正是1972年在江邊照的,和我三姑一起。那年母親只有28歲。照片上,高個(gè)子的三姑穿著看上去簇新整齊的彝族傳統(tǒng)服裝,笑臉燦然,母親穿一件的確良襯衣,手拿語(yǔ)錄本,頭戴黃軍帽,臉上也微笑著。記得那張照片下腳的時(shí)間里還寫(xiě)了月份,我這時(shí)已不記得了,但能猜想大約應(yīng)該就是大橋竣工后的某一個(gè)時(shí)間。
關(guān)于大橋所在位置的行政區(qū)屬,北邊是漾濞縣雞街鄉(xiāng)(大橋建成時(shí)間應(yīng)該是公社,南邊也如此)達(dá)村密喜把社。“密喜把”是我的村莊的名字。南邊是巍山縣馬鞍山鄉(xiāng)河南村阿系古社。橋北邊往上兩三百米就是小貴家沙壩地。
這是一座高大的鋼架結(jié)構(gòu)式吊橋,那時(shí)候在我的眼里,這橋足可以用課文上寫(xiě)南京長(zhǎng)江大橋的那個(gè)成語(yǔ)來(lái)形容:雄偉壯觀。大橋的兩端各豎一對(duì)高大的水泥橋墩,看上去就像一個(gè)大寫(xiě)的“H”,只是每組橋墩間各有上下兩根橫梁,比“H”多出了一橫。橫梁面寬約一米。每邊橋墩的上橫梁正面均書(shū)“朝陽(yáng)橋”——我一直也沒(méi)弄清楚過(guò),起這橋名的人起意的時(shí)候是把這“朝”字讀cháo還是讀zhāo,我們這里的人則把它讀為cháo,而更多的時(shí)候,人們直接就把這橋叫“橋”或者“大橋”“江橋”。上橫梁的背面及下橫梁的兩面寫(xiě)著像天安門(mén)上那樣的紅漆大標(biāo)語(yǔ)。用以支撐起大橋主體的兩股大鋼繩在壓過(guò)橋墩頂部后分開(kāi)成多股,之后斜下,以牢固的鋼混水泥固定到近20米外的山體中。從鋼繩所固定位置以下山壁,用水泥平整成墻面,頂端飛出窄窄的平檐。墻上用石灰刷白后,用豎體寫(xiě)著毛澤東詩(shī)詞。大橋橋面的構(gòu)造先是在鋼架橫梁上橫向鋪一層厚木板,再在橫板上縱向鋪兩道約一米寬的厚木板為行車(chē)道。拉著滿車(chē)木料的大解放和大東風(fēng)走在橋上的時(shí)候,整座橋就在一片“嘎吱”聲中搖晃不停。
橋過(guò)去是街。人們把這街叫作“江橋街”,把這地方叫作“江橋”。我小時(shí)候?qū)τ谶@橋的美好向往以及記憶,更多地想必是源于對(duì)橋那端七天一街的集市的美好向往和記憶。那時(shí)候,我還遠(yuǎn)遠(yuǎn)不能想到,這大橋有一天會(huì)在這江面上消失。
是2006年左右,小灣電站早已經(jīng)在下游的瀾滄江上開(kāi)工建設(shè)。朝陽(yáng)橋因?yàn)樵趲?kù)區(qū)水位以下而將要被拆除的事實(shí)已不可更改,屆時(shí),連同橋那邊的江橋街也要沒(méi)入庫(kù)區(qū)。而兩岸的人們不能沒(méi)有橋來(lái)通行。按照設(shè)計(jì),到時(shí)候這里將建起一座新的大橋。恰好,這個(gè)時(shí)候,大理州政協(xié)來(lái)征集文史資料,我于是想到了這座老橋。我以一種難以言說(shuō)的復(fù)雜心情,為朝陽(yáng)橋?qū)懴铝艘黄^為詳細(xì)的記錄文字。在這篇文字里,我把關(guān)于這座橋的一些數(shù)據(jù)資料作了收集和整理:朝陽(yáng)橋動(dòng)工于1970年,當(dāng)時(shí)規(guī)模宏大的森工企業(yè)漾江林業(yè)局為開(kāi)發(fā)林區(qū)的需要,由局工程師自行設(shè)計(jì)建造,工程在當(dāng)時(shí)耗資75萬(wàn)元,歷時(shí)兩年多建成。橋身全長(zhǎng)126米,寬5.7米,橋墩高18米,橋體共有43根橫梁,每一根鋼架橫梁高32厘米,寬27厘米。
那時(shí)候,我四表兄還在橋這邊開(kāi)鋪?zhàn)幼錾猓@些數(shù)據(jù),有許多是他因?yàn)槲业恼?qǐng)求親自量、親自數(shù)了告訴我的。
也是因?yàn)閷?xiě)這篇資料的需要,我第一次認(rèn)真地弄清了橋頭兩端山壁上所書(shū)的毛澤東詩(shī)詞。北面書(shū)的是《長(zhǎng)征》:“紅軍不怕遠(yuǎn)征難,萬(wàn)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xì)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guò)后盡開(kāi)顏。”南面墻上書(shū)的是《為李進(jìn)同志題廬山仙人洞照》:“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gè)仙人洞,無(wú)限風(fēng)光在險(xiǎn)峰。”兩首詩(shī)詞皆以毛澤東字體書(shū)寫(xiě)。小時(shí)候識(shí)得的字不多,也不知道這兩首詩(shī)詞,一年一年走在橋上,對(duì)山壁上那龍飛鳳舞的字竟從來(lái)沒(méi)有認(rèn)真讀懂過(guò)。
這橋是有人守著的。那個(gè)守橋的年輕人,我一直還記得他。
那間磚瓦結(jié)構(gòu)的守橋房在橋的南頭。我對(duì)這房子的印象是美的:青磚砌的墻,綠色的“目”字門(mén),綠色的木窗框,屋頂是四面檐,也就是除了一般的前后“人”字檐外,左右兩側(cè)還各有一個(gè)比前后檐更窄一些的 “人”字檐。我就覺(jué)得,這房子的青磚墻,比村莊里的那些土墻美。這房子的四面檐的屋頂,比村莊里那些只有前后兩面檐的屋頂美。最美的是這房子的門(mén)和窗。村莊里的房屋都沒(méi)有玻璃窗,何況這玻璃窗的窗框還漆著好看的綠色,村莊里的房子,只有一些老屋子上有那種厚重的木推拉窗。還有那綠色的門(mén),中間兩道杠,像一個(gè)“目”字。村莊里的房屋,門(mén)大多都是平板,并且也少有漆色的,尤其是綠色。
那個(gè)守橋的年輕人名叫王永吉,長(zhǎng)相清秀,皮膚白凈,上身常穿一件綠軍裝,夏天時(shí)則常穿白襯衣。村莊里的人們把從外面來(lái)的說(shuō)漢話的人統(tǒng)稱為“拉本”,就是“漢人”的意思,并把說(shuō)漢話稱為說(shuō)拉本。我那時(shí)的印象里,王永吉就是優(yōu)雅的“拉本”,直到我后來(lái)得知,王永吉是南澗縣人,也會(huì)說(shuō)土話,只是他們的土話和我們不同,我也仍然固執(zhí)地把王永吉看成“拉本”。印象中,王永吉性情和善,守橋多年,與村莊的人們大都熟悉了,村莊里的人們?nèi)ペs江橋街,王永吉常和大家打招呼,請(qǐng)大家到屋里喝水。又因王永吉性情好,大姐姐們還愛(ài)跟他開(kāi)玩笑。王永吉后來(lái)娶的媳婦是阿系古村的一位漂亮姑娘,他也由此,真正在這地方扎下了根。
20世紀(jì)80年代末90年代初,漾江林業(yè)局的采伐逐漸結(jié)束,原設(shè)的林場(chǎng)逐漸撤離,大橋也由此不再被漾江林業(yè)局固定維護(hù)。這以后,不知道王永吉被單位另外安排了什么工作。失去維護(hù)的朝陽(yáng)橋,殘破的橋板得不到更換,大橋快速損壞,至1992年,大橋的橋板已徹底損毀,無(wú)法通行。至此,因橋建成而消失多年的竹排又重新出現(xiàn)在橋下的江面上。趕街的人們渡竹排過(guò)江,一人來(lái)回一塊,一只牲口來(lái)回兩塊。
大橋后來(lái)曾多次不同程度修復(fù)。其間,曾有私人出資修橋,在橋上鋪上簡(jiǎn)易邊皮板供人通行,收取過(guò)往人畜的過(guò)橋費(fèi)。簡(jiǎn)易邊皮板鋪的橋面縫隙較大,且木板又沒(méi)有被固定,有很大的安全隱患。1995年,雞街鄉(xiāng)與馬鞍山鄉(xiāng)兩鄉(xiāng)共同協(xié)商出資,為大橋鋼繩全部上了一次黃油。1998年,兩鄉(xiāng)再次協(xié)商出資修復(fù)大橋,這次修復(fù)共耗資12萬(wàn)元,新修復(fù)的大橋除了供人畜通行,還可通過(guò)小型車(chē)輛,大橋的通行由此又持續(xù)了數(shù)年。
2007年8月,新朝陽(yáng)橋動(dòng)工。新橋在原橋往下約10米處,是一座水泥橋,由國(guó)家林業(yè)局西南林堪設(shè)計(jì)院設(shè)計(jì),設(shè)計(jì)建造資金為1270萬(wàn)元。根據(jù)大理州移民開(kāi)發(fā)局的統(tǒng)籌安排,新橋建造資金劃拔巍山縣,由巍山縣主持建造。在新橋的開(kāi)工典禮上,巍山縣移民開(kāi)發(fā)局發(fā)了一個(gè)紀(jì)念水杯,上書(shū)“巍山縣朝陽(yáng)橋開(kāi)工典禮”。自建縣以來(lái),漾濞、巍山兩縣以漾濞江為自然分界,原朝陽(yáng)橋由漾江林業(yè)局建造,兩縣對(duì)這橋一直不存在權(quán)屬問(wèn)題。之前修復(fù)大橋,也是所在兩鄉(xiāng)共同出資。而在那紀(jì)念杯上,這橋變成了“巍山縣朝陽(yáng)橋”。
新大橋在庫(kù)區(qū)水位上來(lái)之前如期完工,朝陽(yáng)吊橋被拆除。大約是在朝陽(yáng)吊橋被正式拆除前兩三年,我聽(tīng)到一個(gè)消息說(shuō),王永吉去世了。
大約是2009年中,我曾有一次繞經(jīng)大倉(cāng)回老家,車(chē)子從新橋上走過(guò)。老朝陽(yáng)吊橋已經(jīng)不在。橋南那間守橋的房子自然也已經(jīng)不在了。
4
自然,在修造朝陽(yáng)橋之前,漾江林業(yè)局先是把公路修到了江邊。漾江林業(yè)局局機(jī)關(guān)所在位置屬于巍山縣馬鞍山鄉(xiāng),離巍山大倉(cāng)鎮(zhèn)約十公里,到江橋約三十五公里。
過(guò)了橋,公路一直沿江向下約七八公里,在這里,雞街鄉(xiāng)境內(nèi)的主河流雞街河匯入漾濞江,故被稱為河門(mén)口。河門(mén)口沙岸寬闊,河上沒(méi)有橋,公路過(guò)了河,從左側(cè)一路倚山溯河而上,又七八公里,到現(xiàn)今的雞街鄉(xiāng)政府所在地。當(dāng)時(shí)的老區(qū)公所則在老雞街社,從現(xiàn)鄉(xiāng)政府再往里一公里半。過(guò)了老雞街,公路繼續(xù)向西向里,穿過(guò)緊鄰雞街的永平縣龍街鄉(xiāng)青和早村、田心村。在這段公路下面,同樣有一條河一路相隨,這河為雞街河的主支流,在老雞街社下面磨坊口匯入從西北而來(lái)的雞街河。這河在途經(jīng)各段的名稱不一,在匯入雞街河之前最后流經(jīng)的是雞街村的畢么社,所以在這一段被稱為“畢么河”。我未曾具體考證,但我猜想,這公路在那時(shí)就已一路經(jīng)過(guò)龍街通向了永平。
在公路從江橋出發(fā)、離雞街河門(mén)口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個(gè)臨江的小村子,名叫吐路么,屬于我們同鄉(xiāng)的菜白村。一條從我們達(dá)村高山下來(lái)的清澈小河穿過(guò)小小的村莊,在腳下流入漾濞江,河被叫作吐路么河。在這里,公路向上分出一條,在穿過(guò)村莊的路段,公路在小河西岸,過(guò)了村莊,公路過(guò)河,并溯河倚著山腳一路向上、向西北,綿延伸向大山腹地。
所有這些伸向大山的公路,后來(lái)被人們一律稱為林區(qū)公路——這些公路測(cè)量水平專業(yè),修挖質(zhì)量高,絕大多數(shù)路段在數(shù)十年后仍然完好無(wú)恙,成為鄉(xiāng)村公路的主干道。朝陽(yáng)橋的建造以及這些蜿蜒于大山的公路,充分證明了一個(gè)事實(shí):那時(shí)的漾江林業(yè)局,是一個(gè)人才濟(jì)濟(jì)的地方。
沿著公路主干道,漾江林業(yè)局一路設(shè)置了養(yǎng)護(hù)道班。江橋街所在之處為六道班。可以想見(jiàn),當(dāng)時(shí)江橋街集市的興起,正是因?yàn)榱腊嘣谶@里的設(shè)置以及江橋的修造,在這之前,這地方并沒(méi)有集市。我曾聽(tīng)母親講過(guò)早時(shí)候村人們趕集,要過(guò)江到馬鞍山鄉(xiāng)青云村的蛇街。蛇街離江橋還有十多公里路,從江邊一路上坡。因那時(shí)候集市少,四面來(lái)趕集的人們大多路遠(yuǎn),所以蛇街是一個(gè)晚集,當(dāng)?shù)氐娜藗兇蠖喑粤嗽缤盹埐怕齺?lái)趕集,而四面去趕集的人們,傍晚離開(kāi)集市,一大夜才能回到家。
七道班設(shè)在吐路么社,道班房就蓋在公路下側(cè)臨河的地方。為此,吐路么社后來(lái)又常被人們叫作“七道班”。從七道班溯吐路么河一路往上約十公里,河?xùn)|岸有一個(gè)和七道班一般大小、只有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莊,名叫上吐路么,屬于我們達(dá)村。公路從上吐路村莊腳下緩緩向西北繞過(guò)村莊,一路繞到村莊身后,繼而一路向上,延伸向高山腹地。在這些蜿蜒曲折爬在大山的公路上,一路分布著漾江林業(yè)局的采伐林場(chǎng)。當(dāng)中的一林場(chǎng)在上吐路么的村后,是個(gè)風(fēng)埡口,林場(chǎng)舊址的下面就是村莊最高處的人家。在我有記憶的時(shí)候,一林場(chǎng)已沒(méi)有痕跡,只留下一個(gè)地名。二林場(chǎng)在上吐路么腳下,依山臨河,與村莊隔河相對(duì)。
在很多年里,二林場(chǎng)對(duì)于遠(yuǎn)近村莊的人們來(lái)說(shuō)一直是一個(gè)美好的地方。林場(chǎng)的房子大多都是四面檐的漂亮的兩層磚瓦樓房,屋頂上有著刷著綠色漆的實(shí)木天花板,那些磚墻以及天花板都是村莊的房屋所沒(méi)有的。林場(chǎng)里有水泥鋪的籃球場(chǎng),水泥鋪的走道,有種著漂亮花草的花臺(tái),有子弟學(xué)校,有商店,里面賣(mài)著各種漂亮和好吃的東西。最最吸引人們的是林場(chǎng)里一段時(shí)間就會(huì)放一場(chǎng)電影。林場(chǎng)有電影的時(shí)候,鄰近村莊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們總要跑去看電影,半大的少年在看完電影返回的途中,跑斷了腳上唯一的涼鞋。
那時(shí)候,林場(chǎng)人是山區(qū)的人們艷羨的對(duì)象,林場(chǎng)的孩子們穿著和電影里面的孩子一樣漂亮的衣服。林場(chǎng)子弟學(xué)校的老師會(huì)教許多東西,學(xué)校里還有年輕漂亮的女老師,而村里的小學(xué)從來(lái)沒(méi)有女老師。上吐路么因?yàn)樵诹謭?chǎng)旁邊,或許是為了協(xié)調(diào)和地方的關(guān)系,林場(chǎng)允許上吐路么的孩子在子弟學(xué)校上學(xué),這個(gè)待遇,成為附近村莊的孩子們不可企及的美好向往。
林場(chǎng)的生活,對(duì)于山上的人們來(lái)說(shuō),是不可企及的另一種世界。上吐路么原本是大山深處一個(gè)偏僻的小村莊,但是因?yàn)槎謭?chǎng)的到來(lái),偏僻的小村莊轉(zhuǎn)身變成了那時(shí)時(shí)尚的前沿。這里的姑娘原本大多長(zhǎng)得漂亮,如今在二林場(chǎng)旁邊耳濡目染,很快學(xué)會(huì)了各種新潮的打扮,在趕集和做客的場(chǎng)合,常常成為人們目光追蹤的焦點(diǎn)。
那些年,綠色的解放牌大卡車(chē)每天在盤(pán)山公路上來(lái)來(lái)往往,進(jìn)山的時(shí)候,車(chē)上帶著林場(chǎng)的人們需要的東西,有時(shí)帶來(lái)局里的電影隊(duì)。出山的時(shí)候,粗大的木料高高裝滿車(chē)廂,上面用鋼繩牢牢剎住。那時(shí)候,村莊的人們常常搭拉料車(chē)進(jìn)城——所謂進(jìn)城,也就是去大倉(cāng),偶爾也有去到巍山縣城或下關(guān)的,但極少。摘橄欖的季節(jié),姑娘們摘幾袋橄欖,在路邊搭了車(chē),人和橄欖袋子一起坐在高高的木料車(chē)上,一路唱著山歌,顛簸搖晃著向大倉(cāng)而去,我五六歲的時(shí)候第一次去大倉(cāng),就是表姐去賣(mài)橄欖帶我去的。而更多時(shí)候,即便不賣(mài)什么東西,姑娘們想進(jìn)城看看了,揣上一塊錢(qián)就在路邊搭車(chē),木料車(chē)不要人車(chē)錢(qián),去到大倉(cāng),住旅館兩毛五一晚,一碗餌絲兩毛五,晚飯吃一碗,第二天早上吃一碗,逛一轉(zhuǎn)大倉(cāng)的街市,再搭上進(jìn)山拉料的空車(chē)回來(lái)。
——當(dāng)然,所有這些,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都是極為模糊的記憶,當(dāng)中絕大多數(shù)是我后來(lái)聽(tīng)大人們說(shuō)的。到我第一次真正到二林場(chǎng)時(shí),二林場(chǎng)已然繁華不再,只留下兩三個(gè)最后守場(chǎng)的人。我去二林場(chǎng)是和母親去賣(mài)麻栗殼。我那時(shí)候不到十歲,每天和母親天不亮出門(mén)上山撿麻栗殼,然后到二林場(chǎng)去賣(mài)。收麻栗殼的人借了二林場(chǎng)的房子在那里收。麻栗殼五分錢(qián)一斤,緊緊的一麻袋麻栗殼有八九十斤,能賣(mài)四塊多錢(qián)。我主要是幫忙母親撿,背的時(shí)候只能背動(dòng)一小籃子。
那時(shí)候,二林場(chǎng)的整個(gè)樣子都還在,只是已經(jīng)沒(méi)有了昔日的繁華和熱鬧氣息。傍晚來(lái)這里交麻栗殼的人們匆匆兌換了一天辛苦的汗水,然后在暮色中趕回家去。那對(duì)收麻栗殼的年輕夫妻,丈夫是我們達(dá)村的,妻子是另一個(gè)村的。——那個(gè)年輕的妻子,她長(zhǎng)得真好看,穿著的確良襯衣,那么白那么清秀,就像我想象中以前二林場(chǎng)的女教師。
曾經(jīng)的三林場(chǎng)要從上吐路么背后的一林所在地再往里走十來(lái)公里。我第一次到三林場(chǎng)是跟著村里的哥哥姐姐們?nèi)ネ诓菟幏里L(fēng),那時(shí)候,三林場(chǎng)已只剩下幾方斷壁殘?jiān)5故窃S多年后,偶然聽(tīng)得一段關(guān)于三林場(chǎng)的往事:那時(shí)候,林場(chǎng)的人們自己種菜,園子里種的洋花菜,附近村莊放牛的孩子好奇,于是乘工人們不見(jiàn)去偷這種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的菜,路上因?yàn)橄又兀焉厦娴牟嘶ㄈ缄簦瑤Щ匾槐~子的洋花菜桿。
從三林場(chǎng)再往里更遠(yuǎn),有個(gè)八林班。聽(tīng)名字,是一個(gè)采伐小組的臨時(shí)采伐地。八林班再往上就是風(fēng)吹埡口,山在這里走到了最高處,山頂上大風(fēng)盡日,呼呼刮盡緲遠(yuǎn)的時(shí)光。
駐得最長(zhǎng)的是二林場(chǎng)。在后來(lái)陸續(xù)撤離上吐路么后,二林場(chǎng)曾轉(zhuǎn)在雞街河門(mén)口西岸山坡上待了幾年,改叫二工區(qū),可以想見(jiàn),都是為了整個(gè)局里的采伐工作需要服務(wù)。二工區(qū)在河門(mén)口大約有五六年,同樣地,商店、學(xué)校等部門(mén)都還跟著。河門(mén)口所在地屬于吐路么社,這期間,林場(chǎng)允許吐路么社的孩子在子弟學(xué)校上學(xué)。五六年后,二工區(qū)整體撤離。隔數(shù)年,二工區(qū)所在位置恢復(fù)成了一片草坡,已看不出任何房屋的痕跡,只有在公路岔進(jìn)當(dāng)時(shí)工區(qū)的路口處修下的一個(gè)水井池子還留著。水井池子在一叢雜樹(shù)下,水仍如舊時(shí)出著,井池中淤滿了軟泥,池子外壁的水泥和石頭的縫隙里長(zhǎng)滿深綠的青苔。
關(guān)于四林場(chǎng),我有一次唯一的記憶。四林場(chǎng)在老雞街進(jìn)去不遠(yuǎn),位置所在應(yīng)該屬于雞街村的畢么社。那是我上小學(xué)二年級(jí)那年,“六一”節(jié)被評(píng)為“三好學(xué)生”,鄉(xiāng)里學(xué)校要表彰,老師就帶著我去了。我那時(shí)候七歲,去到那里,和我們達(dá)村的一位在那里上初中的親戚姐姐吃飯。那天晚上,聽(tīng)說(shuō)四場(chǎng)小學(xué)要開(kāi)“六一”晚會(huì),鄉(xiāng)里學(xué)校的老師、學(xué)生許多都去看,那位姐姐就帶我去了。晚會(huì)在林場(chǎng)子弟學(xué)校的操場(chǎng)上舉行,整個(gè)操場(chǎng)上燈火通明,看晚會(huì)的人們擠滿了操場(chǎng)的四面。那天的晚會(huì),令我記憶最深的是一曲舞蹈《娃哈哈》,看上去和我一樣大的一群女生穿著紅色的裙子,臉上畫(huà)著紅紅的妝,在老師的帶領(lǐng)下,邊唱邊跳,我看著她們,真的羨慕極了——在我們村莊的茅草屋教室的復(fù)式小學(xué)里,唯一的男老師從來(lái)沒(méi)有教過(guò)跳舞,我也從來(lái)沒(méi)有穿過(guò)裙子。這是我第一次看晚會(huì)。那些跳《娃哈哈》的同學(xué),不知道她們后來(lái)都走向了何方,而她們?cè)谖业挠洃浝铮肋h(yuǎn)定格成了那晚穿著裙子、畫(huà)著紅妝的樣子。那天晚上回來(lái)的時(shí)候是那位姐姐背我回來(lái)的,路上,我在她的背上睡著了。
縱觀那段歷史,在整個(gè)20世紀(jì)70年代至80年代,漾江林業(yè)局的林場(chǎng)駐到哪里,哪里就成為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文化的中心,乃至一種時(shí)尚潮流的前沿,這種效應(yīng),甚至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當(dāng)?shù)貐^(qū)、鄉(xiāng)機(jī)關(guān)的影響力和帶動(dòng)力。林場(chǎng)的“拉本”們帶來(lái)的那種城市文明的氣息,讓山區(qū)的人們深深向往,并且努力模仿。就連七道班那樣一個(gè)小小的道班,也會(huì)成為吐路么整個(gè)村莊乃至周?chē)恍∑胤降娜藗冊(cè)敢庀蛩械牡胤健.?dāng)時(shí)的漾江林業(yè)局機(jī)關(guān)所在地,被人們簡(jiǎn)稱為“漾林”,附近地方的人們生了病,最高的治療級(jí)別就是上漾林醫(yī)院。
直到20世紀(jì)80年代末,漾江林業(yè)局的采伐漸入尾聲。我曾向人問(wèn)過(guò),那些林場(chǎng)是于1989年完成最后撤離的。并且,最后撤離的應(yīng)該就是在河門(mén)口的二工區(qū),這二工區(qū)在當(dāng)時(shí)除了從二林場(chǎng)撤下來(lái)的工人,還應(yīng)該包括了從四林場(chǎng)撤出來(lái)的部分。
關(guān)于漾江林業(yè)局的采伐,關(guān)于他們?cè)谀莻€(gè)年代給大山帶來(lái)的文明以及數(shù)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難以修復(fù)的濫殤,當(dāng)中的功過(guò)是非,涉及時(shí)代以及社會(huì)的諸多方面因素,無(wú)以輕易定論。只有一個(gè)明確的事實(shí)是:那個(gè)時(shí)代,在云南各地(我不清楚是不是全國(guó)各地)都有許多這樣的林場(chǎng),在漾濞境內(nèi)、漾濞縣城附近兩三公里的地方就有云臺(tái)山林業(yè)局,采伐地涉及漾濞、永平、云龍。同樣地,云臺(tái)山那時(shí)也是地方上的人們無(wú)限羨慕和向往的地方,據(jù)說(shuō)那時(shí)候云臺(tái)山林業(yè)局在漾濞一中上高中的學(xué)生,兩三公里的路,局里每周還專門(mén)派班車(chē)接送,羨慕得四面山區(qū)來(lái)的學(xué)生們眼睛都綠了。
我后來(lái)多年才知道,漾江林業(yè)局、云臺(tái)山林業(yè)局這些森工單位,單位建制為縣團(tuán)級(jí),有醫(yī)院、學(xué)校、電影隊(duì)等一應(yīng)機(jī)構(gòu)。單位雖在地方,但不受地方行政管制。那時(shí)局里的干部職工們來(lái)自全國(guó)各地,是在那個(gè)年代“響應(yīng)時(shí)代的號(hào)召和祖國(guó)的召喚”而來(lái)的。
20世紀(jì)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地的采伐陸續(xù)結(jié)束之后,林場(chǎng)逐漸面臨困境,陷入艱難支撐的局面。1999年到2000年左右,這些林場(chǎng)劃歸到地方,建制改為科級(jí),成為地方天保部門(mén)(前二十年砍樹(shù),后數(shù)十年育林,這算是一種歷史的回環(huán),卻也更像是一場(chǎng)歷史的懲罰或者說(shuō)啟示)。漾江林業(yè)局局機(jī)關(guān)搬到大倉(cāng)鎮(zhèn)鎮(zhèn)政府所在地。幾年后,馬鞍山鄉(xiāng)政府從原來(lái)臨漾濞江一面的田口村搬遷至漾江林業(yè)局舊址。
我最后一次去二林場(chǎng),是我在鄉(xiāng)上工作以后,去上吐路么下鄉(xiāng)。這時(shí)候,原本二林場(chǎng)的所在,房子已然破的破,拆的拆,有一小部分被上吐路么當(dāng)?shù)氐囊粦羧思屹I(mǎi)了下來(lái),經(jīng)過(guò)修繕,變成了民居。這戶人家有一只黑狗,進(jìn)去的時(shí)候?qū)χ覀円煌穹汀U麄€(gè)二林場(chǎng)場(chǎng)區(qū)一片清蕭。
同樣,位于吐路么社的七道班道班房也在多年前賣(mài)給了當(dāng)?shù)氐拇迕瘛?/p>
往事杳然,時(shí)光遠(yuǎn)遁。一段無(wú)以評(píng)說(shuō)的歷史,留下最后清寂的背影。
5
公路從漾林出來(lái),順著一條長(zhǎng)峽谷一路向外向西,約三十五公里,一直來(lái)到漾江邊。在到達(dá)朝陽(yáng)橋頭之前,公路在青云山伸到江邊的山腳上繞了一個(gè)馬丘彎。六道班的道班房就在馬丘彎的頂部,一排帶窗子的好看的平房,大約應(yīng)該有六間。房子后墻背街,面向江流,門(mén)外的空地邊上種一排桐油,一些房間的玻璃窗臺(tái)上常放著盆栽的花。
整個(gè)江橋集市就在道班房的兩側(cè)展開(kāi),許多用邊皮板搭建的簡(jiǎn)易商鋪分立在街的上下兩側(cè),把街道擠成窄窄的一溜。在這些邊皮板房里開(kāi)著飯店,賣(mài)著日用百貨,地方小吃卷粉和油粉,后來(lái)還開(kāi)著冰棒室,錄像室,以及臺(tái)球室。曾經(jīng)有幾年,還有過(guò)一間修表的小店。整個(gè)街面上,飯店和百貨鋪的店主絕大多數(shù)都是大倉(cāng)人,包括那間賣(mài)卷粉和油粉的小店也是,另有少數(shù)幾家是當(dāng)?shù)伛R鞍山鄉(xiāng)人。唯有那間修表的小店,是我們雞街鄉(xiāng)菜白村的一位小伙子開(kāi)的,小伙子個(gè)子瘦高,皮膚白凈,往這街上一站,還真像是大倉(cāng)“拉本”。
江橋街逢星期天趕集。每逢集日,街上的各種店鋪一律擠滿了買(mǎi)東西的人。除了那些固定的店鋪,又有許多走街的大倉(cāng)人來(lái)賣(mài)服裝、冰棒、雜貨。大貨車(chē)一早從大倉(cāng)出發(fā),等四面村寨的人們吃過(guò)早飯趕到集市上,走街的大倉(cāng)商販們?cè)缫训搅恕Yu(mài)服裝的固定地在道班房斜對(duì)面山腳下沒(méi)有店鋪的地方排開(kāi),兩個(gè)木馬上面支一塊床板,大人孩子的衣服、鞋子就在上面擺開(kāi)。在許多年里,那些攤子上面的服裝、鞋子,一直引領(lǐng)著江橋集市周邊各個(gè)村寨的著裝潮流。賣(mài)冰棒的背著冰棒箱子在街上來(lái)回走,里面的冰棒紅紅綠綠地,小的兩分錢(qián)一支,大的三分錢(qián)一支。雜貨郎挑著擔(dān)子,搖著手鼓,頭上戴個(gè)草帽,擔(dān)子里挑著各種雜貨,挑頭上掛著一大把剪成小段的各種顏色的毛線,五分錢(qián)一根。
四面村莊來(lái)賣(mài)農(nóng)副產(chǎn)品和山貨的籃子、挑子在店鋪和那些服裝攤子的兩頭一路延伸開(kāi)去。在集市的最外頭賣(mài)的是豬雞牛羊。一個(gè)集市熱鬧與否,只要看看這天集市的兩頭延伸到多長(zhǎng)便知道。
這個(gè)江邊的集市,曾經(jīng)帶給我許多幸福美好的記憶。
第一次在這集市上大倉(cāng)人開(kāi)的飯店里吃餌絲是哥哥帶我吃的,餌絲三角錢(qián)一碗,上面放有 肉,蔥花,挑上一點(diǎn)油辣子。在這集市上開(kāi)店的大倉(cāng)人,與周邊村寨里常來(lái)趕集的人們大多熟悉,老板娘一邊跟我哥哥打著招呼,一邊做事,態(tài)度熱情,動(dòng)作麻利。如今,數(shù)十年過(guò)去,我仍記得那時(shí)吃那碗餌絲的香美滋味。那一碗最初的餌絲,永遠(yuǎn)在我的記憶里留著餌絲白、蔥花綠的清新樣子,以及幸福滋味。
我最早的頭飾是在這集市上的貨郎挑子上買(mǎi)的兩根毛線,一根紅,一根綠,一根毛線五分錢(qián),兩根毛線一角錢(qián)。為了買(mǎi)這兩根毛線,那個(gè)集市,我省了一碗油粉錢(qián)。回到家里,用那兩根毛線扎上頭發(fā),我美了許久。我后來(lái)買(mǎi)過(guò)的小鋼夾、小別針等一些頭飾也都來(lái)自這個(gè)幸福的集市。
我的第一條滌綸褲,第一雙酒紅色帶一點(diǎn)跟的漂亮滌綸鞋,也一一都是在這集市上買(mǎi)的。山村人家大多艱辛,一個(gè)孩子,一年中能被大人帶著趕集市的次數(shù)不算多。每次難得地跟著大人來(lái)趕集,一路歡欣地下山,來(lái)到江邊,在心里,一點(diǎn)點(diǎn)靠近集市上的那些幸福和美好。
我第一次照相也是在這集市上。那時(shí)候有一個(gè)照相的年輕男子,不記得是馬鞍山的還是大倉(cāng)的,幾乎每個(gè)集市日都會(huì)來(lái)這街上,要照相的人們?cè)诮诌叺纳狡律匣蚴窃诮呥x個(gè)風(fēng)景請(qǐng)他拍了,下一個(gè)集市日,便可拿到照片。記得那時(shí)的照片是按尺寸大小收錢(qián)的,照片上也可以給你彩上色,就是人工彩色那種,彩了色的照片價(jià)格又更貴一些。我那年應(yīng)該是八歲,平日很少帶我趕集的母親那天特意給我梳洗打扮了一番,給我穿上了最好看的衣裳。我一路心情雀躍,到了集市上,才知道母親原來(lái)是要給我照相。我們?cè)跇蚰项^的山坡上選了一個(gè)地方,我站在那里,照相機(jī)的鏡頭對(duì)準(zhǔn)了我。不知怎么,我極不自然,對(duì)著那個(gè)照相機(jī)的鏡頭怎么也不會(huì)笑。那幅約三寸見(jiàn)方的黑白照片,如今還被母親保存在箱子里,照片上我的神情,就像小學(xué)課本上即將英勇就義的劉胡蘭。
我擁有的第一支鋼筆,是在這集市上的“基建隊(duì)”里買(mǎi)的。那是在我上五年級(jí)畢業(yè)班的時(shí)候。大約在這之前兩三年的時(shí)候,集市上道班房所在的坡頭下建起了一院好房子,房子的主體為“﹃”形直角,院子的一面靠著道班下面的坡,公路從街頭岔下去,通到“基建隊(duì)”門(mén)口。這個(gè)院子被稱為“基建隊(duì)”,里面其實(shí)是個(gè)大商店,賣(mài)著各種各樣的東西。這個(gè)“基建隊(duì)”建成后,它的房子是整個(gè)江橋集市上最好的房子,里面賣(mài)的東西是整個(gè)集市上最好、最高檔的百貨。自從有了這個(gè)“基建隊(duì)”,人們趕集買(mǎi)東西時(shí),“我這是基建隊(duì)里買(mǎi)的”成為了一種商品質(zhì)量以及檔次的象征。“基建隊(duì)”雖不在街面上,卻因?yàn)槔锩嫠u(mài)的商品,每個(gè)集市日都被買(mǎi)東西的人們擠得滿滿當(dāng)當(dāng)。直到如今,我仍記得我在基建隊(duì)買(mǎi)的那支“英雄”鋼筆的價(jià)格是一塊七角九,這是我的第一支鋼筆,是那時(shí)我所有買(mǎi)過(guò)的文具中最貴、最好的文具。那支鋼筆,我一直用到初中。那個(gè)“基建隊(duì)”,關(guān)于它的所屬問(wèn)題,我不曾具體問(wèn)過(guò),應(yīng)該是屬于漾江林業(yè)局吧,我猜想是因?yàn)檫@是林業(yè)局的基建隊(duì)建設(shè)并經(jīng)營(yíng)的商店,所以被叫作“基建隊(duì)”。
這江邊的集市雖是一條窄窄的街,在這集市上趕集的人們卻涵蓋了兩州四縣的眾多村寨和集鎮(zhèn)。我們漾濞的、巍山的不用說(shuō)了,還有鄰縣永平的,鄰州保山昌寧的。昌寧羊街人趕著牲口來(lái)這集市上賣(mài)茶葉,據(jù)說(shuō)要半夜從家里出發(fā),中午來(lái)到集市上,傍晚回去,再半夜到家。人們把昌寧人賣(mài)的散茶葉統(tǒng)稱為“羊街茶”,“羊街茶”因?yàn)閮r(jià)格適中,適宜村莊人們的大眾消費(fèi),買(mǎi)的人多,故而引得羊街人一次次不辭遠(yuǎn)路來(lái)趕這集市。永平龍街的回族人在這集市上開(kāi)了第一家回族飯店。不知道哪里來(lái)的外地牙醫(yī)在這集市上開(kāi)了第一家鑲金牙的店門(mén)。
20世紀(jì)90年代初的時(shí)候,有一戶大倉(cāng)人借了一間道班房,在集市上開(kāi)起了第一間冰棒坊,這集市上于是第一次有了雪糕和冰激凌。冰棒坊生意火爆,主人家被人們稱為“冰棒家”。“冰棒家”姓高,大哥特別能干,帶著弟弟妹妹們?cè)谶@里做生意。大哥做木材生意,妹妹們經(jīng)營(yíng)冰棒坊,幾個(gè)妹妹都長(zhǎng)得漂亮,被人稱作“冰棒西施”。一個(gè)弟弟沒(méi)有事做,大哥于是又在街對(duì)面的山坡腳上蓋了一間邊皮板房開(kāi)錄像室,讓弟弟管著。那些年,“冰棒家”的生意,占了江橋集市上的三分之一條街。
也是在這個(gè)時(shí)間,我們達(dá)村一位從鄰鄉(xiāng)醫(yī)院退休的叔叔在道班房斜對(duì)面的街坡上開(kāi)了第一間診所。四面村寨的人們于是大多就近來(lái)這里看病就醫(yī),三五間簡(jiǎn)易的病房里常常住滿了打針輸液的病人。
20世紀(jì)90年代初的數(shù)年間,是江橋集市最熱鬧“繁華”的時(shí)代。這時(shí)候,漾江林業(yè)局的采伐漸近尾聲,而從20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因外部市場(chǎng)上的木材交易而引發(fā)的亂砍濫伐卻進(jìn)入了最深最嚴(yán)重的階段。這一時(shí)期,木材交易替代江橋集市最初的生產(chǎn)生活用品交易而成為了江橋集市新的主體和主題。在這集市上,每天都有數(shù)不清的木材從四面八方的山寨里馱到或是用車(chē)?yán)竭@里來(lái)交易。因?yàn)槟静慕灰祝猩暇瓦B空天也是人來(lái)人往,極大地帶動(dòng)了集市上各種店鋪的生意。最火爆的時(shí)候,不足一千米長(zhǎng)的街市上,邊皮板錄像室開(kāi)到了三家,臺(tái)球室數(shù)家,飯店、百貨鋪天天生意紅火,各種店鋪的數(shù)量達(dá)到歷史最多。各種明的暗的生意每天在這集市上你來(lái)我往。這是江橋的“鼎盛時(shí)代”,這個(gè)時(shí)期的江橋集市,被人稱為“小香港”。
在這一時(shí)期,從江橋到大倉(cāng)的公路上,每天都有各種拉木料車(chē)和貨車(chē)來(lái)來(lái)往往。而直到這時(shí)候,從雞街鄉(xiāng)上到漾濞縣城還沒(méi)有固定車(chē)次來(lái)回,雞街境內(nèi)的人們?nèi)タh城或是去州府下關(guān)上學(xué)的、辦事的,都要從江橋搭貨車(chē)到大倉(cāng),然后轉(zhuǎn)客車(chē)前往,回來(lái)的時(shí)候也是如此。我在外面上學(xué)的那些年,每次都是這樣出發(fā)和回來(lái)的。
為了努力制止亂砍濫伐,從20世紀(jì)80年代后期起,雞街鄉(xiāng)政府在橋北端設(shè)了木材檢查站,由鄉(xiāng)林業(yè)站換崗駐人,對(duì)非法木材交易形成了一定威懾,卻無(wú)法完全避免貓和老鼠的游戲情景。因?yàn)閷?duì)面市場(chǎng)的誘惑,許多木材照樣偷偷過(guò)了江,過(guò)了江那就是另一塊地面,超出了檢查站的管轄范圍。
圍繞著當(dāng)時(shí)的木材檢查站,橋北端也建起了一片房子,好多戶人家,開(kāi)飯店的開(kāi)飯店,賣(mài)百貨的賣(mài)百貨,形成了一小片新的集市。
我關(guān)于這江橋集市的最后的美好記憶是:這江橋集市雖是一個(gè)魚(yú)龍混雜的市儈地方,但是這集市上的人們對(duì)于上學(xué)這件事、對(duì)于在外上學(xué)的人還是有著一種尊重。那時(shí)候,四面村莊里在外上學(xué)的人還少,我在省城昆明上中專,假期間每去集市上,常引來(lái)集市上的人們友善的注目,就連不太認(rèn)識(shí)的店鋪老板也會(huì)打招呼,問(wèn)我在昆明好不好玩,書(shū)讀得怎樣等等。
20世紀(jì)90年代末,隨著四面山上木材的徹底砍伐殆盡,木材交易終于漸漸沒(méi)落,江橋集市日漸冷清下來(lái),“冰棒家”早已遷回了大倉(cāng),聽(tīng)說(shuō)他們靠著在江橋集市上賺得的大桶金銀,在大倉(cāng)開(kāi)了更大的店鋪。親戚叔叔的診所因?yàn)槲∩椒矫娴母缮娑岬搅藰虮边@邊,叔叔也因年紀(jì)漸大回到村里老家,診所由叔叔衛(wèi)校畢業(yè)的女兒接了手。江橋集市上的各種店鋪日漸凋弊,許多大倉(cāng)人都把店鋪兌給了當(dāng)?shù)睾幽洗灏⑾倒派绲娜恕<猩显?jīng)日夜紅火的錄像室已銷(xiāo)聲匿跡。臨街上一兩張殘存的臺(tái)球桌前冷冷清清。
時(shí)光流變,時(shí)移事遷。多年后的江橋集市,和朝陽(yáng)橋一起成為小灣電站的規(guī)劃庫(kù)區(qū),原本集市上留下的不多的幾戶人家被列為移民,補(bǔ)償搬遷到集市上面一兩公里的山坡上。新改線的一段公路穿過(guò)移民點(diǎn),之后轉(zhuǎn)彎,斜向新橋橋頭。橋北端這邊我們達(dá)村的幾戶,全部補(bǔ)償遷回村莊,當(dāng)中唯一相雜的一戶馬鞍山鄉(xiāng)青云村的人家遷回了青云。
也就是2009年中那次我經(jīng)大倉(cāng)回老家,車(chē)子走過(guò)新朝陽(yáng)橋的時(shí)候,我努力地看向那片曾經(jīng)的集市。集市上私人家的邊皮板房多數(shù)已被拆走,剩下的幾間東倒西歪。馬丘彎頂部的那排道班房還沒(méi)有最后拆去,這集市上最初蓋起的房子,它在這里一直堅(jiān)守到了最后。曾經(jīng)的街面上,只見(jiàn)一片模糊的狼藉。
這昔日江邊的熱鬧集市,終于在流水的時(shí)光中最后散場(chǎng)了。
6
在從江橋到河門(mén)口約八公里的距離內(nèi),共有三條河流注入了漾濞江。
先是歪角河在基建隊(duì)院子的后面流入江里,也可以說(shuō),基建隊(duì)就建在一江一河與青云山腳圍成的三角地帶。“歪角河”是這河的漢名,讀方言音,“歪”在這里讀第三聲,“角”讀“guó”,“河”讀“huǒ”,整個(gè)名字讀起來(lái)成了“崴國(guó)火”。同樣,歪角河也是與公路一起從漾林出發(fā)的,河與路一路并行,一路出峽谷來(lái)到了這里。路來(lái)到這里,接到橋頭;河來(lái)到這里,流入了漾江。歪角河在當(dāng)?shù)氐囊驼Z(yǔ)名字叫“路處厄”,“路處”,有小河汊、小水流的意思,與江對(duì)應(yīng),“厄”就是水。
從歪角河流入漾江口往回溯約一公里半,在河的南岸有一間水磨坊,這間磨坊屬于阿系古社。阿系古村莊在高處,與我的村莊正正隔江相對(duì),位置比我的村莊還高些,當(dāng)我們上到村莊后面兩公里多的皇家莊房地時(shí),看過(guò)去感覺(jué)才與阿系古村莊相平齊。磨坊邊上有一戶單獨(dú)的人家,屬于阿系古社,就是這戶人家在這里守著水磨坊。這間水磨坊,是那時(shí)候離我的村莊最近的水磨坊,村莊的人們常常把糧食背到這里來(lái)研磨。
依稀記得曾有一次,我跟著母親來(lái)這磨坊拉磨。磨坊老叔叔是個(gè)個(gè)子很高的和善的六十多歲老頭,在我們等著面磨好的時(shí)間里,老叔叔掃了一撮磨盤(pán)轉(zhuǎn)動(dòng)中飛到磨槽外面的玉米面,在一個(gè)盆里和了,摶成粑粑,然后燒到火塘的一角灶灰里。灶火上架著銅罐,銅罐里燒著水,母親和老叔叔說(shuō)著話。過(guò)一陣,漸漸聞見(jiàn)那粑粑的香味,老叔叔把粑粑從灶灰里刨出來(lái),那粑粑的兩面已經(jīng)燒得焦黃,一股香氣撲鼻而來(lái)。老叔叔邊左右抖著那粑粑,邊掰下一塊來(lái)給我,我燙不住,也學(xué)那老叔叔把粑粑在手里左右來(lái)回抖,直到能拿住了,才迫不及待地掰下來(lái)吃。母親和老叔叔也吃著粑粑,繼續(xù)聊著話題,直到母親背去的玉米都磨好,母親背著面口袋,我跟在身邊,涉過(guò)歪角河,在暮色中回家來(lái)。
后來(lái)又有一次是和嫂子一起。那時(shí)候,我嫂子和我哥哥已訂了婚,但還沒(méi)有過(guò)門(mén)。村莊的姑娘,但凡訂了婚,就要常去夫家?guī)椭鲂┦拢◣兔ψ鲛r(nóng)活,辦事時(shí)幫著去家里做飯,以及打掃衛(wèi)生等等。那天嫂子要去磨房背面——有時(shí)候,磨坊里排隊(duì)的人多,糧食不能當(dāng)天磨出來(lái),人們就把口袋放下,說(shuō)好哪天能磨好,再來(lái)背面。磨坊主是誠(chéng)信的人,袋子里的糧食一點(diǎn)也不會(huì)少——說(shuō)剛好帶我去河里洗衣衫。我的村莊,守著一條在山下日夜流淌的江,卻一直以來(lái)是一個(gè)干旱的村莊,到了枯水時(shí)節(jié),村莊里唯一的老井供村莊的人們吃水都難,更沒(méi)有余地洗衣衫。那是初冬時(shí)節(jié),河岸的沙灘上,蘆葦開(kāi)始開(kāi)出了一支一支潔白的蘆花。嫂子讓我換了衣衫,自己也去蘆葦?shù)乩飺Q了,把換下來(lái)的衣衫在河里洗。河水清澈,淡綠的青苔在石下柔柔地飄,嫂子把洗好的衣衫晾在蘆葦叢上,衣衫在陽(yáng)光和風(fēng)中很快晾干了。河對(duì)面的水磨坊里傳來(lái)轟轟的轉(zhuǎn)磨聲,磨坊的茅草屋頂,看上去就像一朵大蘑菇。
印象中,大多數(shù)的時(shí)候,歪角河河水清澈。我后來(lái)在外求學(xué)的多年,曾一次又一次溯著這河出發(fā),蜿蜒的公路,公路下蜿蜒的河,搭乘的貨車(chē)一路起伏顛簸,一雙手努力撫著車(chē)箱板或是篷桿,心里默默告別身后遠(yuǎn)去的家人和熟悉的景物。而當(dāng)學(xué)期結(jié)束,我又一次順著這公路、這河回來(lái),河水一路流淌,窄窄的河岸上田疇寧?kù)o,牛羊安然。終于,遠(yuǎn)遠(yuǎn)地看見(jiàn)了那間灰蘑菇似的水磨坊,我于是又回到了我的鄉(xiāng)愁,回到了我的村莊。
與歪角河從漾林出來(lái),一路往西流入漾江相對(duì),發(fā)源于我們漾濞龍?zhí)多l(xiāng)境內(nèi)的雞街河從龍?zhí)陡粡S山下出來(lái),一路往東,流經(jīng)雞街鄉(xiāng)所轄四個(gè)村中的新寨、雞街、菜白三個(gè)村,在離吐路么往西約一公里半的地方流入漾濞江。雞街河自身又有畢么河、許么邑河等眾多支流,雞街鄉(xiāng)政府機(jī)關(guān)所在地即位于許么邑河流入雞街河的三角地帶,屬于雞街村雞街社,政府機(jī)關(guān)距河只有五百米遠(yuǎn)。雞街河總長(zhǎng)與歪角河大體相當(dāng),但歪角河流出的峽谷狹長(zhǎng),沿河的田疇相對(duì)較少,雞街河流經(jīng)的河谷寬闊,兩岸稻田眾多,雞街鄉(xiāng)所轄的每個(gè)村——當(dāng)然也包括了我們達(dá)村,都在河邊分有河田。
雞街鄉(xiāng)所處位于漾濞全境的最南端。雞街河流入漾濞江的河門(mén)口海拔1174米,是漾濞全境海拔最低的地方。雞街河谷氣候炎熱,最適宜水稻種植。每一年的水稻栽插,住在雞街鄉(xiāng)政府附近的雞街社村民黃應(yīng)福總是第一個(gè)在全縣首開(kāi)秧門(mén)。自然,雞街河谷的水稻也在全縣最早收獲,每年農(nóng)歷七月半,人們就能吃上新米。然而,由于河谷寬闊,更由于流域地區(qū)植被的大量破壞,雞街河常發(fā)洪災(zāi),沿河許多地方的稻田常常今年造,明年沖,甚至許多時(shí)候,眼看著一季稻谷就要收獲了,一場(chǎng)洪水下來(lái),一片即將收獲的稻田轉(zhuǎn)眼又被夷為一片沙岸。這條河流,它滋養(yǎng)著兩岸村莊人們的悠長(zhǎng)歲月,卻又常常無(wú)情地帶走人們一年辛勞的希冀與汗水。
雞街河流入漾濞江的河門(mén)口,沙岸寬闊如練兵場(chǎng)。有幾年,沙岸靠西面山腳的一片也曾被吐路么社的幾戶人家開(kāi)墾成稻田,后來(lái)終于又被洪水沖去。河門(mén)口從來(lái)沒(méi)有過(guò)橋,公路一直涉河而過(guò)。在公路涉河處往上約三百多米是一個(gè)大拐彎,河水在那里直抵山腳,之后,斜斜向外拐出來(lái)。從拐彎處往上那段,河兩岸的稻田屬于我們密喜把村——從這一點(diǎn)來(lái)說(shuō),這雞街河可以說(shuō)也流經(jīng)了我們達(dá)村。大約是包產(chǎn)到戶前的最后一年,母親曾帶著我來(lái)這田里栽秧,我們自帶著行李和鍋灶。稻田周?chē)纳侥_下,搭著一個(gè)一個(gè)的“人”字窩棚,因?yàn)榇迩f離得遠(yuǎn),為了省去來(lái)回的時(shí)間和勞累,大家都在這里做飯吃,晚上就住在各自的窩棚里,一直到一趟活干完了才回去。記憶里,那一壩即將栽插的蓄滿了水的稻田在陽(yáng)光下一彎一彎閃亮,田邊溝渠里的流水咕嚕咕嚕地響,我們?cè)谇呄匆孪床耍稛熢谝蛔C棚的面前裊裊升起,順著山坡,一點(diǎn)點(diǎn)飄向高處。田下的河水里青苔濃密,平緩的水灣里有一片一片擺著尾巴的小蝌蚪,還有一片一片未孵出小蝌蚪的黑黑的青蛙卵。大人們分工干活,在最后栽插之前,女人們一趟趟上山拿葉子(也就是采葉子)捂田,男人們用耙架把田再一次耙平,牛蹄下水花飛濺,牛歌隨著河水流淌。
這些河田在之后聯(lián)產(chǎn)承包時(shí)分到了戶,分給了村里的七八戶人家。我們家分得的是山田,于是那年之后,我們?cè)贈(zèng)]有去河田里勞作過(guò)。那年母親和村人們一起栽下的田也許是收獲了吧。而在許多年景里,這些河田仍然一年一年受著洪水的威脅,一年一年栽插下去,卻永遠(yuǎn)不知道秋天的時(shí)候能不能收獲。漸漸地,幾戶人家已經(jīng)棄種了,也有的人家把田無(wú)償?shù)亟杞o吐路么人來(lái)種,還有人家讓給對(duì)面江邊的巍山縣龍街鄉(xiāng)底固社的親戚來(lái)種。河水拐彎處靠山腳的地方有一間茅草屋,聽(tīng)說(shuō)那戶底固人家的老父親常住在這茅屋里守田。
河田對(duì)面,隔著公路的山坡上就是之前的二工區(qū)。我在鄉(xiāng)上工作的多年里,常來(lái)來(lái)回回在這公路上走過(guò),從公路上,看見(jiàn)對(duì)面河邊的田已越來(lái)越少,漸漸地只剩了薄薄的三五丘,春天的時(shí)候,三五丘田里開(kāi)著零星的紅花。拐彎處那間茅屋漸年衰朽,聽(tīng)說(shuō),那位之前在這里守田的底固老叔叔已經(jīng)去世了。
這些河田,后來(lái)也成為小灣電站的庫(kù)區(qū),不管稻田還在不在,一律按聯(lián)產(chǎn)承包時(shí)的戶籍和畝籍,各家各戶得了補(bǔ)償。
沿著雞街河,早前一路上也有好幾座水磨坊。河門(mén)口靠西面山腳的地方舊時(shí)也有一間,屬于吐路么社,由吐路么社的一位老叔叔守著。那時(shí)候人們拉磨,若是沒(méi)有現(xiàn)錢(qián),記得也能用糧食來(lái)交付,每百斤糧食交幾斤作為磨錢(qián)。這磨坊因?yàn)殡x我們村莊較遠(yuǎn),除非歪角河的磨坊在大修或是實(shí)在擠不開(kāi)的時(shí)候,村人們大多不會(huì)來(lái)這磨坊磨面。另外,人們選擇磨坊,也還要看一方石磨拉出來(lái)的面細(xì)不細(xì),損耗大不大,磨坊主友不友善等諸多因素。一間好的熱鬧的磨坊,總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再說(shuō)說(shuō)第三條河:吐路么河。吐路么河小,河從北面我們達(dá)村境內(nèi)的高山上下來(lái),河上段的村莊上吐路么屬于我們達(dá)村,下面的吐路么歸菜白村。吐路么社十多戶人家,分布在小河的兩側(cè)。與雞街河相比,這小河對(duì)兩岸的威脅要小得多,河岸的稻田里一年一年收獲著稻谷,曾經(jīng)在許多年里羨煞了我們達(dá)村看老天下雨種雷響田的山上人。
吐路么河流過(guò)村莊的那一段,河的兩岸種了許多芭蕉。岸上的蘆葦在冬天開(kāi)著潔白的花。岸上還有一株高大的攀枝花樹(shù),在蘆花開(kāi)盡之后,開(kāi)出一樹(shù)火紅的花朵。
吐路么河下了村,很快在蘆葦叢中流入了漾濞江。往下幾步,江在村莊下面打了一個(gè)手臂彎,遠(yuǎn)看去,清江如帶,沙岸如銀。
7
在一次省水利設(shè)計(jì)院來(lái)勘測(cè)小灣庫(kù)區(qū),我才第一次知道,漾濞江在正式的地圖上被稱為“黑潓江”。后來(lái),在我有意識(shí)逐漸接觸的許多文字資料上,這個(gè)問(wèn)題被一次次證明。如此,我也才想到,“漾濞江”,這原是我們對(duì)于這條江的充滿著歷史、地理以及文化情感的一個(gè)稱謂。
在配合省水利設(shè)計(jì)院的彭工程師對(duì)庫(kù)區(qū)進(jìn)行勘測(cè)的過(guò)程中,作為一個(gè)最核心的主題詞,彭工程師和他的助手把這條江叫作“黑潓江”,而我和我們鄉(xiāng)土地所的兩位工作人員固執(zhí)地把這江叫作“漾濞江”。我記得后來(lái),彭工程師和他的助手不時(shí)地也開(kāi)始說(shuō)出“漾濞江”三個(gè)字來(lái)。五個(gè)人在一起工作,我們?nèi)齻€(gè)人,他們兩個(gè)人,我們的影響力要更大一些,更何況,在我們所有勘測(cè)的沿江流域,所涉及的每一個(gè)人物對(duì)象都無(wú)一例外地把這江稱為“漾濞江”。我猜想,在彭工程師和他的助手來(lái)到這里之前,他們已經(jīng)知道這條江在當(dāng)?shù)乇蝗藗兎Q為“漾濞江”,但也僅僅只是知道這一點(diǎn)而已,對(duì)于他們來(lái)說(shuō),關(guān)于這條江的這個(gè)地方性稱謂還只是一個(gè)客觀的概念。而當(dāng)他們來(lái)到了這里,從進(jìn)入雞街工作開(kāi)始,在差不多一個(gè)月的時(shí)間里,關(guān)于這條江的名字,在他們的意識(shí)當(dāng)中被當(dāng)?shù)氐娜藗儫o(wú)數(shù)次地灌輸以“漾濞江”三個(gè)字。當(dāng)他們最后完成勘測(cè)工作離開(kāi)的時(shí)候,“漾濞江”三個(gè)字在他們的意識(shí)里,想來(lái)已不再僅僅是一個(gè)客觀的地理稱謂,而是變成了一條與他們?cè)谶呥h(yuǎn)山區(qū)的某一小段時(shí)間相連的、在上面連綴著當(dāng)?shù)氐纳健⑺⑷恕⑽锷踔溜L(fēng)雨晴暖等具體內(nèi)容的有著具體流動(dòng)形態(tài)的江流。而與此同時(shí),在我的內(nèi)心里,對(duì)于“黑潓江”三個(gè)字,也開(kāi)始慢慢有了一種陌生的親切感,知道了這兩個(gè)名字,她們?cè)瓉?lái)是一體的。在這之后,當(dāng)我在一些場(chǎng)合對(duì)人說(shuō)起這條江的時(shí)候,有時(shí)也會(huì)根據(jù)情形,說(shuō)出“黑潓江”三個(gè)字來(lái)。
當(dāng)然,也就是僅此而已。在更多的時(shí)候,我,以及在這條江的流域世代生息的人們,仍然像稱呼自己的母親那樣,一如繼往地把這條江稱為“漾濞江”。我們像知道外婆家的路那樣,知道這江從同屬大理州的劍川的劍湖流出來(lái),流經(jīng)了洱源縣,從北到南流經(jīng)漾濞大地。在出漾濞縣境之后,這江進(jìn)入了緊鄰的保山市昌寧縣。當(dāng)然,我們還知道這江最后匯入了瀾滄江。然而多年來(lái),除了從內(nèi)心出發(fā)去感受這條江之外,我一直不曾在某一幅地圖上細(xì)細(xì)地看過(guò)這條江流,不曾以除了置身其中以外的另外一種角度,細(xì)細(xì)審視過(guò)這條江流的所來(lái)和所向。
是在我終于想著要寫(xiě)寫(xiě)這條江的時(shí)候,家里正好有一幅云南省測(cè)繪工程院2011年5月編制的1:1800000的云南省旅游交通圖。于是我,第一次在一幅地圖上細(xì)細(xì)地看了這條江,這條自己數(shù)十年的人生都一直與她相伴的江。在上面,我看見(jiàn)這江彎曲的流向,看見(jiàn)那條細(xì)細(xì)的藍(lán)線從劍川縣的劍湖畫(huà)出來(lái),畫(huà)過(guò)劍川的甸南鎮(zhèn)、沙溪鎮(zhèn),洱源的喬后鎮(zhèn)、煉鐵鄉(xiāng),直到進(jìn)入漾濞縣境之前,這條藍(lán)線都被標(biāo)注為“黑潓江”。在從北到南流經(jīng)漾濞全境的部分,藍(lán)線上的標(biāo)注變?yōu)椤把ń薄V螅瑥某鲅ㄒ恢钡搅魅霝憸娼囊欢危@藍(lán)線才重又被標(biāo)注為“黑潓江”。——我忽然對(duì)面前的這幅地圖有了一種親切感。在外界,有許多人把這條江整個(gè)稱為“黑潓江”,把這條江的流域整個(gè)稱為“黑潓江流域”,而這幅地圖,它在上面把這江流經(jīng)漾濞的長(zhǎng)長(zhǎng)一段標(biāo)注為“漾濞江”,這一標(biāo)注,它更多了一種對(duì)一個(gè)地域的歷史、文化以及民族情感的尊重。
在這幅地圖上,我還注意到了這條江的源頭。我們之前一直說(shuō)是來(lái)自劍川的劍湖,算是一種官方認(rèn)可。在地圖上,我才發(fā)現(xiàn),劍湖又來(lái)自另外一條河流:麗江境內(nèi)的九河。“九河”是我對(duì)這條河的命名,因?yàn)槲铱吹皆谶@條河的源頭上,有一個(gè)名叫“九河”的鄉(xiāng)鎮(zhèn),我于是以我們雞街鄉(xiāng)、雞街河那樣的推理為之命名。至于九河的更細(xì)微的源頭,地圖上沒(méi)有顯示和標(biāo)注。
江從劍湖出來(lái),甸南鎮(zhèn)、沙溪鎮(zhèn),洱源的喬后鎮(zhèn)、煉鐵鄉(xiāng),全都依江而居。進(jìn)入漾濞,漾濞的漾江鎮(zhèn)、平坡鎮(zhèn)、縣城所在的蒼山西鎮(zhèn)以及瓦廠鄉(xiāng)四個(gè)鄉(xiāng)鎮(zhèn)的政府機(jī)關(guān)也都臨江而建,順濞鄉(xiāng)、雞街鄉(xiāng)兩個(gè)鄉(xiāng)則各自以棲于漾濞江的重要支流順濞河和雞街河之側(cè)的形態(tài)靠近漾濞江。
出了雞街,漾濞江流入相鄰的保山昌寧縣,地圖上標(biāo)注這一段沿岸的地名有比此——這是一個(gè)村,緊鄰我們雞街鄉(xiāng)菜白村龍鳳社;羊街——這地方產(chǎn)茶,當(dāng)年江橋集市興盛的時(shí)候,有許多羊街人不辭遠(yuǎn)路趕著牲口來(lái)江橋街上賣(mài)茶葉,成為集市四面村寨里所消費(fèi)的茶葉的主要來(lái)源;珠街——這是一個(gè)鄉(xiāng)鎮(zhèn),以滇西的人們習(xí)慣以十二屬相為地區(qū)命名,并且在這一區(qū)域內(nèi)就有我們漾濞的雞街,永平、巍山各有一個(gè)龍街,巍山緊鄰龍街有牛街,相鄰的永平和昌寧各有一個(gè)羊街等等地名來(lái)看,這昌寧的珠街,想必原本是為“豬街”,“珠街”應(yīng)是同音雅化。
漾濞江從劍川一路出來(lái),一直到漾濞縣城的近百公里,再加縣城到平坡鎮(zhèn)的十多公里,流向一直為西北向東南。在平坡集鎮(zhèn)腳下,漾濞江接收了從洱海出來(lái)的西洱河,之后一個(gè)拐彎,一路向南。從平坡出來(lái)不久,在漾濞江的南岸,巍山縣有很長(zhǎng)一段縣境與漾濞隔江相對(duì),一路有紫金鄉(xiāng),馬鞍山鄉(xiāng),原來(lái)的龍街鄉(xiāng)(后來(lái)因鄉(xiāng)鎮(zhèn)撤并歸為五印鄉(xiāng))。過(guò)了漾濞往下,巍山在沿江附近的鄉(xiāng)鎮(zhèn)還有牛街鄉(xiāng),青華鄉(xiāng)。
從古以來(lái),人們逐水而居的意念從來(lái)沒(méi)有變過(guò)。漾濞江從劍湖發(fā)出(或者說(shuō)從麗江出發(fā)),一路流經(jīng)洱源,漾濞,巍山,昌寧,南澗,在一條江的兩岸,密布著眾多的集鎮(zhèn),以及無(wú)以計(jì)數(shù)的村莊。這些村莊以及集鎮(zhèn),與這條江所有大大小小的支流一起,共同構(gòu)成了一條江久遠(yuǎn)的歷史,滋養(yǎng)出了“流域”這個(gè)詞語(yǔ)的厚重以及深邃。
應(yīng)該說(shuō)是從當(dāng)年在鄉(xiāng)上的時(shí)候開(kāi)始,我慢慢注意到了一個(gè)事情:在江的兩岸居住的彝族人,有許多“左”姓,并且,靠江越近的地方,“左”姓就越為集中。在漾濞這邊,包括瓦廠鄉(xiāng)的瓦廠村,我們雞街鄉(xiāng)的達(dá)村和菜白村都有許多“左”姓,尤其是雞街達(dá)村我的老家密喜把社、菜白村沿江的吐路么社、本竹社、卡馬咋社、龍鳳社又更為集中。在江的對(duì)面,與我的老家村莊密喜把隔江相對(duì)的阿系古社,雞街河門(mén)口對(duì)面原屬龍街鄉(xiāng)現(xiàn)為五印鄉(xiāng)的底固等,“左”姓也明顯集中。下到昌寧的珠街,也有許多彝族,聽(tīng)說(shuō)也還有一些“左”姓。隔江稍遠(yuǎn),姓氏主要有常姓、茶姓(漾濞當(dāng)?shù)厝藗円幌蚰J(rèn)“常”“茶”同為一姓),習(xí)姓,楊姓,李姓等,在漾濞、巍山兩地沿江地區(qū)的分布“海拔”也都大體對(duì)應(yīng),并且也全都是彝族,有著相同或相近的語(yǔ)言、生產(chǎn)生活以及文化習(xí)俗。在我的村莊里,老人們?cè)鴤髦旁挘f(shuō)我們是南詔的后裔,至于我們姓氏的漢化具體是始于什么時(shí)代、什么原因,則已無(wú)從考察。在我之前所接觸的范圍內(nèi),似乎對(duì)這一問(wèn)題也不曾見(jiàn)到過(guò)相關(guān)的考察和論證。
漾濞設(shè)縣較晚。漾濞南部我的家鄉(xiāng)一帶,早時(shí)一直歸蒙化府(現(xiàn)巍山縣)所屬。1912年漾濞設(shè)縣,縣治為從當(dāng)時(shí)蒙化府和永昌府(今保山市)各劃一部分,形成現(xiàn)在的漾濞,縣境國(guó)土面積為1957平方公里。1985年,漾濞經(jīng)國(guó)務(wù)院批準(zhǔn),成立彝族自治縣。
從精神到地理,這條名叫漾濞的江,她所涵蓋的意義,都遠(yuǎn)遠(yuǎn)不止于是一條自然的江河。
編輯手記:
作家左中美筆下的漾濞江,更多是那段流經(jīng)自己故鄉(xiāng)的那一段,它除了是自然意義上的江,還是一條精神意義上的江,是眾多自己所熟識(shí)的人與物命運(yùn)交匯的一條江。作家寫(xiě)自己的記憶時(shí),往往是以一種離鄉(xiāng)者的角度來(lái)重新回到故鄉(xiāng),回到與這條江有關(guān)的那些故鄉(xiāng)的人,一些人在消失,一些物在消失,很多生命與物的消失與江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作家在這里提供的是面對(duì)故鄉(xiāng)的至少一種方式,那些美好的記憶,那些美的因子如漾濞江一般淌入心底,那些與丑相對(duì)的被過(guò)濾,那些隨著時(shí)間的推進(jìn),而不斷向好的故鄉(xiāng)呈現(xiàn)在了人們面前。那是一種過(guò)往與現(xiàn)在之間美好的呼應(yīng),那些過(guò)往更多是作為一個(gè)童年視角的我在回看,而此刻的漾濞江與故鄉(xiāng)是成年的我在看,兩種看的視角在這篇散文中交錯(cuò),也讓故鄉(xiāng)和作為故鄉(xiāng)一個(gè)重要部分的漾濞江變得豐富起來(lái),我們看到的是一個(gè)活的故鄉(xiāng),以及一條流淌不息的漾濞江。
左中美,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出版有《不見(jiàn)秋天》《時(shí)光素箋》《拐角,遇見(jiàn)》《安寧大地》4部個(gè)人散文集。多年來(lái),在《民族文學(xué)》《文藝報(bào)》《散文》《美文》《散文選刊》等報(bào)刊發(fā)表散文作品逾百萬(wàn)字。作品入選《2014年度中國(guó)精短散文》《2017年度中國(guó)精短散文》《2017年度中國(guó)隨筆精選》等多種選本,文章入選多地初、高中語(yǔ)文試卷閱讀題。曾獲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作家學(xué)會(huì)文學(xué)獎(jiǎng)、第六屆“中華寶石文學(xué)獎(jiǎng)”、第七屆云南文藝創(chuàng)作基金獎(jiǎng)、云南省2017年度優(yōu)秀作家獎(jiǎng)、作品入選2020年度“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之星”叢書(shū)、被評(píng)為大理州首屆優(yōu)秀文學(xué)藝術(shù)獎(jiǎng)等。2017年10月,被命名為大理州“白州文化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