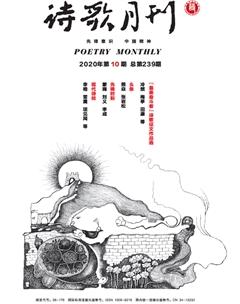胸中山河,筆底春秋
王士強
《羅平記》是我近年讀到的最好的長詩之一。可以感受到,詩人何曉坤是豁出去、動了真格的,他下決心要動用自己全部的儲備來為生長于茲的土地樹一塊碑、立一個傳。這是他深愛的土地,也是他唯一的土地,他的確做到了為之樹碑立傳。《羅平記》之于羅平尤其重要,它是一次終結,也是一次開始,是時間長河中具有節點性意義的一件大事:時間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歌者,羅平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詩人,擁有了與其滄海桑田、生生死死、多災多難的歷史相稱的詩性言說。“羅平”與《羅平記》具有一種互相成全的關系,羅平以其厚重、豐富、可歌可泣的歷史與現實滋育了《羅平記》,予其以血脈和精魂;而《羅平記》則在詩學的層面上對羅平進行了總體性的、深度的提煉與總結,體現著文化、文明的薪火相傳,并將把“羅平”推向外界,使之成為一個重要、獨特的文化符號和地標。當然,這一切的基礎,是作品的人文內涵和藝術品質。《羅平記》首先是何曉坤一個人的,是他個人的心靈史、精神史和懺悔錄。他首先寫出了他自己,寫出了一個人的血與淚、喜與悲、信任與懷疑、奮斗與放棄……而后,才寫出了一代人、一代代人的羅平,才具有了代這一片土地發聲、為羅平樹碑立傳的能力與可能。也因此,《羅平記》避免了“大”與“空”,避免了成為理念的“傳聲筒”,而具有意味無窮、耐人尋味的盎然詩意。
一
何曉坤寫羅平,由古到今,由外而內,方方面面,無所不包。他的胸中包含了羅平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的目光則穿越了千秋萬代、滄海桑田,的確做到了“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這注定是一件苦差事,是力氣活,它要求寫作者動用巨量的生命積累、知識儲備、情感經驗、精神意志……因為面對如此龐大的書寫對象,怎樣的投入都是不嫌多的,它需要寫作者有一種相匹配的精神結構和主體力量,否則,寫出來的東西要么力不能敵、瞎子摸象,要么空洞浮泛、淡乎寡味。恰恰,何曉坤是一個有著大體量、大心臟,內心強悍而又無比溫柔的人,他對所生存的土地有著強烈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他與羅平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內在的同構、對應關系。
回到過去、回到原點,才能夠定義自我,明白“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并進而回答“我要到哪里去”。然而,回視過往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回到前塵的鑰匙/一直握在我們手中/只是我們,從來沒有/轉動的勇氣”。理論上講,面對過去是一件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情,在現實中之所以變得如此困難重重,無疑是由于人類的某種迷失、羞愧、逃避。而詩人,自然需要面對這一切、迎難而上。“往回走!一直走!/走到時間的原點,我們就到了/石頭的深處。”“石頭”是時間的見證、歷史的化身,它看起來堅硬冷漠,卻包含了水與火,是經水火熔鑄而成,“它們共同完成了/時間的檔案。所有的劇情/都可以忽略。所有的揣度和禮贊/都形同虛設。在熔為石頭的/鐵證面前,只有時間/如石頭般清白,如石頭般/沉默!”在永恒的時間面前,一切的價值都有了重估的必要,一切都呈顯出了另外一種面貌。“城西的白臘山,二億三千萬歲了。/很難考證,這么久遠的時光/它有沒有,長高了一點。/而風,從那時開始吹起/至今從未停歇。”在如此長的時間刻度前,人類微渺,人生短暫,地老天荒自然而然便具有了某種神性。神性一定意義上也是人確證自我、對抗時間的方式,“羅平人”“堅信”:
每一座山頭,都是一座廟宇。
每一片原野,都可以回蕩
木魚的聲音。每一聲鐘鳴
都應該成為絕唱!而我們不用抵達
因為無從抵達。我們要抵達的
只是我們的內心。
這其中呈現了一種非常特別的景象:自然即神、神即自然,沒有遙不可及的遠方和彼岸,人的內心即是遠方和彼岸……“神”不是唯一的、絕對的存在,它更多的是一種尺度,是內心的敬畏與規約,神性更多不是外在的,而“只是我們的內心”,或者說,是我們的“心”。何曉坤的《羅平記》,也正是面對“內心”的寫作。對于急匆匆趕路,氣喘吁吁,很大程度上已經把靈魂走丟、把心走丟的現代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尷尬、奢侈卻又至關重要的問題。“人間花團錦簇/塵事蒼茫如幕/搬一座山在心中/就可以安然入眠”,這樣的“一座山”是給人依靠、讓人安全的一種力量,是人的來處、緣由、基礎,有它,心便可踏實,人便可安定。
歷史的行進從來不只是風和日麗、花好月圓,而更多的是血雨腥風、斷壁殘垣。《羅平記》寫到了歷史中的梟雄、魔頭,也寫到了令人仰望的往圣先賢,他們構成了歷史和文明演進中的關鍵因素,或遺臭,或流芳,為時間和后人所記取。比如明代的者繼榮,他弒父奸母、聚眾謀反,“成為迤東時空深處/最丑陋的疤痕”,“魔鬼讓時間停在了苦難的原點/他讓萬歷十三年的花朵,尚未綻放/便成為迤東大地上,無處藏身的/孤魂。恐懼和仇恨,眼淚和血/凝成天空的背景,凝成釘子/穿透山河的心。”而后者如黃禮門,“這個信仰與良知的囚徒/因此想到了文字和水,寬闊與柔軟/想到溫度,濤聲,以及濤聲背后/漸漸清晰的面孔。”他建文廟、興禮教,為官清廉,品行高潔,成為精神、信仰、光明的使者,“他堅信靈魂的碎片,足以抵御/從舊州到磨盤山麓的利刃。堅信/陽光下行走的影子,將一路綻放蓓蕾!”由此而“成為一座城市的奠基者,成為一塊土地的/喊魂人!”這樣“信仰與良知的囚徒”代表了文化、文明的存在,而一代代如此的“囚徒”則構成了薪盡火傳的鏈條,這是形成“迤東文脈”的基礎,是“文化羅平”的重要品格和內在秘密。
神性、尊重與敬畏是這一文脈的重要維度,它構成的是天、地、人、神的和諧共處。“這條蜿蜒而來的山脊,一直與神為伴/從曉寺到香山寺,從玉皇閣到文廟/紛至沓來的山頭,眾神有序而居/所有人都說,這是迤東的文脈”,神是一種映照、鏡鑒,他是構成文明、文脈的基礎。詩中寫:“黃禮門也認同這個觀點。他還認為/天地間應該有一面鏡子,于是他掘了/太液湖。在迤東大地上/這面鏡子,已經整整掛了430年”——
那天在白臘山頂,我看見魚兒
飛翔在云朵之上,看見所有的高處
原來都在低處。那天在太液湖畔
我看見鳥兒,遨游在澄波之下
看見所有的低處,原來都是高處
這并不是對于神的消解,而恰恰是對于神的發揚。一方面,神是在的,是有的,他在高處,也在低處,而高處便是低處,低處便是高處,他無處不在;另一方面,神并不是對于人的否定,而是對于人的完善與提升,他是為人的、有人間性的,人的身上、萬事萬物身上皆可具有神性。“所有的高處,原來都在低處”“所有的低處,原來都在高處”,這里面包含了多么簡單而又復雜、淺顯而又深刻的認知與發現!再如關于水的書寫。如果說詩中關于山峰、石頭的書寫代表了大自然之堅硬、不變的一面,那么水則代表了其柔軟、變化的一面;但是,這種柔軟同樣有著堅硬與強韌的力量,一定意義上甚至要更為堅硬與強韌。古語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羅平記》中寫:“它們的流淌/隱蔽而安靜。它們全都從高處/出發,在低處抵達/它們把所有顯目的位置/都讓了出來。在巖縫里,泥土中/樹根之下或草叢深處,完成涅槃/之后開始用身體唱誦梵音/用身體演繹經文。在迤東大地的/每個角落,發自肺腑地珍惜/每一次遇見,并讓每一次遇見/從此不再分離。”這主要是寫其“小”,但由小而大、由少而多,它最終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存在,成為一種撫慰性力量和與天空相對位的存在:“它們因此成為山泉/成為溪流,成為我們心中的/江河與湖泊。它們還會向/更低的地方流去,最終成為/海洋,成為巨大的存在/這讓每一滴水,都有了意義/像多依河與九龍河,用身軀/蓋住羅平所有的傷口/也像遙遠的塊擇河,每一朵浪花/都遙望著天空”。水、河流由此成為生命與文明的源頭,同時也具有了一定的神性特征。當一個地方的山與水、天與地均具有了神性,生活于其間的人自然也會變得莊嚴、肅穆起來,而不再僅僅是無智慧、無靈性、生死由之、混沌無明的生物。
二
《羅平記》處理的核心問題之一,是精神性的“信”。在變動不居的歲月長流中,什么是可以信賴、值得信賴的。“信”與信仰庶幾同義,卻又不是狹義的、宗教意義上的信仰所能夠涵蓋的。“信”關乎每個人,關乎靈魂、內心,有這種“信”,方可找到自己、確認自己。沒錯,《羅平記》正是何曉坤在尋找自己,尋找“回去”的道路,并與往圣先賢進行的一場精神對話。正如他在詩中所說:“先賢啊!賜我一盞燈!/讓我毫無恐懼地/回去!”這是他向自己精神的策源地、大本營所發出的吁請,更是自我的激勵與壯行。“回去”,回到哪里?說簡單也簡單,便是回到內心、回到起點、回到自己。“只有來到太液湖/只有看到鏡中人/我們才敢確認/自己,沒有丟失”,在鏡子、在他者、在客體對應物的映照之下,才能夠重新發現自我。現代語境下,更多的人是被遮蔽、被遺棄了,找不到自己,甚至也不需要自己了。故而,這種重新發現,很大意義上是失而復得,是意義重大的。詩中關于從文廟到醫院的書寫頗具象征意味,這種變遷或許不無合理性,從現代化的角度來看也是不得不如此的、不可逆的,但是問題卻依然存在,甚或更為凸顯:“重要的是/除了安身之外,我們還得找個地方/安心!和安魂!”這一問題既有現實意義和緊迫性,也是一個關乎“人”、關乎人類的“元命題”。
如何安心、安魂?“從塊擇河峽谷出來的人/都會在時間之外,回到河谷之中/從塊擇河峽谷出來的人,很多的傷痛/都已忘記。忘不了的,是浙溪書院/中天斗閣、清真寺、天主教堂/以及危崖孤石之上的觀音寺/這個地方,只屬于時間和信仰/屬于禱告和懺悔,以及燈火通明的經堂/經堂里出來的人,都會說/那些死了的人,一些在天上/一些歸于塵土,還有一些/下落不明”。在“時間和信仰”面前,有著各色人等,有著不同抉擇,最后的去處自然也各有分別。他寫人“應該”做的事:“應該努力靠近石頭,靠近水/靠近心中那顆,搖搖欲墜的淚滴/應該在黑暗中,采擷光亮/在傷口結痂的地方,種植花朵”,其中的意象多是有所指、有象征意義的,黑暗與光亮、傷口結痂與種植花朵具有直接、感人的力量。“熙熙攘攘的靈魂,來路都不清楚/去處,卻驚人的一致/熙熙攘攘的靈魂,仍燃燒著煙火/數不盡的悲歡,一刻不停地/從人間穿過。/心中的石頭,應該在/流水的中央。流水之下/是堅實的大地。心中的寺廟/應該在石頭的頂端,寺廟之上/是高闊的天穹。”人世熙攘、紅塵萬丈、溢彩流光,但在這背后,是內心能夠信仰、依靠、仰望的一些東西如大地、天空、寺廟等等。沒有內在的豐盈與妥帖,外在的一切不過是自欺欺人和過眼浮云。詩中有一節專門談“信仰”:
信仰之于人世
就是當你在黑暗中獨坐時
依然能夠看見一座山,和山頂的霞光
也能看見一條河,及河中的波瀾
簡練、生動而傳神!有這樣的信仰,自然也便是有希望、有力量的,同時,也是沉靜、有歸屬的。信仰本身便是一種光和熱,它是一種照亮和溫暖。人生的太多問題,都與這個“信”有關。
何曉坤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他對羅平這片土地有著深摯的愛,他熟悉這里的一切,對之懷有深沉的感情。同時,他又是出離的、超脫的、不僅僅屬于當下的,而往往是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是從未來的、永恒的視角看取當下,具有穿透性、反思性。羅平那色多山峰,被稱為“那色峰海”,是一道著名景觀。詩人頗為辯證地寫了那色的“空”與“不空”。首先是“不空”:“那色不空/那色的峰,已被稱為海/有野心的人,總能看見千軍萬馬/列出了新的陣形。石頭和森林/讓排山倒海的誓言,在那色/成為可能,那色不空/那色的風,沒有一點腥味/隨風而去,能找到預言者的遺骸/化為滿山的舍利/那色不空,那色的天空/有翅膀的劃痕,也有絨羽的吻印/有人身在遠方,卻把魂/寄存在那色的云朵中”……詩中寫了諸多的“不空”。它是萬千世相,是事功,是變化,是實有。但是,另一方面,那色又“本空”:“那色本空/萬千景象皆在云霧中”。云霧起,萬千景象均遁失不見,一切成為空空,這或者是比“不空”更為恒久、更為本真的存在?抑或,云霧與景象,孰為本孰為末,孰為假孰為真,莊周夢蝶,蝶夢莊周,如何分得清楚?通過這“空”與“不空”,何曉坤往來于天地、神界與人間、俗世之間,出世而又入世,入世而又出世,可謂是生而又死、死而又生,既是朝圣、修行,又是苦熬、纏斗。但無論是“空”與“不空”,最終仍是落腳于人,為人、為人生、與人生有關。正如他極有見地地指出的:
最大最透的那顆舍利
一直在人間鬧市的熔爐中!
鬧市、世俗生活、人間煙火,并不是需要克服和摒棄的對象。而人們所要返回的“內心”、所要尋找的“自己”,所要建立的“信仰”,都需要投入到“鬧市的熔爐”中去求取。這實際上也是對人的肉身性、世俗性的禮贊,精神性、靈魂性的維度自然是需要的,但應該以肉身性、世俗性為基礎和前提,否則,就可能陷入某種誤區。在這個意義上,《羅平記》于其作者何曉坤而言,更大程度上是“在羅平記”,他記錄了一個人在生活中的摸爬滾打,記錄了精神的遭際與磨難,記錄了他與世界、與自我的對峙及和解。于羅平而言,他既是“在”的,又是“不在”、出離的,因為只有離開羅平才能更好地看清羅平,“在”一定意義上是需要以“不在”為前提的。可以說,這首詩中既有“出羅平記”,又有“回羅平記”,回還往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方形成這部“羅平記”。
三
《羅平記》在結構上獨具匠心,全詩三百余行,26節,卻絲毫不給人冗長的感覺。全詩首尾呼應、錯落有致,既有內容的充實、厚重,又有語言的輕盈、靈動,有如一部復雜精妙的復調音樂、交響樂,輕與重、長與短、強與弱等的結合、搭配體現出良好的平衡感。一般來說,每節之間均是長短間隔,一節較長,表達的內容多,往往句式也長、密度高、質量重,是宏觀敘事、大敘事,繼而的一節便較短,二到五行不等,內容少,密度小,句子更為靈動、輕逸,往往是小敘事、微觀敘事,這種節奏性、音樂感是頗為獨特的。整首詩有宏闊的思考與關切,又有細部的扎實與豐盈,技藝、節奏、語言與形式等方面均有獨到之處,耐尋味,耐咀嚼,種種妙處不一而足。
無論是在題材的獨特性、內容的厚度、思想的深度,還是藝術的創造性與完成度上,《羅平記》都堪稱卓異,屬于那種一次性寫作、可遇而不可得的作品。它穿越時空,實現了歷史正義與詩性正義的共時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