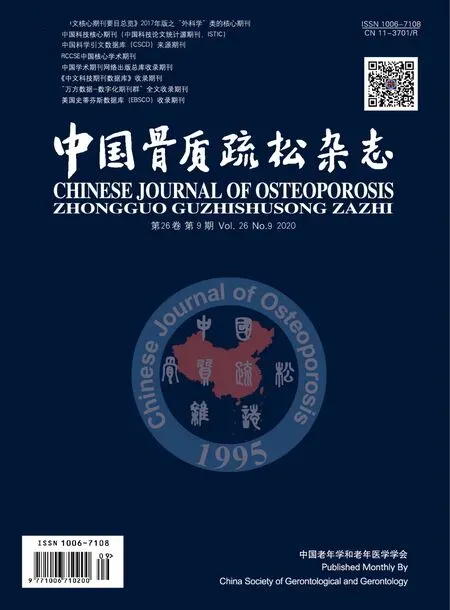阿茲海默癥骨骼研究進展
張玲莉 元宇 雷樂
1.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10631 2.上海體育學院,上海 200438
阿茲海默癥(Alzheimer’s disease, AD)是一種起病隱匿的進行性發展的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會導致記憶喪失、認知缺陷和行為變化等全面性癡呆表現。目前主要病理特點是β淀粉樣蛋白斑塊的積聚和過度磷酸化Tau蛋白神經原纖維纏結,但病因迄今未明。65歲以前發病者,稱早老性癡呆;65歲以后發病者稱老年性癡呆。大多數AD的發生都是零星起病或以非孟德爾的方式遺傳,和不到1%的病例是常染色體顯性遺傳。零星起病不會顯示出家族聚集性,具有復雜的遺傳和環境的相互作用[1]。
骨是人體的主要結構支架,骨質疏松癥是以骨量下降和骨組織微結構退變為特點的退行性疾病,骨脆性增加[2]導致的骨折等并發癥可致殘、致死[3]。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降低及其臨床后遺癥骨質疏松癥是AD患者常見的并發癥[4],出現在疾病早期,未見明顯的認知功能下降[5]。流行病學發現二者具有很高的共病率[6],但目前對它們之間聯系的機制知之甚少。近年來,通過對骨源性細胞和其分泌蛋白的研究,證明骨骼與其他幾個器官系統相互作用[7]。研究表明,大腦似乎屬于這個相互聯系的網絡[7]。
本文查閱國內外大量文獻,總結AD患者和動物模型的骨表型,深入探討AD相關的骨骼信號轉導通路以及骨骼來源的細胞移植和骨骼相關維生素、micro-RNA對AD的影響,試圖為AD患者骨質疏松的預防和治療提供新的理論依據,為今后篩選基因輔助治療AD提供關鍵性靶點,同時也開拓研究AD的新思路。
1 阿茲海默癥患者的骨骼表型
1.1 骨密度下降
2005年報道,在社區的隊列研究中納入987名社區居民,檢測了受試者的股骨頸、股骨大轉子和橈骨軸的BMD并跟蹤隨訪8年,發現女性的股骨頸BMD偏低,且與AD發病風險有正相關聯系,但在男性結果中并無反映[8]。性別和年齡是AD發病過程中納入討論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考慮性別,臨床上AD患者的篩查、治療以及照顧就會受到較大的阻礙[9]。Rentz等[10]發現中年女性的所有記憶測試均超過同齡男性,但絕經后女性的記憶略有下降。Loskutova等[11]發現早期AD患者BMD降低,且與腦萎縮和記憶力下降有關,這表明中樞機制可能導致早期AD患者骨質流失。Loskutova等[12]對71名早期AD老年患者和69名健康人進行了為期2年的觀察性研究,檢測受試者的BMD、身體成分、下丘腦體積、血清瘦素、生長激素和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IGF-1)水平,初步得出AD患者骨質流失可能與下丘腦的神經退行性萎縮有關。血清素合成減少后hTau小鼠(AD模型的一種)骨骼中的Tau蛋白過度磷酸化,其腦干中色氨酸羥化酶蛋白總體減少,而中縫背核中色氨酸羥化酶陽性細胞減少70%。中縫背核是調節成年骨骼的關鍵結構,提示基于Tau蛋白的AD小鼠模型中,BMD降低比腦部磷酸化發生得更早[5]。
1.2 骨質疏松
Zhou等[13-14]用雙能X線(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檢測了946名60~75歲的中國男性和女性腰椎和髖部的BMD,且縱向持續追蹤了5年,通過簡易智力狀態檢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和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ssessment of the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量表的篩選和測評發現骨質疏松與認知功能衰退成正比,呈現出低BMD,總結出骨質疏松會增加AD起病的風險。Liu等[15]隨后將樣本量擴大至1 802名AD患者,實驗方法一致,追蹤觀察了6年,得出相同的結論。
1.3 骨折
Liang等[16]采用Meta分析對AD患者骨折風險進行量化,137 986名受試者被納入隊列研究,經過分析發現AD是髖部骨折的一個危險因素。
AD骨骼表型研究多集中于臨床研究,主要表現為BMD降低、骨質疏松和骨折風險性增加。上述研究僅從BMD等宏觀指標觀察性探討了AD患者骨骼表型,較少涉及到動物和細胞基礎實驗,因此對于引起BMD降低的骨轉換(包含破骨細胞介導的骨吸收和成骨細胞介導的骨形成)目前也尚未可知。
2 阿茲海默癥相關的骨骼信號轉導
多條轉導通路參與骨髓間充質干細胞(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MSCs)分化的胞內信號調控,Wnt/β-catenin信號通路、骨形態發生蛋白信號通路(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signaling pathways, BMPS)等是BM-MSCs向成骨細胞分化的主要途徑。
2.1 Wnt/β-catenin信號通路
Wnt信號通路在腦、骨骼的結構和功能的正常發育和維持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7]。Wnt蛋白配體與卷曲蛋白結合受體是激活Wnt信號通路的關鍵。經典Wnt/β-catenin信號轉導通路是骨骼發育和穩態所必需的通路,在成骨早期,Wnt/β-catenin信號通路的上調可激活Runt相關轉錄因子2(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2, Runx2)、鋅指結構轉錄因子(osterix, OSX)和堿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 ALP)等基因和蛋白的表達,進而促進BM-MSCs向成骨分化[18-19];在成骨晚期,Wnt/β-catenin信號的下調又是成骨細胞終末分化和骨鈣蛋白表達的關鍵[20]。在大腦中,Wnt信號參與軸突引導、成神經細胞遷移和神經元增殖分化,其功能障礙會引發AD[21]。Dengler-Crish等[22]發現6到14月齡雄性hTau小鼠(一種AD小鼠模型)較之于同窩對照和C57BL/6 J對照持續存在低BMD,骨細胞基因表達顯著下調,骨骼重塑受損。且在hTau小鼠大腦和神經中,Wnt/β-catenin信號通路明顯受到抑制。表明Wnt信號功能失調可作為AD骨骼流失的一個潛在靶點。
Dickkopf1(Dkk1)是Wnt信號重要的抑制劑,與骨骼的穩態和骨質疏松密切相關[17]。在轉基因AD小鼠的大腦中發現Dkk1表達水平增加,提示Dkk1可能是骨質疏松癥和AD共同的潛在危險因素[23]。
2.2 BMP-Smad信號通路
骨橋蛋白(osteopontin, OPN)是一種由多種細胞類型表達的糖磷蛋白,具有促黏附和趨化,類似細胞因子屬性,它參與血管生成、細胞凋亡、炎癥、氧化應激、髓鞘再生、傷口愈合、骨重建、細胞轉移和腫瘤發生[24]。OPN是BMPS下游成骨細胞相關的mRNA,能刺激成骨細胞增殖、鈣化[25],也是一種由髓細胞高表達的母細胞免疫調節促炎細胞因子,可調節免疫細胞的遷移、通訊和對腦損傷的反應,在各種神經炎癥疾病中發揮重要作用[26]。
Sun等[26]收集35例AD患者、31例輕度認知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患者和20例健康受試者的腦脊液和血漿樣本,酶聯免疫吸附實驗分析受試者腦脊液和血漿樣本中OPN蛋白的表達水平。臨床跟蹤3年后,發現13例MCI患者轉換為AD,18例仍為MCI患者。AD和MCI患者腦脊液中的OPN水平較之于健康受試者顯著增加,同時新診斷AD患者腦脊液和血漿中OPN蛋白水平患者的平均年齡高于慢性患者;縱向實驗中當MCI患者轉換為AD后其腦脊液和血漿中OPN水平增加。Cheng等[27]招募了98名AD患者和101名健康老年人并收集了血漿樣本,利用液相芯片技術檢測50種血漿蛋白,發現AD患者血漿中的OPN蛋白水平顯著高于健康老年人(P<0.01)。Wung等[24]檢測AD患者病例樣本,發現59歲到93歲AD患者海馬中OPN表達量顯著高于對照組。免疫細胞化學定位OPN在錐體神經元的細胞質中。大腦中的OPN水平和巨噬細胞浸潤有著較強的相關性,主要反映在OPN和Aβ斑塊之間有緊密的聯系。抑制OPN的表達后影響Aβ纖維的吸收,表明OPN在調節巨噬細胞免疫和抵抗致病Aβ的能力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8]。
3 骨骼來源的細胞對阿茲海默癥的影響
3.1 骨髓間充質干細胞
BM-MSCs是一種具有多向分化能力的成體干細胞,位于骨髓腔內。在一定的微環境或培養條件下,BM-MSCs可誘導分化為成骨細胞、軟骨細胞、脂肪細胞、成肌細胞、神經細胞和血管內皮細胞等[29]。而成骨細胞、骨細胞和破骨細胞的數量和協調活動決定了骨骼重塑和骨量的變化,因此BMSCs對骨骼發育和骨轉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成人BM-MSCs能夠再生神經細胞,且神經干細胞/祖細胞是治療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如AD、帕金森病和亨廷頓病的理想方式[30]。BM-MSCs系統移植對APP/PS1轉基因AD小鼠神經炎癥具有免疫調節的作用。Naaldijk等[31]對APP/PS1轉基因AD小鼠進行尾靜脈注射MSCs,分析小膠質細胞組織學、淀粉樣蛋白pE3-Aβ斑塊數量、膠質和pE3-Aβ斑塊大小分布;尾靜脈注射28 d后小鼠大腦皮層的小膠質細胞數量和大小都減少,且pE3-Aβ斑塊在海馬中變小。這些研究結果支持MSCs移植可能通過免疫調節功能作用于小膠質細胞進而改善AD病理的假設。Salem等[32]給予AD 大鼠單次靜脈注射BM-MSCs,觀察其4個月后療效,定位受傷的腦區,發現乙酰膽堿轉移酶的陽性細胞數量和生存表達顯著增加,同時Seladin-1和Nestin的表達水平也增強。組織病理學檢查表明BM-MSCs可清除海馬淀粉樣斑塊。在探究AD模型中BM-MSCS的作用時發現移植BM-MSCs,增強Seladin-1和Nestin的表達水平可能通過激活PI3K/Akt和ERK1/2信號通路,提示BM-MSCs是一種治療AD腦損傷的潛在方法[33]。Bae等[34]研究表明BM-MSCSs有助于減少Aβ斑塊和改善突觸傳遞,從而緩解AD前兆的小鼠模型。Lee等[35]通過BM-MSCs系統移植,發現可以減少APP/PS1轉基因AD小鼠大腦淀粉樣蛋白沉積,挽救記憶缺陷。
3.2 小膠質細胞
小膠質細胞可產生形變運動,具有較強的吞噬功能,屬于單核吞噬細胞系統的細胞,也是中樞神經系統中神經膠質的干細胞,能分化為星形膠質細胞或少突膠質細胞。神經退行性疾病患者腦內存在大量激活的小膠質細胞,并伴隨眾多炎癥因子的產生[36]。大量證據表明激活的小膠質細胞是有害的神經元,它們會加重Tau蛋白的病理分泌炎癥因子,可直接損傷神經元或者通過激活神經毒性星形膠質細胞[37]。
小膠質細胞是大腦的免疫細胞,在大腦中的增殖和活化,集中在淀粉樣斑塊周圍,是AD的一個突出特征[37]。而臨床上公認這些淀粉樣蛋白沉積是AD的主要特征。大多數AD風險基因的高表達和選擇性表達都是通過大腦中的小膠質細胞[37]。在AD轉基因小鼠模型中,淀粉樣斑塊的核心內顯示了大量浸潤的高度分化和伸長的小膠質細胞[38]。這些細胞大部分來自骨髓,在體內被淀粉樣蛋白40/42亞型特異性吸引,這些新招募的細胞對大腦中的外源性和內源性β淀粉樣蛋白也表現出特定的免疫反應[38],并通過吞噬作用參與淀粉樣蛋白的清除,從而能夠阻止小鼠腦中淀粉樣蛋白沉積形成或消除其存在[39]。提示骨髓來源的小膠質細胞抑制淀粉樣蛋白沉積和AD患者老年斑塊的形成[38]。此外,AD小鼠腦內小膠質細胞選擇性激活與腦內MSCs移植后CCL5表達升高有關,可溶性CCL5可招募BM-MSCs中的小膠質細胞并激活[40]。
3.3 單核細胞
單核細胞來源于骨髓中的造血干細胞,作為脾臟和骨髓中的單核細胞的前體細胞處于不同分化階段和種類,并最終釋放入血[41]。骨髓來源的單核細胞可以減少AD小鼠Aβ斑塊,已有研究證明單核細胞較之于內源性腦中小膠質細胞具有較強的吞噬功能,由于單核細胞具有浸潤損傷區的自然傾向,可作為AD細胞治療的最佳選擇[42]。在AD轉基因小鼠模型中,靜脈移植骨髓單核細胞進入APP小鼠后發現其大腦中Aβ沉積減少,提示移植骨髓單核細胞預防記憶損傷;即使在DAL小鼠出現認知損傷后進行移植,也能觀察到這種效應[43]。
3.4 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G-CSF)
G-CSF動員造血干細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HSCs)或BM-MSCs參與提高AD小鼠認知功能,G-CSF治療作用的關鍵中介因子是C-X-C趨化因子受體4型/基質細胞衍生因子1(CXCR4/SDF-1),其趨化后參與修復能力細胞的招募。需要指出的是,被動員的HSCs或BM-MSCs都可進入大腦內,但是只有BM-MSCs才可以補充神經譜系細胞,緩解AD小鼠大腦神經病變。提示動員的BM-MSCs通過CXCR4/SDF-1趨化性參與G-CSF治療、補充神經譜系[44]。
4 骨骼相關維生素、micro-RNA對阿茲海默癥的影響
4.1 維生素K和D
Sato等[45]在日本一家神經病學和神經精神病學的醫院中收治100例AD女性患者,對應匹配100名健康社區居民,發現AD女性患者體內營養維生素K1缺乏,會降低骨鈣素羧化,進而導致BMD的降低;而AD較嚴重患者的BMD較低,可能意味著此類患者普遍存在營養不良。陽光不足和營養不良、維生素D缺乏,是導致AD患者BMD下降的重要原因[46]。低BMD使得AD患者髖部骨折的風險增加,可以通過補充維生素D提高[46]。Sato等[47]發現陽光照射對AD女性患者骨質疏松癥和維生素D缺乏癥的具有改善作用。
4.2 Micro-RNA
Micro-RNA失調是導致神經退行性變的主要原因之一。Gupta等[48]討論了miR-9、miR-107、miR-29、miR-34、miR-181、miR-106、miR-146a、miR132、miR124a、miR153在各種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發病機制中作用,建議miRNAs作為檢測和管理AD的一種更敏感的方法。將大腦和神經中重要的miRNAs和骨骼中重要的miRNAs做一個交叉,發現共同有變化的miRNAs是Let-7f-5p、miR-106b、miR-155、miR-29、miR-181c、miR-30(如圖1所示)。

圖1 大腦和骨骼交叉miRNAsFig.1 Cross miRNAs between the brain and bone
miRNA修飾的MSCs移植是治療神經退行性疾病的一種有前景的方法。Caspases-3是micro-RNA Let-7f-5p的靶基因,Han等[49]研究發現,在AD模型中Let-7f-5p通過Caspase-3促進BM-MSCs存活,在BM-MSCs中上調let-7f-5p,降低了caspase-3表達水平從而緩解Aβ25-35介導的細胞凋亡;而減少let-7f-5p水平和增加caspase-3表達,MSCs則出現顯著早期凋亡。
5 總結
臨床認為和Aβ關系密切的蛋白質以及Tau蛋白異常是引起AD病情發展的主因。由于機理不明,AD還無法治愈,實驗室中通過研究轉基因小鼠產生高水平的人類淀粉樣蛋白,在大腦中出現斑塊,但小鼠并不會表現出人類的記憶衰退問題。很多能成功移除小鼠大腦中蛋白斑塊的實驗藥物并不能減輕人類AD癥狀。目前實證上沒有任何能有效預防AD的方式。
AD和骨質疏松癥都是兩種常見的多因素的進行性退行性疾病,與AD相關的下丘腦結構改變會改變骨骼重塑的神經和神經體液調節系統,并導致AD早期骨量丟失,進一步探討骨量丟失與AD的時間關系可能具有重要的診斷價值。
代謝組學、轉錄組、表觀基因組學、高通量分析技術的分子表達譜有助于篩查和確定AD病因、發病機制和關鍵生物標志物。從臨床上揭示AD與骨質疏松癥的關系,對于了解AD的發病機制和制定治療策略具有重要意義,GWAS研究AD表明可從骨骼出發[50]。同時進一步研究AD在骨量丟失中的作用及其調節機制也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