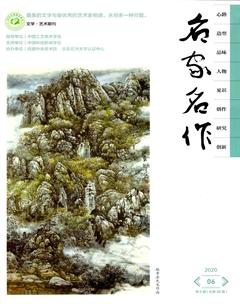雕塑中的兩種力
張怡
威廉·塔克在《雕塑的語言》一書中寫道: “物體是固定的、靜止不動的,在其自身結構既定條件的范圍內,它的生命在于喚起,甚至是重建我們的移動和自由。”塔克的論述主要是為了說明雕塑中重力感對雕塑塑造的作用。當雕塑所塑造對象的自身內在本質的力量與外在重力發生作用時,雕塑中的“活力”就誕生了。
如果把塔克所說的“重力”擴展到各種與雕塑對象內力所對立的外力,其實也是一樣適用的。比如像“風”所造成的飄動的力,或者像“雨”所造成的沖刷和腐蝕的力。這些在偉大的藝術作品中經常作為藝術家表現雕塑對象內在“活力”的對立面。
亨利·摩爾尤其善于表現雕塑內在的“活力”,而它指的活力“并不是說對運動、肢體活動、跳躍、舞蹈形象等活力的反映,而是指作品內在的被抑制的能量,屬于作品強烈的生命力”。這種“活力”正是因為被抑制,才格外動人,但是誰抑制了雕塑對象的“活力”呢?我覺得正是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的外力。
下面我從非生命體和生命體兩方面來看這種“內力”和“外力”的關系。
一、非生命體
當我們為非生命體做雕塑時,更多考慮的是這種非生命體自身材質的特性與大自然外力的對抗。例如我們在做衣紋時,衣服顯然是沒有生命的,所以它的內力其實就是衣服自身材質的力,通俗點講就是衣服面料的軟硬度、柔韌性等。而外力則是穿衣服的人給它造成的擠壓與牽扯、地心引力造成的垂落感、空氣流動造成的衣服的飄動等。外力總是存在的,而內力則因為衣服材質的不同有大有小、變化多樣。當我們在做雕塑時,所有不同的衣紋,都是由內力和外力對抗而產生的結果。軟的布料和硬的布料產生的衣紋是截然不同的,這都是由布料的內力(也就是材質的力量)所決定的。軟的布料顯然自身材質力不強,受外力的影響比較大,所以產生特定的繁復而柔軟的衣紋,并且垂感強;而硬的布料由于自身材質力較強,不太容易受外力的影響,所以產生硬朗簡潔的衣紋,并且垂感和飄動感都會比較弱。在雕塑制作中,利用外力是手段,表現材質的內力才是目的。若將兩塊軟硬不同的布分別平鋪到桌面上,顯然無法從形體的結構看出來哪塊布是硬的,哪塊布是軟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施加一個外力,讓它產生褶皺,這樣我們便可以一眼看出兩塊布的材質不同。
同樣,當我們做山石時,道理也是一樣的,不同的石材材質差別很大,軟硬不同、粗細不同,但都受風雨雷電的侵蝕。通過表現這些外力,也一樣是為了表現石頭本身的材質力。更重要的是通過表現石頭自身內力與外力所對抗而呈現的結果——一塊被風化的石頭來表現時間。因為只有經過漫長的時間洗禮,石頭才會被風化,才會有滄桑感。雕塑也從三維的空間屬性中加進了第四維的時間。雕塑的內涵也得到了延展,在摩爾的雕塑中經常能看到這樣的表達。這也是國畫作品中經常畫“枯樹瘦石”,而從不畫“新樹”或者“干干凈凈的石頭”的原因。
二、生命體
在表現生命體的時候,依然要考慮多種力之間的對抗,要塑造鮮活的生命,必須要找到這種力與力之間對抗的平衡點。打個比方,當我們要做扭腰的動作時,顯然扭動的這個力是主要要表現的力,但是人的身體有自身的結構和約束,骨骼和肌肉的屬性限制了人扭腰的范圍。我們扭動的這個力在扭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骨骼和肌肉的限制,這個限制就是不讓你扭動的力,也就是肌肉的材質力,它反而成了外力或者阻力,而內力就是那個肌肉內所迸發出的“動力”。在做動作時,兩種力其實是對抗的。如果只表現扭動的力,而不表現對抗扭動的阻力,做出來的雕塑就像把腰扭斷一樣,失去真實感。
生命體的動力,都在嘗試拉高生命體的勢能,無論是抬胳膊還是扭腰,都會使生命體擁有更高的勢能,它使生命體有活力,趨向有目標的運動,趨向有選擇的改變。重力和骨骼肌肉的材質力使其趨向勢能最低、趨向隨波逐流、趨向靜止、趨向無變化。當我們完全不表現生命體自身的動力時,所做的雕塑,就跟一具尸體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松垮著、靜止著,被自身的重力所禁錮,擁有著最低的勢能。它所呈現的也將是結構最靜止的狀態,如完全沒有扭動的腰、完全放松下垂的胳膊、耷拉著的腦袋。而我們要表現生命,就必須要與這種勢能最低的狀態做對抗——對抗的目標主要是重力,也包括其他自然界的力,要想辦法讓它的動能充沛起來,拉高勢能。米開朗基羅的雕塑《被縛的奴隸》《哀悼基督》中,都能看到這種強有力的對抗。
這也是當我們照著書本上的解剖圖來做雕塑時,永遠也不可能做生動的原因。我們要做的永遠是肌肉的力量在對抗外力時的變化,而不是僅僅按照正確的排列規則,把肌肉分布到我們的雕塑上而已,只有那個變化才是最動人的,而無論怎么變,它總是被一種阻力所牽扯著。好的雕塑,就是要找到動力和阻力之間的平衡點。
參考文獻:
[1]赫伯特·里德,現代雕塑簡史[M].曾四凱,王仙錦,譯,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5.
[2]威廉·塔克,雕塑的語言[M].徐升,譯.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7.
作者單位:中國煤炭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