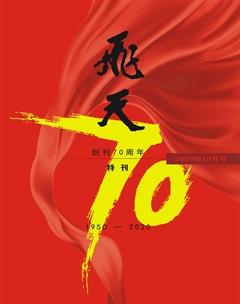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飛天》70不算老,亦不能稱老。
人活70古來稀。我這個年長《飛天》數(shù)歲的老編輯,確實老了,未癡呆,但大腦常常“斷電”,回憶往事時斷時續(xù)……碎片化……缺乏邏輯……時空倒錯……
丑話說在前頭——曰“70年的跳躍記憶”……
之一 甘肅有四張名片:敦煌·飛天,讀者·牛肉面
坊間傳言,甘肅有四張名片:敦煌·飛天,讀者·牛肉面。
初聞,愕然。思之,信然。深思,必然。
其一,《飛天》的前身《甘肅文學(xué)》是新中國創(chuàng)刊最早的文學(xué)刊物之一。在蘭州解放一周年之際,《甘肅文學(xué)》于1950年8月創(chuàng)刊,而且相當(dāng)隆重——刊名為茅盾墨寶,郭沫若、茅盾、周揚三巨頭題詞祝賀。其后易名《隴花》、《紅旗手》、《甘肅文藝》,直到1981年定名《飛天》……而甘肅文聯(lián)成立于1954年,甘肅作協(xié)則成立1958年。
那時,中學(xué)生都算文化人,何況聚集在《甘肅文學(xué)》周圍的那些舞文弄墨把文稿變成鉛字的人呢!在之后的歲月中,這些人紛紛成為各行各業(yè),特別是文學(xué)、文藝、新聞、出版等的領(lǐng)軍人物及骨干力量。
其二,《甘肅文藝》歷經(jīng)“文革劫難”,于1973年復(fù)刊,成為全國省級文學(xué)期刊復(fù)刊的報春鳥,為數(shù)年后甘肅文聯(lián)、作協(xié)的成立,集結(jié)了力量,儲備了人才。在文聯(lián)、作協(xié)及其他各協(xié)會的領(lǐng)導(dǎo)及骨干中,都有編輯部“支援”的人才。有的老同志戲稱《飛天》為甘肅文藝界的“黃埔軍校”。
其三,1980年代初,甘肅省文聯(lián)采取了強有力的改革:一是從《飛天》分孽而出,創(chuàng)建了全國第一家省級文藝?yán)碚摽铩懂?dāng)代文藝思潮》,實現(xiàn)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評論“鳥之雙翼”、“車之雙輪”并駕齊驅(qū),平衡發(fā)展的新格局。二是《甘肅文藝》改為《飛天》。“飛天”系敦煌莫高窟中最常見又非常漂亮的壁畫,是佛國里的“香音神”。每有節(jié)慶盛會,她就滿天飛舞、播放祥和的音樂、拋撒如雨的繽紛花瓣,增加和諧歡樂的氛圍。
改刊《飛天》,令刊物格局大變,使得“立足甘肅、面向全國的”的辦刊理念,變得清醒、明確而自覺。加之版面的革新、擴容,頁碼增至144頁,為省級期刊之最,每期可發(fā)兩個甚至三個中篇,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大型文學(xué)月刊。有了梧桐樹,自會招來金鳳凰。記憶所及,像陜西的陳忠實、賈平凹、路遙,寧夏的石舒清、季棟梁,乃至全國一些新銳作家、詩人,經(jīng)《飛天》這人間的“香音神”,將文學(xué)的繽紛花瓣——真、善、美撒向全國。
其四,自甘肅有期刊(不僅僅是文學(xué))評獎以來,在優(yōu)秀期刊或一級期刊的名單中,《飛天》從未缺席。由北京大學(xué)牽頭、國內(nèi)十多家權(quán)威科研機構(gòu)組織實施了全國中文核心期刊評選,《飛天》與《人民文學(xué)》、《收獲》、《當(dāng)代》等25家刊物,從全國448家文學(xué)刊物中脫穎而出,被評為文學(xué)作品類核心期刊(北京大學(xué)2008版)。這在《飛天》是首次,在西北五省區(qū)是唯一。
筆者曾著文,稱文學(xué)期刊為“三級火箭”——地巿為一級,省、直轄市為二級,囯刊、名刊、大刊為三級。通過“三級火箭”的通邊合作,把一個個作家詩人“衛(wèi)星”送上了《太空》。70年,在太空遨游的“衛(wèi)星”中,有多少是經(jīng)《飛天》發(fā)送上去的?難以計數(shù)。
甘肅的文學(xué)名片:舍《飛天》其誰!
之二 王蒙的理論文章《雪的聯(lián)想》、蔣子龍的處女作《新站長》及李瑛《詩五首》背后的故事
王蒙的一篇理論文章《雪的聯(lián)想》,在《甘肅文藝》保存了15年,終于在“文革”后的1979年7期的《甘肅文藝》刊出。
《雪的聯(lián)想》,寫于1963年夏天,寄給了《甘肅文藝》的謝昌余。謝昌余時任《甘肅文藝》評論組組長(后為《當(dāng)代文藝思潮》總負責(zé)人),1963年在西山八大處的“反修讀書會”與王蒙同住一室。編輯部是三級審稿制,所以謝昌余將稿子交給理論編輯余斌初審,然后自己簽注意見送主編楊文林終審。三審意見一致:好稿,可用。但楊文林又綴了一句:暫存,擇期刊出。
既是“好稿,可用”,為什么還要“暫存,擇期刊出”呢?
《甘肅文藝》1962年1期發(fā)表了大理論家陳涌的長篇論文《魯迅小說的思想力量和藝術(shù)力量》,第5期又發(fā)了他的長篇論文《政治與藝術(shù)關(guān)系的幾個問題》。斯時陳涌正下放蘭州的甘肅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教書,稿子都是特約的。1963年第1期,又刊發(fā)了公劉的政治抒情長詩《空氣》……于是有人告狀,說《甘肅文藝》專門發(fā)外地“摘帽右派”的作品,觀點、態(tài)度、方向、立場有問題,責(zé)令編輯部“整改”。此時再發(fā)“摘帽右派”王蒙的文章,無疑是“頂風(fēng)作案”,往槍口上撞。接蹱而至的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接著開始“文革”……擇機,這一擇就擇了16年。
將稿子保存16年的是細心負責(zé)而具有敬業(yè)精神的初審編輯余斌。
保存了16年得以完璧刊出的《雪的聯(lián)想》,令王蒙感觸頗深,見面常憶及此事。因為“西山讀書會”的同窗之情,也因為《雪的聯(lián)想》,王蒙與謝昌余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當(dāng)年,對風(fēng)云激蕩中的《當(dāng)代文藝思潮》,困難時也常出手相助。只要他來蘭州,必請接待方聯(lián)系謝昌余,請他來賓館聊天敘舊吃頓飯。此次《飛天》70年刊慶,請他題詞鼓勵,僅僅過了三天,他就寄來了“墨寶”——一筆一畫恭恭正正地寫道:
想念黃河,想念蘭州想念《飛天》,感恩《甘肅文藝》。作于一九六三年的《雪的聯(lián)想》經(jīng)《甘肅文藝》保存十六年,發(fā)表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撫今思昔,感念祝福——王蒙? ?2020夏。
在“王蒙”二字之后,蓋有鮮紅的方方正正的名章。
蔣子龍的短篇小說處女作《新站長》寫于1964年,據(jù)說投了數(shù)家刊物均遭退稿。盡管那時刊物的編輯大多盡職盡責(zé),不僅退稿,往往還附有退稿信,肯定成績、指出缺點,希望繼續(xù)努力。但是,屢投屢退畢竟不爽,蔣子龍有些灰心,認為自己不是寫小說當(dāng)作家的料。恰在此時,他當(dāng)兵(海軍)時的甘肅戰(zhàn)友給他“指點迷津”:我們省的《甘肅文藝》不排外,常常能讀到外省作者的好作品,不妨試試。蔣子龍將信將疑,抱著有棗無棗打一竿的態(tài)度將稿子投給了《甘肅文藝》,并對他的戰(zhàn)友說,如果《甘肅文藝》再退稿,這輩子我再也不寫小說了。不承想,數(shù)月后《新站長》竟在《甘肅文藝》1965年第6期登出來了。
斯時責(zé)編都不署名。不署名便不知道,越是不知道便越想知道……蔣子龍整整思念了28年。1993年夏,《飛天》與《中國作家》聯(lián)袂舉辦“金川·敦煌筆會”,王家達來賓館看蔣子龍,迷底終于揭曉。
此事,在筆會迅即傳開。無論是乘車還是在街上散步,每有穿海軍舊軍服的男子從旁經(jīng)過,楊匡滿就同蔣子龍開玩笑:“子龍,這是不是你那位‘文學(xué)向?qū)А拭C的戰(zhàn)友”?
筆會之后,蔣子龍寫了篇題為《尋找王家達》的文章,刊于《美文》某期。可惜我一直沒有讀到。蔣子龍在與王家達見面之后,仍以《尋找王家達》為題著文,向自己處女作的責(zé)編表達感謝、感恩,是如此地別出心裁!如此地富有創(chuàng)意!
如今又有27年歲月流逝……
人生啊,能有幾個27年?
人生啊,除了文學(xué),還有什么值得半個多世紀(jì)的記憶、思索與回味!
有文壇常青樹、歲月不老松之稱的軍旅老詩人李瑛,2006年7月17日給我寄了五首詩并附有簡短的信,陰差陽錯,歷時近三年我才收到。原因是2006年6月我就退居二線,當(dāng)了《飛天》的顧問,安居北京,不再上班。其間老詩人還寫過兩封信詢問,同樣原因,也未收到。直到2009年春,李小雨同我聯(lián)系,方知誤了大事。老詩人不會電腦,詩都是一筆一畫抄寫在稿紙上的,而且一旦詩成便不留底稿。老詩人的焦慮可想而知。我急忙專程趕往蘭州,果然兩大捆落滿灰塵的郵件在編輯部靜靜地等著我,其中就有老詩人的詩與信。
這五首詩是《青青的小樹林》、《聽雨》、《烈馬》、《一只阿拉伯單峰駝爬上了黃山》及《蒙娜麗莎的微笑》。首首都是難得一見的上乘之作。我急忙給老詩人寫信,謝罪而外還談了我閱讀這五首詩的心得體會。信中有這樣幾句:“好在您的詩并非‘速朽的應(yīng)景之作,永遠不會過時,猶如陳年老窖,塵封愈久,愈顯醇厚芬芳。正應(yīng)了那句老話:真正的文學(xué)是超越時空的。”然后我把信——題名為《您的詩有大愛存焉——陳德宏致老詩人李瑛的信》(復(fù)印件)及這五首詩,一并轉(zhuǎn)交給了我的繼任者馬青山,并于2009年7期《飛天》刊出。
李瑛是《飛天》數(shù)十年的老朋了,自1958年李季、聞捷主政《飛天》的前身《紅旗手》就發(fā)他的詩,從未間斷。之后他軍中的身份不斷在變,以至“顯赫”,但他始終以詩人的姿態(tài)與刊物的主編、副主編及一般詩歌編輯互通書信,談詩論藝,保持友誼與交往。20年前《飛天》的50周年刊慶,老詩人滿含深情地題寫了“文雄詩美看《飛天》”的贈言。2011年1月11日,“《李瑛詩文總集》暨李瑛同志詩歌座談會”在京隆重舉行。投桃報李,我準(zhǔn)備的發(fā)言稿的題目是——《〈飛天〉與李瑛:半個世紀(jì)五任主編的詩歌情緣》……
看稿、改稿、發(fā)稿、校稿、保存稿……在瑣碎平凡中守望著文學(xué),這就是文學(xué)刊物編輯。他們與作家詩人肩并肩、手牽手、心相連,為文學(xué)大目標(biāo),風(fēng)雨同舟,不離不棄,薪火相傳。
之三 “大學(xué)生詩苑”與《大學(xué)生詩歌家譜》
“大學(xué)生詩苑”是《飛天》專門為在校大學(xué)生、研究生開設(shè)的一個詩歌欄目,始于1981年2月,至明年2月整整40年。截止至2014年2月,33年來,共編輯出版了212期、發(fā)表了全國462所高校的2003名大學(xué)生詩人創(chuàng)作的詩歌4338首。《大學(xué)生詩歌家譜》(姜紅偉編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還有一個副名《飛天·大學(xué)生詩苑創(chuàng)辦史》(1981-2014)。姜紅偉自稱是“一部詩人輩出、佳作紛呈、影響深遠、意義重大、史無前例、載入史冊的《大學(xué)生詩苑》創(chuàng)辦史”!
放倒是一本書,立起是一座碑。
用煌煌40萬言一本書為文學(xué)期刊的詩歌欄目寫史,前無古人,后很難再有來者。
面對姜紅偉洋洋灑灑的《大學(xué)生詩歌家譜》,面對當(dāng)年從“大學(xué)生詩苑”起飛而今已是成就非凡的國刊主編,名校教授、博導(dǎo), 詩人、作家、評論家……對“大學(xué)生詩苑”感情真摯、激情澎拜的溢美贊揚,我這個從業(yè)數(shù)十年的老編輯,深感想象力的缺失及語言的潰乏。
序有三篇,分別是葉延濱《80年代詩歌史的“另類書寫者”》,于堅《歷史不能忘記》,潘洗塵《多元性詩歌寫作的源頭活水》。 這三篇序言可謂篇篇精彩,篇篇真摯感人,篇篇都有切身體會。篇幅所限,恕不征引。下面引述徐敬亞、邱華棟、蘇童的短評,以饗讀者:
80年代的中國天空,飄滿了一個個無家可歸的靈魂。
那是從無數(shù)焦灼的青春夜晚中冒出來的一縷縷詩歌青煙……那些內(nèi)含無邊能量的血淚詩篇,從來不缺少翅膀,它們只缺少土地。
在饑渴的年代,哪怕有一尺一寸的土地愿意收留那些流浪的精神囚徒,也必將被歷史放大般銘記為無邊的巴比倫花園——這就是“大學(xué)生詩苑”!一個后代人無法理解的偉大欄目。中國鉛字自發(fā)明以來,在它那里發(fā)出了最刻骨銘心的青春之光。
——徐敬亞。
我記得我發(fā)表在這個欄目的詩歌作品是《大雷雨》,那是一首類似惠特曼風(fēng)格的氣勢洶涌的詩篇。發(fā)表之后我拿到了雜志感到很激動。我覺得《飛天》雜志的這個欄目,非常大地推動了80年代大學(xué)生的詩歌創(chuàng)作……
——邱華棟。
我的大學(xué)時代是一個詩歌時代,很多大學(xué)生的文學(xué)飛天夢,恰如其分地從《飛天》雜志開始。這本雜志有一個著名欄目——大學(xué)生詩苑,那是我們最可親最可信的造夢平臺,我因此感念《飛天》雜志,并記住了張書紳這個詩歌編輯的名字……
——蘇 童。
事在人為。姜紅偉的《大學(xué)生詩歌家譜》從頭至尾都在告訴你《飛天》“大學(xué)生詩苑”的成功離不開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詩人、編輯家張書紳!他是這個欄目的的首倡者、奠基者、開拓者。在這本《大學(xué)生詩歌家譜》中,隨處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感受到他對詩歌由摯愛而執(zhí)著而神圣而敬畏而虔誠而付出而奉獻的高尚情懷。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吾等這些辦刊人,都是文學(xué)的事物主義者,只顧耕耘,不問收獲。在此,我要真誠地感謝姜紅偉!是他幫我們打撈出了比金子還要珍貴的系統(tǒng)而完整的記憶。
之四 筆會,研討會……
筆會、硏討會不是《飛天》的獨創(chuàng),卻是偏處西北經(jīng)濟欠發(fā)達地區(qū)的《飛天》平穩(wěn)致遠保持質(zhì)量持續(xù)前行的“秘訣”。特別是市場經(jīng)濟越來越多地介入了文學(xué)與刊物時,筆會就是最有效的“感情投資”,留住一些大家、名家的稿子有利于當(dāng)前;同時又吸收省內(nèi)那些已顯示了創(chuàng)作潛力的青年作家、詩人與會,與這些名家、大家朝夕相處,觀摩學(xué)習(xí)、切磋交流、言傳身教,促其提高,有利長遠。
A.創(chuàng)多項紀(jì)錄的“金川·飛天筆會”。
1983年9月15日-10月底,由《飛天》、《當(dāng)代文藝思潮》與金川公司聯(lián)合舉辦“金川·飛天筆會”。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湖南、湖北、安徽、山西、陜西等省市的青年作家譚談、賈平凹、梁曉聲、王振武、陸星兒、竹林、方方、黃蓓佳、程乃珊、史晶晶、周矢、王大鵬、譚元亨、李銳、陳煥新及省內(nèi)的青年作家浩嶺、匡文立、杏國等40余人與會。這次筆會創(chuàng)了多項全國紀(jì)錄:
第一,創(chuàng)了地域最廣、時間最長的記錄。與會者來自9省市,從9月15日蘭州報到開幕,到10月底金川結(jié)束,實打?qū)嵉?5天。
第二,創(chuàng)了全囯最隆重的記錄。甘肅的黨政軍三巨頭——省委書記李子奇、省長陳光毅、蘭州軍區(qū)政委肖華會見并參加了開班式。
第三,創(chuàng)了普及面最廣及創(chuàng)作與理論相結(jié)合的記錄。筆會期間,安排了三次作家與當(dāng)?shù)刈髡呒拔膶W(xué)發(fā)燒友見面座談會。形式自由、雙向交流,每次都有近300人參加。安排了兩次《當(dāng)代文藝思》編輯和與會作家的座談交流,就小說創(chuàng)作的理論與實踐、創(chuàng)作潮流的變化及發(fā)展趨勢,進行了探討。
當(dāng)然,比“創(chuàng)紀(jì)錄”更重要的是收獲。僅《飛天》陸續(xù)刊發(fā)的中篇就有:陸星兒《名人和她的女兒》、黃蓓佳《金發(fā)姑娘埃米》、方方《制片主任》、程乃珊《當(dāng)一個嬰兒誕生的時候》、譚談《你留下一支什么歌》;另外還有十幾個短篇,也陸續(xù)在《飛天》刊出,普遍獲得好評。
賈平凹也寫了個中篇《雞窩洼的人家》,編輯部上上下下都認為寫得好,定于某期頭條刊出。可是來了“狀況”——賈平凹來電話說,他想修改修改再發(fā)……數(shù)月之后,《雞窩洼的人家》在北京某大刊發(fā)出。
編輯部同仁當(dāng)然有意見。可我們的老主編楊文林很豁達、寬容。他說,辦刊物當(dāng)然希望留住好稿子,可作家有作家的盤算,總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國刊、大刊、名刊發(fā)表,影響大、稿酬高。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我們設(shè)身處地,換位思考,多理解吧……
《雞窩洼的人家》發(fā)表后好評如潮,不僅獲當(dāng)年(1984)的優(yōu)秀中篇獎,而且很快改編成電影《遠山》。電影《遠山》也好評如潮,順理成章,被評為1986年度的電影最高獎“金雞獎”。就在等待擇日對外公布頒獎之時,又枝節(jié)橫生,有人告狀,說《遠山》是“換老婆的故事”。“換老婆”在我國的傳統(tǒng)道德中跨越了“底線”,這還了得。于是“大領(lǐng)導(dǎo)”(王蒙語)要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拿出意見,然后處理。王蒙的策略是冷處理,放段時間,涼一涼再說。在情緒激動之時,理性很難湊效。過了段時間,王蒙給上面寫報告,先說《遠山》主題是積極的、是歌頌改革開放的,“換老婆”只是一種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形式,象征著 改革開放者的聯(lián)合及傳統(tǒng)保守者的重組……又說,評獎不是評“完美無缺”的作品,而是評那些具有時代精神及藝術(shù)特點突出的作品。有缺點的作品獲獎后,讀者、觀眾仍然可以批評……當(dāng)然,還有一些溫潤周全動人感人的說詞。王蒙的睿智之舉還在于,請副部長高占祥也在報告上簽名。高占祥在黨內(nèi)素有文化藝術(shù)的“行家里手”的美譽。 如此,更增加了報告的分量及說服力(詳見王蒙自傳《大塊文章·換老婆的風(fēng)波》——筆者)。于是“換老婆”風(fēng)波便告平息,《遠山》有驚無險,獲獎依舊。
賈平凹及《遠山》很幸運,撞上了小說家當(dāng)部長。其實幸運者豈止賈平凹!電影是綜合藝術(shù),一部電影的成功凝聚著許多電影從業(yè)人員的智慧與心血:編劇、導(dǎo)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攝影、美工、音樂……一部電影成功了,都有可能跟著摘取這些大獎。而這些獎項對許多人來說,傾其一生都可遇而不可求。
“換老婆的風(fēng)波”還告訴我們:文學(xué)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及欣賞是很復(fù)雜的精神審美現(xiàn)象,不能憑個人的興趣愛好,一言而興,一言而亡。
……
賈平凹是有故事的人。
而且是有福的人。
B.“豪華”且“高潮”迭起的筆會。
1993年夏,《飛天》與《中國作家》聯(lián)合舉辦了歷時半個月的“金川·敦煌”筆會。
“豪華”是指與會者的“量級”及影響,“高潮”是指筆會的活動內(nèi)容精彩紛呈。
先看與會者的陣容:唐達成、蔣子龍、陳丹晨、楊匡滿、高洪波、程樹榛、袁和平、李云鵬……還有兩位“臺灣同胞”——現(xiàn)代派畫家李錫奇(馬英九藝術(shù)顧問)及其太太女詩人古月。
筆會的第一次高潮出現(xiàn)在第二天晚上,公司安排作家與職工在會議中心“五彩城”聯(lián)歡。公司職工藝術(shù)團演出的歌舞堪稱專業(yè),都很精彩,語言類的小品、相聲都來自公司的生活現(xiàn)實,詼諧、幽默生動而接地氣……作家們也不示弱,紛紛主動獻藝——蔣子龍的山西民歌,舉座皆驚,特別是他把那“頭一次到你家,你呀不在,你媽媽打了我三鍋蓋”的歌詞,用山西方言,土得掉渣,演繹得繪聲繪色,堪稱原生態(tài);楊匡滿用漢俄“雙語”演唱的《三套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沉、婉轉(zhuǎn)、抒情;袁和平這位當(dāng)年在內(nèi)蒙古草原插隊的知青,以其寬厚的男中音演唱的內(nèi)蒙民歌,似馬頭琴的演奏,低沉、悠揚,把人帶進了“風(fēng)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牧場;張倩的花腔女高音、李錫奇的臺灣民謠、李云鵬的“花兒”也都廣受歡迎。
第二次的高潮是蔣子龍掀起來的。當(dāng)時廠礦企業(yè)的改革——黨政分離、政企分離正穩(wěn)步深入推進,金川公司的職工自然會把改革的現(xiàn)狀與蔣子龍的“改革文學(xué)”掛起鉤來予以討論。筆會安排的兩場對話研討會熱議這一問題,在礦山車間參觀也遇到這一問題。
一次,從閃速爐車間參觀出來,我們乘坐的大巴車周圍,已聚集了聞迅趕來的二三十名職工,有幾位拿著蔣子龍的書要求簽名;更多的是請教探討各種創(chuàng)作問題。有個青年提的問題很尖銳,他蔣對子龍說:“你的《喬廠長上任記》已經(jīng)過時了。現(xiàn)在的工業(yè)企業(yè)改革,比你作品反映的內(nèi)容、揭示的矛盾、處理的人際關(guān)系要復(fù)雜得多。你的喬廠長,放在今天的工廠里,恐怕一天也干不下去。”蔣子龍則笑著說:“我的那個喬廠長早就不干了,已經(jīng)離休了。”蔣子龍的幽默引起一片歡笑。
作家為難之時,理論家登場了。唐達成解釋說:“任何文學(xué)作品都是歷史的時代的產(chǎn)物,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更應(yīng)該具有歷史的積淀,體現(xiàn)著時代精神。社會發(fā)展了,時代進步了,會有新的作品產(chǎn)生,但并不能替代原有的成功的作品。真正優(yōu)秀的作品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喬廠長上任記》也一樣,不會過時,因為它已成為新時期的經(jīng)典。”
高洪波則給出了一句話的總結(jié):“子龍,金川公司職工對你作品的認知與賞識,比100篇評論家的文章更有價值、更有意義。”
第三次高潮,是唐達成的書法掀起的。
唐達成的書法已超越了“作家書法家”的層次,在全國已很有名氣,特別是在文藝界。對其書法,我的評價是“行云流水中蘊含著典雅大器,風(fēng)流倜儻里濃縮有人生滄桑”。達成含笑點頭,深以為然。因此,從抵達之日起不斷有人求字。日程安排得很滿,寫字只能放到中午及晚上,我怕影響達成休息,提出公司及市上各寫一張條子,不能超過十人。結(jié)果是你有政策,他有對策:一是條子上的名單嚴(yán)重超標(biāo)。二是前一張條子尚未寫完,后一張條子又遞上來了……我上前“擋駕”,而達成這位好好先生來者不拒,于是我也不再扮演得罪人的角色……事畢,我開玩笑說:“物以稀為貴。你的字寫得太多,僅在金川不下百幅,將來拍賣,拍不出高價。”達成則揉著酸脹的手腕,笑著說:“我本來就沒有打算靠賣字發(fā)財,怕什么!下來一趟不容易,大家喜歡我的字,也是一種厚愛與確認嘛!”
第四次——嚴(yán)格說來不是一次高潮,而是一段佳話。
臺灣的現(xiàn)代派畫家李錫奇及女詩人古月伉儷與會,雖只二人,卻豐富并擴大了這次筆會的內(nèi)涵及外延:由文學(xué)而文藝,由大陸而兩岸。古月原是囯民黨黨員,后因反對李登輝的“兩國論”憤而退黨。這是后話。此時尚是國民黨黨員的古月及無黨派大畫家李錫奇與我們相處半個月,其樂融融,令人感慨:國共第三次合作尚待時日,我們筆會國共合作的新局面,已經(jīng)形成。
……
類似的全國性的筆會、研討會還有很多,記憶所及——
1995年“全國文學(xué)期刊主編研討會”,2004年9月“東部作家西部行”筆會,2006年6月“兩岸文藝會隴原”筆會……
之五 《飛天》的詩歌長項與甘肅的詩歌大省強省
進入21世紀(jì),不斷有人說甘肅是詩歌大省、強省,而且這“大”和“強”與《飛天》的長項詩歌有關(guān)。說這話的既有本省的文友,也有外省的文友。
聽到與自己工作有關(guān)的贊揚,還是有些激動與竊喜,但不敢張揚。一是缺乏自信。二是為人低調(diào),生怕說大話,放空炮,落個吹牛的惡名。直到2006年我退居二線,安居京東燕郊,與詩歌界的朋友交往多了,像雷抒雁、楊匡滿、韓作榮、張同吾、李小雨等對詩歌的現(xiàn)狀及發(fā)展了如指掌的人,也持此觀點,方使我對甘肅詩歌發(fā)展的源流進行反省與深思。
首先,詩歌一直是甘肅文學(xué)中的先鋒部隊。
解放初,因歷史及現(xiàn)實的種種原因,甘肅的文學(xué)整體而言,處于落后狀態(tài)。上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甘肅文藝界提出的口號是“走出甘肅”,而走出甘肅的目標(biāo)既包括國刊、大刊、名刊,也包括像《延河》這樣的兄弟省市的刊物。而率先“走出甘肅”的正是詩歌。高平的敘事長詩《大雪紛飛》在《人民文學(xué)》1956年5-6期合刊刊出,反響強烈。張賢亮(斯時張賢亮的工作單位是甘肅省政府政治干校)的長詩《大風(fēng)歌》在1957年《延河》某期刊出,同樣引起熱議。何來的《烽火臺抒情》1962年《詩刊》某期發(fā)表——具體的期數(shù)忘了,但當(dāng)時的轟動盛況仍歷歷在目——該期詩刊的頭題是李季的訪越詩章《還劍湖》,二題便是何來的《烽火臺抒情》。詩刊專門派人來蘭州開座談會,而該同志發(fā)言的第一句話竟是“何來先生來了沒有”?而斯時的何來尚是甘肅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的學(xué)生,年齡只有23歲。在此后的二三年,《烽火臺抒情》成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春節(jié)賀歲詩朗誦中少有的保留。
其次,有一支迅速成長的少數(shù)民族詩人隊伍。汪玉良(東鄉(xiāng)族)、伊丹才讓(藏族)、趙之洵(回族)、丹正貢布(藏族)是他們的優(yōu)秀代表。他們起步于50年代末,成長于60年代,直至80-90年代仍馳騁于詩壇,都曾獲過少數(shù)民族優(yōu)秀詩歌獎。
再次,甘肅詩歌真正意義上的發(fā)展,應(yīng)追溯到1958年。這一年李季、聞捷二位大詩人來甘肅,成立了甘肅作家協(xié)會,分別擔(dān)任主席、副主席,同時擔(dān)任《飛天》的前身《紅旗手》的主編、副主編。大詩人辦刊,自然注重詩歌的刊發(fā)與發(fā)展,而繼任者楊文林、李云鵬,也是詩人。與此同時,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頗具實力的詩人編輯還有好多,可以開岀長長的名單。因此,《飛天》注重詩歌的傳統(tǒng),得到了持續(xù)不斷的繼承與發(fā)展。
李季、聞捷惠風(fēng)流韻所致,是刊物為詩歌提供了更多的篇幅,開設(shè)了更多的園地,吸引了更多的老詩人、大詩人的杠鼎之作,刊出了更多的詩論詩評,舉辦了更多的全國詩歌大獎賽,辦了更多的詩歌、散文年終專號,舉辦了更多的各類型、各種規(guī)模的詩會、詩歌創(chuàng)作研討會,以及國刊、大刊、名刊詩歌編輯座談會。每有這樣的機會,編輯部總是招集盡可能多的全省詩歌作者、特別是青年作者與會,白天聽大會發(fā)言、小組討論,晚上三五成群,請上全國的名家,到黃河邊泡上“三泡臺”,提上兩捆啤酒,邊欣賞“澄江靜如練”的黃河夜景,邊談詩論藝:聽方家高論,釋胸中疑惑……那愜意,那滿足,那詩情、詩美的陶冶,非一般課堂所能比擬。對此,我頗為自豪地稱之為:《飛天》氣派!《飛天》精神!《飛天》胸懷!《飛天》境界!
半個世紀(jì)前,甘肅鼓勵自己青澀而靦腆的詩人走出甘肅,而今隨意打開全囯的囯刊、大刊、名刊,不意間都會碰到甘肅的詩人及其詩作。《詩刊》、《星星》等專門的詩歌刊物,有時不惜版面,讓甘肅的青年詩人,呈方陣式展現(xiàn)。
老鄉(xiāng)和娜夜同一年雙獲“魯迅文學(xué)獎”,既是詩歌大省、詩歌強省的必然結(jié)果,也是詩歌大省、詩歌強省的確證!
之六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北宋 晏殊)。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北宋 柳詠)。
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南宋 辛棄疾)。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征引這三位詞人的話,闡釋人生的三個階段,三個層次, 三種境界:深刻雋永、睿智醒世、妙不可言。
70歲的《飛天》,何嘗不是如此!
責(zé)任編輯 閻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