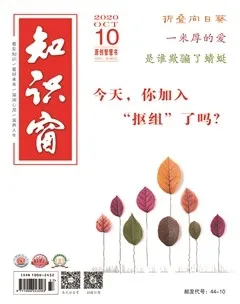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
劉雨欣
聲音與顏色,有時候比劇情與對白更有記憶度。
我喜歡《末代皇帝》,尤其對里面蒼涼悠揚的配樂、昏黃幽暗的色調(diào)印象深刻。我在某年初冬來到紫禁城,印象最深的是末日黃昏感的色調(diào)、寒鴉棲復驚的啼叫。
俯瞰故宮是完全不同的體驗,幸得朋友引路,帶我走上角樓,沿著城墻邊行走,縱使我已來過故宮兩三次,仍被這新的視角所打動。角樓之上人煙稀少,唯有北風寒。這是一種絕妙的過濾,讓我們和歷史又少了一層隔膜。正是因為嘈雜都被過濾了,我得以給此情此景賦予自己的音樂。我在高高的城墻上,猶如浮在歷史與當下的半空中。
鴿子在紅墻邊以神秘的軌跡盤旋,烏鴉嘎嘎的嘶叫回聲愴然,這是動物秘密的儀式感。“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寒鴉一叫,萬點愁如海,紛紛涌了上來。平白有一種失去感,仿佛我也失落了故園,寒枝不可棲,高樓休獨倚。
《末代皇帝》的配樂《Where is Armo》是我隨時隨地都能哼出的曲調(diào),曲調(diào)本來莊重富麗,但是二胡讓調(diào)子平白一轉(zhuǎn),莊重變成了沉重,富麗變成了靡靡。
去故宮的日子,北京的空氣中有些霾,使黃昏更添滯重感,有朦朧的光暈。太陽都落了塵土,斂了光華,仿佛圓月。但妙處在于,霾使得近處的景物都像遠隔天邊,迷蒙感拉長了空間,模糊了地平線,像被熱氣蒸烤得模糊的沙漠。
柿子樹是初冬故宮最令我感到驚喜的存在。彼時臨近日落,故宮的琉璃瓦都泛著橘黃,零落的一兩棵柿子樹掛著不多的果子,但圓潤鮮紅得很。如此生機,與疏落蕭索的枯枝,形成了生與死的鮮明對比,使明媚的更加鮮活,暗沉的更加衰亡。
站在角樓上可以看見許多尚未向游客開放的宮殿,肅殺寂寞。有些宮殿還覆蓋著薄薄的殘雪,像遲暮美人的面紗。
塵封的門,巍巍的墻,密實的瓦,是一種阻隔與拒絕。
“紗窗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劉方平的《春怨》寫的是漢武帝與陳阿嬌之間的故事。暮色作底色,各個意象都籠著一層郁氣,仿佛聽得見風聲在回廊的回響。
張愛玲說:“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故宮最配得上“蒼涼”二字,這里的故事或無疾而終,或戛然而止,一地逗號與省略號,唯獨沒有句號。
故宮復雜的建筑結構,天生適合展現(xiàn)不同建筑立面的交錯、互動、矛盾。就像《末代皇帝》中許多重帷深院的鏡頭,皇帝走過一扇扇門,錯過一個個人。
皇城建筑氣勢無限,善用廣闊空間、嚴謹結構、大立面形成莊嚴感與壓迫感。人物只是從屬,建筑方是權力。人物早已是“渺滄海之一粟”,建筑仍是“鳳去臺空江自流”。
我喜歡故宮,尤其喜歡它名字里的“故”字,它讓我聯(lián)想到故鄉(xiāng)的“故”,平添了一分鄉(xiāng)愁。那是失落的、離別的、憂郁的一個背影。
林語堂在《說北平》中寫道:“北平又像是一株古木老樹,根脈深入地中,藉之得暢茂。在它的樹蔭下與枝軀上寄生的,有數(shù)百萬的昆蟲。這些昆蟲如何能知道樹的大小,如何生長根,在地下有多深,還有在別枝上寄生的是什么昆蟲?”
在北京,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能覓得容身之地,每個人身上都背著一部關于北京獨特的編年史。如今的出租車司機和曾經(jīng)的黃包車車夫一樣,侃侃而談的嘴里能蹦出大千世界的千奇百怪,偏生什么樣的煩惱苦楚,經(jīng)他們一說,都像是幽默故事。同樣,堂倌、書生、商人、老人,各類人物都在皮膚之下,藏著獨特甚至矛盾的重重故事。
然而,如今的東城區(qū)、西城區(qū),幾乎成了完全的旅游景區(qū)與高層辦公區(qū),生活氣息層層剝蝕。北平從前嘈雜熱鬧卻又風情古樸的光景,確是回不去了。
幸得仍有故宮這一“故”字存在,讓民族的鄉(xiāng)愁有了依托,讓回望的目光有了落點,讓繁華競逐、悲恨相續(xù)、謾嗟榮辱的故事有了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