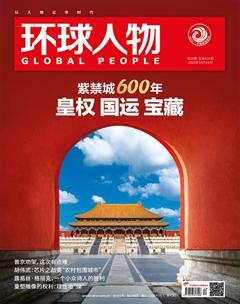西安鼓樂,“打”出來的秦韻
春田

能表演世界級文化遺產(chǎn)的不一定是大師,也可以是樸實的農(nóng)民。不少西安鼓樂節(jié)目開演前,面色黝黑發(fā)紅的農(nóng)民朋友徐徐走上臺,稍顯羞澀,但一拿起鼓槌,立即起范兒,鼓聲一出,伴著悠揚笙簫聲,鼓點一層層鋪開……
西安鼓樂是世界級、國家級文化遺產(chǎn),敲擊鼓、鑼、鐃鈸、梆子、鈴,吹奏笛、笙、管等,進行組合表演。西安的許多地方就有鼓樂的痕跡,有些村莊甚至從18世紀就有鑼鼓制造和加工產(chǎn)業(yè),到20世紀末達到頂峰,小作坊遍布農(nóng)村,一度出現(xiàn)“女人會燒火,男人精鑄銅,老人善做鼓,青年跑經(jīng)營”的場景,也留下了多個分支,比如集賢鼓樂。
翻越秦嶺北麓,從西安市周至縣的縣城驅車25公里就是集賢鎮(zhèn)。“我們的樂社就是泥腿子樂社。我的家鄉(xiāng)一直是農(nóng)村,鼓社的傳承者代代靠農(nóng)業(yè)生活,農(nóng)忙時拿鋤頭務農(nóng),農(nóng)閑時就拿起樂器。傳承鼓樂的好多是咱們泥腿子農(nóng)民!”田中禾77歲了,是西安鼓樂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也是西村樂社第四十六代傳人,說話中氣十足,這股精氣神兒正是幾十年的打鼓生涯帶給他的。
田中禾是集賢鎮(zhèn)的一名退休教師,上世紀40年代生于周至縣南集賢西村的一個鼓樂世家。爺爺是樂社中的老把式,擅長打鑼,父親精通吹管子和打鼓拍。小時候,父親把他抱進樂社,老師傅們圍著大炕,你一言我一語,有人說了孔融讓梨的故事,大家希望孩子品行好,便給他起了個小名,田讓梨。
平日,小田常盯著大小不一的鼓,時不時打一打。有一次,當?shù)卣垬飞缛パ莩觯镏泻桃哺蠄觯蛄恕袄鲜罄前省惫摹N鞔鍢飞绲谒氖宕鷤魅藦堄忻饕豢矗瑢λ赣H說:“讓娃跟我學打鼓,我看這個苗子能打鼓。”就這樣,田中禾便開始打鼓。練鼓之人,哪里都能“打”。田中禾在自家的墻上、炕邊練鼓點,走路時還把肚皮當鼓面,拿雙手在肚子上拍打,練就了一身本領。那時候,西安有四五十家樂社,每到演出季,大街小巷,笙管齊奏,鼓樂齊鳴,人們總能見到田中禾的身影。

左上圖:西安鼓樂是世界級、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圖為其中一種樂器。左下圖:20世紀80年代,鼓樂藝人在樂社演出。2018年,田中禾正在掌鼓,表演西安鼓樂。右上圖:西安鼓樂使用的工尺譜。右下圖:傳承千年的老樂譜。中下圖:西安鼓樂的表演者大多是平民百姓,平日也常“ 斗樂”比賽,不亦樂乎。
“文革”期間,鼓樂被當作“四舊”,樂社便改編為宣傳隊,許多鼓樂藝人被派去唱樣板戲。田中禾也暫別鼓樂,在山里當老師,但常練習技藝,還對樂曲進行分類、整理、記錄,以防失傳。這一晃,20多年過去了,改革開放后,民間藝術再度百花齊放。1992年,西村樂社東山再起,招了一批學員。8年后,田中禾擔任鼓樂社社長,打破鼓樂傳男不傳女的舊傳統(tǒng),招收了17名女學員,當?shù)貥访远己八肮纳瘛薄?/p>
西安鼓樂雖為世界級文化遺產(chǎn),但不那么高高在上,表演者均為平民,有農(nóng)民、退休工人、學生……這種與民同樂的文化形式從何而來?你翻開西安鼓樂的曲譜就知道了,它有著濃厚的唐宋遺風。
西安鼓樂的樂譜主要是古代樂譜,沿用唐宋時期的記寫方式,比如工尺譜。這是中國最早采用漢字的曲譜形式之一,“上、尺、工”……分別表示“do、re、mi”等,有時會在漢字下方畫斜線等來表現(xiàn)音高。
“安史之亂”之時,唐玄宗倉皇西逃成都,皇家樂隊中有些人逃到了周至縣的南集賢村避難,長達三年多,得到當?shù)匕傩盏恼疹櫋穾焸優(yōu)榱嘶貓螽數(shù)匕傩眨瑢m廷音樂技藝傳授給他們,鼓樂開始相傳。當時,村里有條河道,東半部稱東瀛村,西半部為西社村,村里長輩就讓兩村的樂社“斗樂”。每年正月,樂隊分列小河兩邊,隔岸輪流吹奏樂曲,從夜晚“斗”到清晨。有時候還舉辦接龍比賽,如果哪家樂社接不上,就認輸,在“觀戰(zhàn)”百姓的噓聲中退場,回去苦練一年,來年再“斗”。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這是鼓樂師傅的“社魂”。你瞧,農(nóng)民、教師、退休工人、學生,一擼袖子,鼓棒落下,便是一曲西北大地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