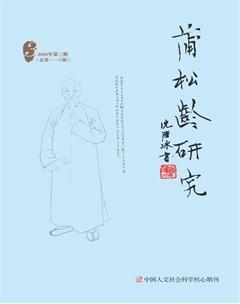《聊齋志異》第一人稱敘事論析
摘要:《聊齋志異》使用第一人稱敘事的作品有4篇,分別是《偷桃》《地震》《上仙》和《絳妃》。在使用第一人稱敘事時,蒲松齡不僅能較為恰當地守住了“余”的感受疆域,具有比較嚴謹的“第一人稱”意識,而且善于把握好介入故事的分寸,在控制“余”與故事的距離上表現得收放自如。
關鍵詞:敘事情境;第一敘事人稱;聊齋志異;敘事介入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識碼:A
在敘事學領域,敘事人稱屬于敘事視角的研究范疇,敘事理論家通過分析敘事人稱來探明敘述者以“誰”的身份或名義敘述故事,敘述者與故事的距離,以及敘事人稱帶來的可靠性等問題。小說使用的敘事人稱無非有三種,分別為第三人稱、第二人稱和第一人稱。中國古代小說尤其是文言小說,真正使用第一敘事人稱的比較罕見,許多作品中的第一人稱實際上只是故事的記錄者而非敘述者。那些真正使用了第一敘事人稱的作品中的“予?蛐余?蛐吾”,有的是故事的旁觀者,僅起到穿線引線的作用,如唐代王度的《古鏡記》中的“度”(作者王度的自稱);有的是主要人物,具有很高的故事參與度,如唐代張鷟的《游仙窟》中的“余”;有的是故事來源的提供者,如白行簡《李娃傳》“公佐命予為傳”中的第一人稱“予”;有的是敘述者與聽眾或讀者對話時所用的自稱,如宋明時期某些話本、擬話本中的“我”。《聊齋志異》中有4篇作品使用了第一敘事人稱,分別是《偷桃》《地震》《上仙》和《絳妃》,實屬難得。這4篇作品故事結構層面不同,敘述者“余”的角色身份各異,讀來別有意趣。
一
從我國古代小說觀念流變歷程看,宋代以前崇實抑虛的小說觀占據優勢地位。魯迅先生認為唐人“始有意為小說” [1]70,胡應麟稱唐人“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 [2]371,照此則唐代小說家的虛構觀念應該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唐傳奇作者常常發出“信而有徵,可為實錄” [3]287“搜求遺逸,傳于必信” [4]75之類的宣言,可見創作上虛構技法的進步與作家小說觀念的革新并不同步。自宋代始,作家虛構意識日趨自覺,小說虛實觀由重實斥虛向虛實并重,甚至向淡化實錄、推崇虛構演進。慶元二年(1196)三月,洪邁在《夷堅支丁序》聲明,小說可以據實而錄,傳載實事,也可以記錄怪奇虛無之事,所謂“稗官小說家之言,不必信固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5]98。同年七月,洪邁在《夷堅支戊序》指出,古今性情有相似,“記夢而有驗之事,不必為實有”,但可以“發好事君子捧腹” [6]100,言下之意是虛幻故事也具有娛情樂意的功能。古代小說紀實觀念的“實”有兩個基本內涵:一個是從故事來源看,“實”意味著如實記錄或轉抄;另一個是從故事內容看,“實”意味著人物在生活中實有、事件真實地發生過。作家使用第一人稱十分謹慎,因為一旦作品中出現“予”“余”之類的第一人稱,則意味著敘述的事件(故事)必須為作者所耳聞目睹,否則就會受到質疑乃至批評。蒲松齡使用第一人稱創作時,也將故事中的敘述者“余”預設為現實生活中的自己。
《偷桃》講述了童時的“余”觀看了一場驚心動魄、令人嘆絕的變戲法的故事。當時街上游人如堵,術人自稱“能顛倒生物” ① 。這一驚人之語給術人招來了麻煩,官員命他表演摘桃技藝,然而時值初春,哪有鮮桃可取?他的兒子以業已應允為由,請父親不要推辭。術人無奈之下提出了破解難題之法,“惟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卸,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于是,一場父子二人相互推波助瀾、懸念迭生的雜藝表演就在“余”的眼前展開了:為了盜取仙桃,術人拋出了一條繩子,“繩即懸立空際”,讓兒子緣繩登上萬仞高天;兒子面有難色,擔心繩子“中道斷絕,骸骨何存”;在父親“為兒娶一美婦”的誘惑下,兒子握著繩子盤旋而上,漸漸登入云霄;就在仙桃從天而降、眾人驚喜之際,令人驚恐的一幕出現了,繩子突然斷落掉到地上,兒子慘被肢解,頭顱、四肢紛紛從天而墜,術人悲痛不已。故事結局出人意料,在術人得到賞錢后,兒子從盛裝尸體的箱子中站了起來,原來這是一場有驚無險的幻術表演。
《偷桃》是回憶過去的事情,在某程度上潛藏著虛構性。《地震》《上仙》以近于據實記錄的方式呈現事件與人物,具有較強的真實感,但無論故事情節、場景描繪還是敘事策略都比《偷桃》遜色許多。《地震》講述了蒲松齡在濟南遭逢地震時的見聞感受,這場地震發生在康熙七年(1668),史籍有記載。該篇前半部分主要是場景描繪,再現了眾人慌亂恐懼、房屋受震坍圮、滿城鴨鳴犬吠等情形,還插入了作者在震后得知的其他地方遭災的情況;后半部分敘述的故事與地震見聞沒有直接關聯,但婦人在情急著慌中無暇顧及衣著的情狀與地震中的人們有相似之處,蒲松齡就旁逸斜出,以令人莞爾一笑的筆墨結束全篇。《上仙》講述的故事發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也是蒲松齡親身經歷之事。當時,蒲松齡與朋友高季文同在濟南,高季文忽然生病,聽人說南郭梁氏家有善于醫術的狐仙,于是與友人一同前去求醫問藥。這篇作品的核心事件是求仙問藥,內容以場景描繪和對話描寫為主。敘述者“余”除了在開頭和結尾交代了自己的行跡,把大量筆墨用于記錄他人的言行。至于求來的仙藥功效如何,“余”未作交代,僅以“過宿,季文少愈。余與振美治裝光歸,遂不暇造訪矣”結束了全篇。
上述三篇作品都敘述了“余”看到的現象和經歷的事件,故事真實性容易獲得讀者的認同,《絳妃》帶給讀者的感受與它們有微妙差異。《絳妃》敘述的“余”的一場夢,或許在蒲松齡的生活中真實發生過,但直接經驗使人們認識到夢境發生的一切都是虛幻的,因此無論作者將夢境之事敘述得多么真實可感,它也只能用來隱喻現實生活或作為現實生活的陪襯物而存在。《絳妃》中,“余”剛進入了夢境,就有兩位艷麗女郎受絳妃委派前來召“余”覲見。“余”在恍惚驚愕中來到一座宮殿,受到了花神絳妃的禮遇。原來絳妃因一向受“封家婢子”(風神)的摧殘,想請“余”代為撰寫討伐檄文,向封氏宣戰。《絳妃》的故事不出奇,無非講述了懷才不遇的文士得到仙人垂青,施展生花妙筆獲得交口稱贊的夢中經歷。此類故事自古有之,唐代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描繪的仙人紛紛前來迎接“我”的場景,瞿佑《剪燈新話·水宮慶會錄》中余善文受邀至龍宮撰寫上梁文的故事,宋代劉斧《青瑣高議·溫泉記》中少負英氣的張俞在蓬萊第一宮得到楊太真垂青的故事,都折射了封建文士感慨遭際而孤芳自賞的心境,以及渴望得到激賞的迫切心情。《絳妃》中占據篇幅優勢的不是“余”的夢境,而是“余”夢覺之后補足的檄文。該檄文辭藻豐贍,典故聯翩,氣勢飛揚,情懷激越,透射出一股恃才使氣、借題發揮的意緒。
二
“在清代中葉之前,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僅僅在文言小說中偶爾有之;自清中葉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某些白話小說開始運用第一人稱視角” [7]84。蒲松齡生活在清代早期,他的第一人稱敘事作品在《聊齋志異》近五百篇作品中所占比例很小,意義卻不可小覷。這4篇作品表明,蒲松齡使用第一人稱敘事是“有意識的美學抉擇的結果,而不是直抒胸臆、表白心曲的自傳的標記” [8]174。米克·巴爾曾指出,敘述者的“第一人稱”(無論是隱含的還是顯性的)與文本中使用的以“我”“自己”為標志的第一人稱是有區別的,前者屬于“一個可以看作是處在他所敘述的故事‘上面或高于這個故事的敘述者,和他所屬的那個敘述層次一樣,是‘超故事的”,而后者屬于故事層面里的人物 [9]170。其實,米克·巴爾所說的這兩種“第一人稱”在某些作品里是合而為一的,當作者將敘述者角色賦予故事中的人物時,人物所稱的“我”自然就成了“超故事”層面上的敘述者“我”。從這個角度考察《聊齋志異》中使用第一人稱敘事的作品,我們會發現超故事層的“余”與故事層的“余”有時是相合的,有時是分離的。
《上仙》《地震》中的“余”不是聚焦對象,而是事件的觀察者(聚焦者)和敘述者。《上仙》中的“余”作為敘述者貫穿故事的始終,從“與高季文赴稷下”到高季文生病,從與高季文一道去求仙問藥到與高振美一同返回家鄉,“余”一直在場。《地震》前半部分描述地震到來時發生的一切的,是地震現場中的“余”;而后半部分講述婦人從狼嘴里救下兒子故事的,是與地震現場中的“余”有差異的另一個敘述者“余”。這兩個“余”都講述了人在慌亂之中某些舉動的滑稽可笑之處,在故事中流露的情感傾向具有一致性。這兩篇作品中的敘述者“余”的共性是:均身處同一故事層之中,沒有具體的話語行為(對話或獨白),并且也很少發出敘事聲音。
《絳妃》的情況相對復雜一些,其敘事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講述了發生在作品虛擬世界中的故事,可以稱為一級敘事層;另一個層面講述了發生在虛擬世界中的夢境中的故事,我們稱為次級敘事層。于是,作品存在兩個有明顯差異的敘述者“余”:一個是在畢際友家坐館的“余”,授課之余與畢際友暢游花園,屬于一級敘事層;另一個是夢中的“余”,為絳妃所賞識而揮灑翰墨,屬于次級敘事層。前一個“余”因為作品中有“癸亥歲,余館于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的陳述,極易使讀者聯想到現實生活中的作者,這一個“余”實際上就是作者自稱。后一個“余”是虛幻空間里的“余”,是真實的“余”(作者)的敘述對象,又是夢境故事的敘述者。后者的生存境況顯然比前者幸運得多:前者是科舉路上困頓不堪的窮經書生,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卻難逢伯樂;后者文名震動仙界,受到花神絳妃的賞識和眷顧。夢中“余”的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心理內涵、文化信息,讀者能從中讀出“余”身上疊加的多重鏡像:有唐李肇《唐國史補》和明馮夢龍《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中的賦詩作文時享受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待遇的李白的影子,有《夢游天姥吟留別》中受到眾仙迎迓的李白的影子;還有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中“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并受都督閆公嘆賞的王勃的影子。這一切滲透了失意文人蒲松齡孤芳自賞、不甘落拓的狷介性格,折射出傳統文人著書立說的微妙心態——在展示才華的同時傾瀉一泓幽微深隱的情志 [10]309。
敘事人稱結構最富特色的是《偷桃》。《偷桃》里的“童時赴郡試”“時方稚”等話語表明,核心故事的敘述者是年少之時的“余”。首先,“余”看到了四位身穿赤服的官員,因年少無知,無法從服色上辨認其官階官職,所以“不解為何官”。其次,“余”作為旁觀者只能看到眾人擁堵、術人表演,聽到人聲的喧雜、術人與官員的對話,無從了解術人與其兒子的內心世界。再次,“余”年少不辨玄奧,只是如實描繪眼前發生的一切,將術人高妙的技藝真實地呈現給讀者。最后,“余”無法揭穿這一戲法的奧妙所在,只能保持旁觀者的敘述口吻。但是,我們不能據此就下斷語,認為《偷桃》只有一個敘述者——“童時赴郡試”的“余”,因為該篇中人物的世界與敘述者的世界并不完全統一,講述故事的“自我”與經歷“故事”的自我(西方敘事理論所謂“敘述自我”與“經驗自我”)并非一體。當身處某一年齡階段時,我們在話語交流中直接使用“我”指稱自己;一旦用某一年齡段的名詞來限定“我”,就意味著我們已經走出這一年齡段,或者從幻想的角度預設這一年齡段。正如史蒂文·康納所說,“在我們處于生活之中時,我們只能部分地認識它;當我們試圖認識生活時,我們其實已經不再處于那段生活的經歷之中了” [11]3。文中有“童時赴郡試”“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等話語,顯然不是過去的“余”對自我的描述,這說明在童時的“余”之上,還有一個視“余”為“童時”“方稚”的敘述者“我”。這段文本潛存兩種不同的敘事眼光:“一是敘述者‘我從現在的角度追憶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憶的‘我過去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 [12]201前者指稱幼年時“余”,站在當下追憶童年“余”經歷的往事;后者是童年時的“余”,講述了親眼所見的一場變戲法。一級敘事層中的“余”僅僅是個“敘述自我”,因為沒有講述自己當下經歷,故而沒有形成相應的“經驗自我”;次級敘事層“余”既是核心故事的敘述者(“敘述自我”),又是感受者(“經驗自我”)。從“敘述自我”與“經驗自我”的關系來說,《上仙》《地震》中的“敘述自我”與“經驗自我”是重合的,均處于故事邊緣,而《偷桃》中“講述自我”不僅與“經驗自我”分離,且“經驗自我”位于故事核心。
三
第一人稱敘事帶有“我看”“我聽”“我想”的標簽,其蘊含的生動感、逼真感容易幫助讀者建構起故事世界的情境表象,也容易喚醒讀者對相似經歷與體驗的回憶。有些讀者甚至相信,虛構作品中的“我”就是現實中的作者,并把對“我”思想道德的評價移植到作者身上。“以第一人稱講述故事的方法是一種精巧的、比其他方式有影響的方法……第一人稱敘述法的目的和效果是富于變化的。” [13]217要想臻于“精巧”“富于變化”的敘事境界,作家使用第一人稱敘事就要恰當處理兩個問題:一是要嚴守“我”感受所及的范圍,避免敘述越界引發讀者對敘述可靠性的質疑;二是要調控好“我”基于故事距離的敘述立場和聲音基調,避免聲音越位擾亂文本主題和敘事意圖。考察蒲松齡筆下第一人稱敘事的藝術效果,也可以從這兩個層面入手。
首先,蒲松齡較為恰當地守住了“余”的感受疆域,具有比較嚴謹而自覺的“第一人稱”意識。第一人稱敘事從“我”的視角出發觀察和感受世界,講述故事,除非借助他人轉述或跨越視界,否則“我”就不能“直接表現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內心世界” [14]199。《地震》《上仙》的敘述者“余”位于故事的邊緣,這一位置決定了“余”只能觀察、記錄和轉述身邊發生的外顯的一切,不能走進其他人物的內心加以描寫和展現。《地震》在開篇簡要交代了“余”地震來臨前夕的情形,“余適客稷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其后則由“忽聞”“見”為引領語描述“余”當時看到的現象、聽見的聲音。對于“余”沒有親歷親聞的事件,如“井傾仄”“樓臺南北易向”“棲霞山裂”和“沂水陷穴”等奇變,作品使用了“后聞”作為補敘標識語,確保敘事不越界。《地震》后半部分講述的事件,可以認為省略了“余聽說”“余知道”等引領語,依然是“余”講述的故事。《上仙》對“余”功能的定位與《地震》的差異在于保持敘述邊界的手段不同。《上仙》敘述核心事件時采用了直接陳述見聞的方式,沒有使用“余見”“余聽”之類的引導語。“余”的“眼光”聚焦在周圍的人和事上,“腳步”追隨著其他人物的行蹤,邊觀察邊記述,這種寫法具有鮮明的紀實色彩。對那些“余”無法眼見只能耳聽的事件,作者很注意用詞的分寸,如“余”沒有進入內室,只能聽到內室傳來的聲音,“細細繁響,如蝙蝠飛鳴。方凝聽間,忽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這里的“如”“若”表明“余”是根據聲響做出了推測。《絳妃》中無論一級敘事層的“余”還是次級敘事層的“余”,都只傳遞給讀者“余”能見到的事情和聽到的聲音,至于其他人物的態度、情感等,則通過敘述和描繪讓讀者自行體會。《絳妃》除了僅用“惶悚”“惶然”“文思泉涌”展現“余”的心理活動、對他人只敘述其行動之外,還有一個細節可以表明蒲松齡使用第一人稱敘事的心思之細密:“余”在絳妃自言身份之前,只知道對方被稱為“絳妃”,對其真實身份毫不知情,小說以“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描繪“余”眼中所見的絳妃,“狀若”一詞非常切合當時的情境。《偷桃》對敘事人稱功能的設定和處理得最為復雜和巧妙:一級敘事層的“余”已經長大成人,走出了“童時”這一年齡階段,而次級敘事層“余”是一級敘事層的“余”以往人生歷程中的另一個自我,因此后者不僅可以描述當下的心理活動,而且還可以展示前者的心理活動,且這兩種心理活動可以是異質的,也可以是同質的。在該篇中,一級敘事層的“余”有能力從當年的“偷桃”表演聯想到白蓮教,進一步強化術人技藝的神秘感,次級敘事層的“余”則直接感受“偷桃”技藝的神秘感;一級敘事層的“余”有權力展現“童時”“余”的內心世界,比如用“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進行描繪,而次級敘事層的“余”受人生經驗限制,只能陳述自己的所見所聞和理解力所能及的內容。《偷桃》對“余”之外其他人行為、言語、神態的敘述,大體上保持了較為清晰的邊界。比如:“似有所白”“不聞為何語”拉遠了“余”與術人之間的空間距離,襯托出周圍人聲之嘈雜;“子受繩有難色”“(術人)捧而泣曰”都是從人物的外部行為、面部表情著筆,以折射人物的內心世界。當然,《偷桃》偶爾也有越界描述,如“(術人)故作怨狀”“坐官駭詫”均直接點明了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動。盡管如此,從整體上看《偷桃》第一人稱敘事還是非常成功的,偶爾出現的敘述越界并沒有削弱其敘事效果,也無法降低該篇的藝術水平。
其次,蒲松齡善于根據事件的繁簡、輕重選擇主觀情致的融入策略,在控制“余”與故事的距離上表現得收放自如。一般來說,敘述者“我”可以選擇不介入故事的做法,以客觀平靜的方式講述故事;也可以選擇某種特定的方式介入故事,這意味著“我”可以對事件(故事)與人物作出評價、表明態度,可以贊美或者批評“余”存身的環境尤其是社會環境,借以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和政治立場。蒲松齡在這4篇作品里,把客觀敘事與主觀介入都演練了一番。《上仙》中“余”除了覺得狐仙附身的女子“致綏綏有狐意”,流露了對人物的評價外,在故事中一直均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作者遠離了故事,敘述者隱沒了傾向性,把闡釋與評價的權力全部交給讀者,這種敘述策略使故事內涵、人物意象、敘事意圖都隱藏在簡練清雋的文辭之下。《地震》的敘述者在故事中留下的痕跡相對多一些:“此真非常之奇變也”,是地震引發的“余”的感慨;“此與地震時男婦兩忘者,同一情狀也”是對震災事件與婦人從狼口中搶奪孩子事件的評價,意在以“余”的感受觸發讀者的聯想;“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則上升到對人普遍心態的認識,有一定的哲理性。總的來說,《地震》《上仙》故事簡單,線索單一,意蘊單薄,故而敘述者以客觀冷靜敘事為主,敘事節奏明快。《偷桃》之所以能令人在緊張的期待中獲得如釋重負的輕松感,除了某些單獨事件的功能性比較強、串聯而成故事情節線比較長等原因,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那就是一級敘事層的“余”對次級故事的“余”的角色限定得比較巧妙。一級敘事層的“余”追敘往事時聚焦于“童時”的“余”,內在地決定了當年的“余”具有涉世不深、滿懷好奇、喜看熱鬧等特點,正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余”自然“參不透”術人把戲的奧秘所在,這就為制造懸念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偷桃》的故事情節就在原有的懸念尚未解除、新的懸念已經紛至沓來中展開了,一個個接踵而至的懸念把觀眾的情緒(包括讀者的情緒)逐漸推向高峰。甚至核心故事結束了,一級敘事層的“余”仍意猶未盡,繼續在核心故事之外制造懸念——“后聞白蓮教能為此術,意此其苗裔耶?”究竟是也非也?讀者自行品味!《絳妃》中的夢境遭際對蒲松齡來說具有非同一般的隱喻意義,故事沾染的主觀色彩在4篇之中是最濃郁的。夢中得到花神絳妃的賞識與蒲松齡在科考道路上的坎坷遭際存在某種對立的意味,這在給蒲松齡帶來許些的安慰與自得的同時,也能激起他“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 [15]899的失意與惆悵。《絳妃》的第一故事層包含兩個主要事件:一個是“余”“館于畢刺史公之綽然堂”,“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屨登床”;二是“余”從夢中醒來,補足了夢中為絳妃撰寫的醒來“強半遺忘”的檄文。這兩個主要事件相當于序幕與尾聲,旨在為次級故事層發生在夢中一切做鋪墊和收束。蒲松齡實際上是因這一夢境而激動的,否則他醒來沒有必要補足檄文,即便補足了也不一定非要情辭激切、義憤填膺,貫入呼喚千軍萬馬的氣勢。可貴的是,蒲松齡沒有將這篇小說打造成強烈的自我情緒的直白的傳聲筒,也沒有以第一故事層“余”的情緒左右夢中的“余”的心境。《絳妃》講述夢境中“我”經歷的一切,仍然保持了冷靜寫實的筆調,“余”的心態與情懷都是在“余”所見所聞的襯托、折射下浮現出來的,而不是依仗第一人稱敘事的優勢直切地表露出來的。“余”受邀來到“殿閣高接云漢”的仙府,有一“環佩鏘然,狀若貴嬪”的仙人降階出迎,“我”受到禮賢下士般的隆遇,折射出“余”的不同凡俗;絳妃經“余”屢次請命,方告知邀“余”來仙宮的目的,透露出絳妃不以地位的尊貴命令“余”的意味,烘托出“余”擁有值得仙人敬重的美質;絳妃是屢受封家女子欺凌的花神,借“余”的文筆撰寫檄文討伐封氏,可見“余”的文才頗受仙人賞識;“余”撰寫檄文時,絳妃賜筆札,侍姬們有的拭案拂坐,有的磨墨濡毫,有的折紙為范,帶給“余”眾星捧月般的陶醉感;侍姬們圍擁觀看,待“余”文稿逋成,就急忙持去呈絳妃觀賞,“余”自述“妃展閱一過,頗謂不疵”,謙遜中含有一股自得之情。盡享尊榮的“余”從夢中走了出來,但是沒有走出人生難得一遇的暢快情境,于是將一腔熱情傾入醒來補寫的檄文,欲“洗千年粉黛之冤”“銷萬古風流之恨”!
由上可見,蒲松齡的第一人稱敘事作品主體上采用了外視角的客觀敘事策略,故事中的“余”無論是旁觀者還是故事的核心人物,都帶有現實生活中作者的烙印,這反映了蒲松齡創作此類作品時還沒有擺脫紀實觀念的拘囿,其虛構敘事、踵事增華的創作才華未能得以有效施展。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反映了蒲松齡對第一人稱敘事有著清醒的意識和藝術上的自覺性:其一,蒲松齡突破了傳統的以“我”的口吻講述故事的慣性思維和敘事策略。王度的《古鏡記》使用了第一人稱敘事,但故事中的“度”作為事件的見證人,時時超越第一人稱的感知界限,以無所不能的全知視角講述故事,未能保持敘事人稱的協同一致。有些唐傳奇作品以“余”的名義記錄故事,目的是向讀者表明故事真實或故事來源真實,沒有把“余”視為具有獨特敘事視角的敘述者。宋明話本、擬話本中出現的蘊含第一人稱的話語表達,如“看官,則近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 [16]135“看官,今日聽我說《金釵鈿》這椿奇事” [16]169,目的是告知聽話人說話的主要內容或故事標題,實質上仍然使用第三人稱全知敘事。而蒲松齡這4篇作品均能在整體上遵循第一人稱敘事規則,將敘述的筆觸統轄在“余”耳目所及的范圍內,較為成功地實現了限制敘事。其二,蒲松齡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不同故事層面的“我”擁有的話語權與聲音是有差異的。《地震》中,地震現場中的“余”主要將眼光聚焦在人們的行動和外在表情上,講述婦人與狼爭子的“余”則能敘述婦人“急與狼爭”“驚定作喜”“忽悟”等心理活動,這反映了蒲松齡體會到了講述“我在現場的見聞”與講述“我聽別人講述的故事”之間的差異。《偷桃》中,追憶往事的“余”有一些理性思索,而在演春現場的童時的“余”則帶有幾分懵懂,這說明蒲松齡意識到了“敘述自我”與“經驗自我”的差異。《絳妃》中坐館的“余”是寂寞落拓的,夢中的“余”則是春風得意的,這折射出蒲松齡能有意識表現“現實自我”與“幻境自我”的差異。當然,如果蒲松齡能深刻認識到這些不同的“我”“在不同時期對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對事件的不同認識程度,它們之間的對比常常是成熟與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與被蒙在鼓里之間的對比” [12]187,那么,以他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對社會的深刻洞察力以及藝術表現力,定能創作出思想內涵更加深邃、故事情節更加豐富的作品 [10]310。這也說明,古代文言小說在第一人稱敘事的藝術性、深刻性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參考文獻: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蛐?蛐魯迅.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2]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3]李德裕.次柳氏見聞序[M]?蛐?蛐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4]鄭綮.開天傳信記[M]?蛐?蛐王仁裕,等.開元天寶遺事(外七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洪邁.夷堅支丁序[M]?蛐?蛐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6]洪邁.夷堅支戊序[M]?蛐?蛐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7]王平.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8]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M].王文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9]里蒙-凱南.敘事虛構作品[M].姚錦清,黃虹偉,傅浩,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
[10]尚繼武.《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
[11]史蒂文·康納.后現代主義文化——當代理論導引[M].嚴忠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12]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13]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新修訂版)[M].劉象愚,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14]羅鋼.敘事學導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5]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M]?蛐?蛐李白集校注.瞿蛻園,朱金城,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6]吳曉玲,范寧,周妙中.話本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責任編輯: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