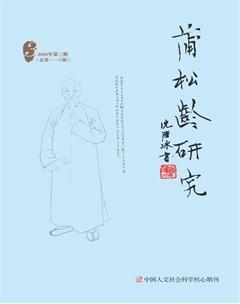論《聊齋志異》夢境敘事
摘要:夢境敘事在《聊齋志異》中具有重要的敘事功能,對情節建構有重要作用。夢境敘事以預敘方式強化了故事懸念,滿足讀者的期待視野,增強了讀者的審美感受,也體現出蒲松齡的天命觀和果報觀念。夢境敘事是小說情節發展的動力因素,一般作為“發送者”行動元和核心事件,推動故事向另一層次發展。在空間維度,夢境敘事構建不同的主題空間,將現實空間與虛幻空間融為一體,展現人物心理,揭示小說主旨,營造出朦朧神秘的意境。
關鍵詞:夢境敘事;預敘;發送者;行動元;主題空間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識碼:A
《聊齋志異》是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說集,代表了清代文言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作者蒲松齡以奇幻之筆,浪漫之思,構建了異彩紛呈的鬼狐世界。從內容方面看,蒲松齡不僅擅長“志怪”,而且也是“記夢”的高手,在四百九十余篇小說作品中,有七十余篇與夢有關,在許多名篇如《陸判》《魯公女》《鳳陽士人》《續黃粱》《絳妃》《田七郎》《香玉》《青梅》《連瑣》《狐夢》《夢狼》《蓮花公主》《司文郎》《王桂庵》等中都有精彩的夢境描寫。孫玉明先生在《〈聊齋志異〉夢釋》一文中曾說道:“夢境手法的巧妙運用,對于人物形象的刻畫及情節的發展等等,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如果離開了夢,便不會有某些作品的產生。” [1]夢境描寫是《聊齋志異》的一大藝術特色,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探討,此方面的論文如郭麗《〈聊齋志異〉記夢作品的敘事結構》,在論文中將夢的敘事結構功能分為四類,對夢的告誡、預示作用及表現人物心理、主觀能動性等作用進行了論述 [2]。從夢的創作類型與意蘊方面研究的論文如劉艷玲《〈聊齋志異〉夢創作類型及意蘊摭談》,文中將小說中的夢分為預兆夢和思緒夢,并認為夢創作的深層意蘊是對理想的追慕和對現實的否定 [3]。總起來看,多數研究者僅僅關注夢的內容、作者之思想,并未從敘事學角度來考察夢的敘事功能以及夢創作所呈現的美學特征,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夢在《聊齋志異》中不僅有預敘的功能,而且作為“行動元”,對情節建構有重要作用。夢境的描繪,更讓作者構筑了多種多樣的敘事空間,通過隱喻意象打破時空局限,營造出朦朧神秘的意境。
一
蒲松齡善寫夢,有其自身的原因。《聊齋自志》中寫道:“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粘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志。” [4]1此段記載,可以看作蒲松齡愛寫夢的淵源。蒲松齡一生坎坷困頓的經歷,如苦行僧般的塾師生涯,讓他對先大人之夢深信不疑,在《聊齋自志》中反復嗟嘆。蒲松齡在小說中精心編織夢境,使小說的敘事時間、敘事空間等方面產生了奇妙的變化,使小說具有了引人入勝的魔力。
夢在《聊齋志異》中首先具備了預敘的敘事功能。預敘一般是指在情節發展中,作者對將來發生之事預先或提前敘述的一種敘述方法,法國著名批評家熱拉爾·熱奈特在《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解釋為:“用預敘指事先講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敘述活動。” [5]1預敘在一定程度上會破壞故事的懸念,在西方的小說中并不多見,而預敘是蒲松齡擅長采用的敘事手法,夢境預敘在《聊齋志異》多篇小說中多次出現。《聊齋志異》中的夢境預敘,多隱喻、暗示,具朦朧性、模糊性特征,在小說中一方面強化了故事的懸念,另一方面促進了情節結構的變化。夢境可以預示故事結局,也可以鋪敘情節,對小說情節建構起重要作用。以接受美學理論來考察夢境預敘,夢境往往喚起了讀者的期待視野,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尋找與現實的聯系,引發他們的聯想與想象,關于此方面的討論可參見拙文《論〈聊齋志異〉預敘敘事》 [6]。
夢境的預敘提前敘述了部分情節內容,消解了部分懸念,但激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增強了讀者對情節的閱讀期待。如《五羖大夫》篇中暢體元“夢人呼為‘五羖大夫,喜為佳兆”,夢境似乎預示其成為高官顯宦,而故事中他以五張羊皮御寒,死里逃生。《放蝶》篇中王進士夜夢女子譴責,“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第二天因不恭而受上司詬罵。《香玉》篇中黃生夜夢絳雪求救“妾有大難!君急往尚得相見;遲無及矣”,后文中黃生星馳至山,阻止了工師砍伐耐冬樹,拯救了絳雪。《石清虛》篇中邢云飛珍愛的奇石被尚書奪走,夜夢一丈夫自稱“石清虛”,并告訴他于明年以兩貫錢贖回,邢云飛如期至海岱門以兩貫錢買回奇石。《寄生》篇中寄生夜夢五可,兩情相悅,后文中兩人雖歷經波折,終結連理。小說中的夢境預敘雖然提前將故事的情節片斷展示給讀者,但是讀者并不能確知故事的全部情節內容,這是由于預敘的情節充滿“未知”,多數情節帶有含糊性和朦朧性,讀者往往對事件的發展過程更加關注,引發更大的閱讀興趣,從這方面看,預敘并未從根本上破壞故事的懸念。《五羖大夫》詼諧的結局出乎讀者的意料,情節設計別出心裁。《放蝶》篇中的“風流小譴”指王進士“以素花簪冠上”拜見直指使,情節富有喜劇性色彩。《香玉》篇中對絳雪的身份,黃生一直猜測,以為她是牡丹花神,直到絳雪托夢求救,黃生才發現絳雪是耐冬花神。在夢境之前,作者已經對懸念進行了層層鋪墊,夢境預敘之后,絳雪身份之謎得以解開,懸念得以消解,使讀者有柳暗花明之感。《石清虛》篇中,邢云飛愛石如命,故事圍繞“得石——失石”而展開,石頭的失而復得,每一次都不相同。邢云飛夜夢一段,預敘了石頭復得的具體情節,而小說下文的鋪敘則顯得合情合理,讀者對相關情節仍然充滿閱讀興趣。《寄生》篇中寄生夜夢五可,五可傾心于寄生,兩人的婚姻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后文中五可卻媒,閨秀待嫁,寄生的婚事一度陷入僵局。夢境預敘雖已經點出故事結局,但情節的發展細節,作者并未透露給讀者,讀者只能通過已知的情節線索,結合自身的閱讀經驗,在大腦中構思故事發展,讀者主動參與小說情節建構,對小說充滿閱讀期待。《聊齋志異》中的夢境預敘,文字極簡省,寥寥數語,引人遐想。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以多變的情節和復雜的敘事手法拓寬更新了讀者的期待視野,給讀者以新奇而又獨特的審美感受。接受美學家姚斯曾經指出:
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識的先在審美經驗與新作品接受所需求的“視野的變化”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特性。 [7]31
《聊齋志異》中的夢境預敘滿足了讀者的期待視野,并且使視野產生變化,形成一定的審美距離,使讀者熟識的審美經驗得以陌生化,提高了小說的審美價值。夢境預敘不僅在情節方面滿足讀者對故事細節的期待,而且在審美經驗方面,往往超越第一讀者的期待視野,以新穎獨特的情節構思增大了期待視野與作品之間的距離,從而提高了小說的藝術性。夢境預敘中布置了許多未定之處和空白點,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加以具體化,增強了讀者的閱讀審美感受。
夢境預敘富有神秘性,有“宿命論”色彩,從表現內容角度來看,《聊齋志異》中多處夢境描寫反映了“因果報應”思想,也表現出蒲松齡受佛學和儒學思想的影響,勸善懲惡,批判社會黑暗現實,表現出儒家知識分子特有的文化心態。蒲松齡雖處于社會低層,卻也關心民生疾苦,亦有“兼濟天下”的雄心,對吏治腐敗,道德淪喪,無不抱有抨擊時弊,挽救世風的責任心。《聊齋志異》中多處夢境描寫,既有預敘的敘事功能,也表現出蒲松齡的天命觀和果報觀念。如《雷曹》篇中樂云鶴樂于助人,終得善報,夢夏平子來“為君嗣,以報大德”,后妻生子考中進士。在《蹇償債》篇中,王卓貸李公綠豆一石,后李公忽夢王卓來投償,家中牝驢產一駒,后數月售驢得錢,適符豆價。《劉亮采》篇中,劉太翁與狐仙胡叟相善,時劉乏嗣,夜夢胡叟來,既醒,夫人生男。《餓鬼》篇中,朱叟幫助齊人馬永,馬永死后報恩,“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即寤,妾生子”。小說中多處描寫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事例,在這些事例中又多采用夢境的描寫形式,來突出“天道”“天命”的神秘與靈驗,這也是蒲松齡夢境預敘的創作動因之一。在《雷曹》中蒲松齡以異史氏評曰:“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在《蹇償債》篇中作者感嘆:“昭昭之債,而冥冥之償,此足以勸矣。”果報思想,在《周易· 坤·文言》中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句,《論語·為政》篇中有“五十知天命”,《季氏》篇中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表述。蒲松齡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他在《賀畢反予公子入武庠序》中說:“大善得大報,小善得小報,天道好還不爽,以所為,卜所報,熾而昌,不俟詹尹也。” [8]99蒲松齡的果報思想,也深受佛教思想影響。方立天先生在《中國佛教的因果報應論》一文中論曰:
因果報應是佛教用以說明世界一切關系的基本理論。它認為世間一切事物都由因果關系支配。善因必生善果,惡因必得惡果。 [9]
蒲松齡顯然以小說中果報的事例來勸人行善,來表彰誠信忠義,凈化社會風氣,以知識分子的擔當來匡濟時弊。正如許勁松先生所說:“儒家的‘天命觀與佛教的宿命論在蒲松齡的頭腦里融合為一,形成了他的世界觀。” [10]蒲松齡在多數寫夢的小說中,在寫夢的外衣下隱藏著他對社會現實、人情世態的看法,用夢境的敘事方式來突出“天道”“天命”的神圣與崇高,以因果報應來闡釋個人在“天命”面前的卑微與無奈。夢的不同內容、夢的不同結果,都體現出蒲松齡獨特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夢境敘事除了具有預敘的作用,在情節建構方面往往是情節發展的動力因素,推動故事向另一層次發展,起到“行動元”的作用。法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家格雷馬斯在《結構語義學》一書中提出了“行動元”概念,此概念的提出,讓敘事學關注小說情節發展的動力因素。不同的人物角色,他們的一系列行動在推動故事不斷發展。行動元旨在考察人物之間,人物與客體之間的行動關系,并將此種關系納入敘事學研究。格雷馬斯提出了三組行動元模式:主體?蛐客體、發送者?蛐接受者、幫助者?蛐反對者,三組行動元呈現二元對立狀態。多數闡釋“行動元”的論文,將人物角色作為考查重點,作為抽象物的行動元很少人去討論,而這正是《聊齋志異》夢境敘事獨特的地方。譚君強在《敘事學導論》中認為:“行動元和角色兩者都被認為是完成或服從于一個行動的,兩者都可以不但包括人(即作品人物或角色),也可以包括無生命的物體和抽象的概念。” [11]160夢境在小說敘事功能方面往往作為“發送者”,屬于“發送者?蛐接受者”行動元模式。胡亞敏《敘事學》中認為:“發送者是推動或阻礙主體實現其目標的一種力量,它可以是人形的,也可以是抽象物。” [12]148夢境在小說中往往改變主體的思想與行動軌跡,成為發送者,促進或阻礙主體實現愿望,從而使情節陡生波瀾,使情節更為曲折。在《田七郎》中,武承休夜夢,一人告訴他惟有田七郎可共患難。夢境不僅預敘了故事以后的情節,而且作為發送者,幫助主體武承休實現“尋知己,共患難”愿望。夢境引出了武承休與田七郎的相識、相知,是情節發展的基礎,也是情節發展的核心事件。羅蘭·巴特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指出:
就功能類而言,每個單位的“重要性”不是均等的。有些單位是敘事作品(或者是敘事作品的一個片斷)的真正的鉸鏈,而另一些只不過用來“填實”鉸鏈功能之間的敘述空隙。我們把第一類功能叫做主要功能(或叫核心),鑒于第二類功能的補充性質,我們稱之為“催化”。主要功能的唯一條件是功能依據的行為為故事的下文打開(或者維持,或者關閉)一個邏輯選擇,簡言之,打開或結束一個未定局面。 [13]14
《聊齋志異》中的夢境在小說中多是核心事件,事件在情節發展中往往為下文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影響整個的情節進程。在故事中,夢境往往出現在情節發展的關鍵之處,決定了故事發展的方向。在《陸判》中,陸判為朱爾旦妻換頭,吳侍御懷疑朱爾旦殺害自己的女兒,要打官司,事情僵持不下。吳侍御女兒托夢,以夢境使朱爾旦洗刷犯罪嫌疑。在小說中,夢境作為發送者,幫助朱爾旦實現“為妻換頭”的愿望,并以兩家成為“翁婿”而完成故事敘事。《魯公女》中,張于旦夜夢青衣人邀去,飲茶沐浴后竟長生不老,使張生能赴“十五年”之約。此文中夢境是發送者,幫助張生與魯公女的相會,而夢中遇仙情節是張生返老還童的關鍵,也是下文故事得以發展的前提,是核心事件。《青梅》篇中,阿喜因家道中落,歷盡磨難,絕望欲自殺,夜夢其父,語之曰:“但緩須臾勿死,夙愿尚可復酬。”在整個故事中,主體行動元是阿喜,客體是其“良匹”張生。青梅是幫助者,幫助阿喜實現自己的目標“得良匹”。因為父母的干預,家庭的變故,阿喜陷入絕境,夢境成為“發送者”,改變了阿喜“欲自殺”的想法,改變了故事發展的方向。《寄生》篇中,寄生鐘情于閨秀,因思成病,夢中得遇五可,兩情相悅。在故事中,寄生是主體,追求的客體開始時是閨秀,后來變成五可,寄生對二女的追求構成了故事的主要情節。夢境作為“發送者”,使寄生從鐘情閨秀到愛戀五可,夢境的干預與介入使主體轉變了思想,從而幫助寄生實現愛情愿望,連娶閨秀、五可二佳人,因夢成婚,得成良緣。夢境作為核心事件,是許多小說敘事過程中的真正鉸鏈,重要性不言而喻。
《聊齋志異》中的夢境作為“發送者”,推動情節前進,成為敘事的動力因素。在小說故事中,對主體與客體這一對行動元來說,主體通常是指人物,客體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其他目的物,人物的行動引導了敘事的演進。而人物的行動則必須由某種動機所支配,有時受到主體情感的影響,從而使小說情節多樣化。夢境作為“發送者”,往往打破情節發展的固有邏輯,改變情節發展的方向,給人以陌生化的閱讀效果,從而使小說情節布局復雜縝密,故事中又有故事,引起讀者閱讀興趣。《聊齋志異》多數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夢境敘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
《聊齋志異》中的夢境敘事,從敘事時間、敘事空間方面來考察,也有很多特色,例如有意識地扭曲時間,多種敘事時序的綜合運用,構筑多種故事空間等。小說一般敘述的是在一定的時間發生在某個空間的故事,人物也好,環境也好,都不能脫離時間和空間而獨立存在。時間與空間是小說敘事的兩大要素,歷來也是敘事學關注的重點。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金曾指出敘事作品情節所顯示的時間與故事空間有密切的聯系,兩者融合成有機的整體。
文學作品中的時空,空間與時間的標示被融合在一個精心布置而又具體的整體中。時間,往往在敘述過程中變得厚實、具體,通過藝術構思顯得清晰可見;同樣,空間變得充滿內容,與時間、情節和歷史發展相呼應。這兩個軸的疊加及其標示的融合顯示了小說世界的時空特點。 [14]84
夢境作為一個超現實的空間,給了作者以相當的自由去擺脫現實世界時空的局限,因而可以“時間倒錯”敘事,在特定的虛幻空間內構思離奇魔幻的事件。事件的發生總是依賴于特定的時間與特定的空間,敘事的時間與空間成為我們考察其敘事類型的一個立足點。《聊齋志異》的夢境敘事,無論是時序、時距的運用,還是空間敘事,都展現出精湛的敘事技巧,這也是《聊齋志異》集古代文言小說之大成的原因之一。下文將從敘事時間與敘事空間兩方面來揭示夢境敘事藝術特征。
敘事學中的時間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解讀,一是敘事時間,一是話語時間。申丹在《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一書中解釋為:
“敘事時間”是指所述事件發生所需要的實際時間,“話語時間”指用于敘述事件的時間,后者通常以文本所用的篇幅或閱讀所需的時間來衡量。 [15]112
小說家為了編排情節的需要,往往有意識地改變敘事時間,對故事中的時間進行重新安排,以求達到最佳的敘事效果。在《聊齋志異》寫夢的篇章中,有以長篇幅寫夢的小說,如《續黃粱》《蓮花公主》《夢狼》等。在《續黃粱》中,小說描述了曾孝廉的夢境,在夢中他貴為宰相,后被彈劾流放,被盜賊所殺,死后入地獄受酷刑,然后投胎為乞兒之女,最終蒙冤受死,醒來始覺一夢。在小說夢境中,蒲松齡有意改變事件的排列順序,使故事發生的先后時序與話語順序產生倒錯現象,采用預敘、倒敘等逆時序的敘事手法,形成“時間倒錯敘事”。在《續黃粱》中,曾某夢中為宰相,其中“王子良周濟”一事與“郭太仆曾睚眥我”都是曾某回憶以前發生的事,“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購充媵御”也是曾某的回憶,都屬于倒敘。小說開頭“星者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與曾某夢境相符,屬于預敘。在《夢狼》篇中,白翁夢長子甲被金甲勇士敲齒,屬于預敘,下文中其長子甲醉中墜馬折齒,時間則是其父做夢之日,兩事件是同時發生的,甲墜馬折齒則是事后回憶,屬于倒敘。小說中的話語時間對故事時間進行了重新調整,以白翁之夢的情節、時間的精確來突出夢境的神奇與“鬼神之道”之不誣。
從敘事時間“時距”來考量,《聊齋志異》中多數寫夢的小說雖為短篇,卻有長篇小說的容量,可以看出“時距”對于展現小說主題與塑造人物所起重要作用。敘述速度以秒、分、小時等時間來計量,它與小說文本篇幅之間的對比關系,往往體現了小說所獨有的敘事節奏。法國學者熱拉爾·熱奈特在《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提出了四種敘述運動即概述(概要)、場景、省略、停頓。在《續黃粱》中,曾某任宰相時的所作所為,基本采用概述。例如“科頭休沐,日事聲歌”“早旦一疏,薦為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擢用”“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等,敘事的速度很快,以快節奏將數月、數年的事情一筆帶過,形象表現出曾某擅權妄為,作威作福的情形。而與之相對照,小說中又有多處場景描繪,放慢了敘事速度,刻畫了曾某被彈劾后的情形。例如抄家一節,以曾某視角詳細紀錄了武士數十人奉旨籍家的過程,再如遇盜一節,曾某與強盜的對話場景,曾某入地獄受刑一節,也詳細描述了其受油鼎和刀山之刑的場景。曾某轉生為乞兒之女一節,則用省略,十四歲之前的經歷被略去,秀才遇賊一段則用概述。小說中不同的敘事速度錯綜其間,形成了輕重緩急的敘事節奏,情節事件有條不紊,突出了小說“人生如夢”的主題。《續黃粱》中曾某經歷榮華富貴,地獄刑罰,轉生后再蒙冤入獄,將幾十年間發生的眾多事件,聚合到一個夢中,而真實的故事發生時間僅僅幾個小時,兩者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形成情節的張力,給人以強烈的心理震撼。在《鳳陽士人》篇中,作者多用場景敘事,鳳陽士人、其妻與麗人相遇、夜飲場景,作者工筆細描,細節生動,將夢境與現實融合在一起。場景敘事的舒緩節奏正好符合女子之夢朦朧、傷感的特點,使故事蒙一層神秘的面紗。細致的場景描寫可以延緩情節的推進速度,打破故事歷時性的順序發展,在敘事上達到了一種時間停頓和共時性的效果。
從敘事空間來看,《聊齋志異》中夢境敘事善于在小說中營造特殊的超現實空間,在“故事空間”中,構建不同的主題空間,在小說敘事中具有重要的結構意義,對人物形象塑造也有重要作用。小說所營造的空間往往是獨一無二的,為人物與情節專門設計的,空間的存在與人物形象的凸顯有著密切的聯系。空間轉換可以引發不同的事件,人物的活動由此展開,夢境的產生空間既是刻畫人物的客觀要求,也是小說主題意蘊的最佳呈現方式。夢境往往對時間扭曲變異,以獨立的主題空間,改變情節發展的固有邏輯;夢本身的非理性又給作者以相當的自由進行創造,使夢境敘事具有多層次的隱喻。如《夢狼》,白翁夢中去長子府衙,所見官虎吏狼景象。府衙,是具有社會因素的空間。民眾對府衙懷有恐懼的心理,而黑暗吏治下,官員貪贓枉法,無疑更加重了府衙的威嚴與神秘。“官虎吏狼”的夢中景象顯然與府衙的空間有關,而吃人等細節的描繪更是官員貪腐暴戾的隱喻。《邵九娘》中夢境空間為廟宇,廟宇為百姓祭拜祈福之地,小說中神靈降臨,對金氏進行譴責警告。而金氏奇妒,屢受懲戒的系列事件顯然與夢境廟宇空間有關,廟宇所具有的象征意義與小說宣揚的“因果報應”思想是相契合的。《薛慰娘》中,夢境空間為屋宅,屋宅是富有家園感的空間,給人以安全感。在小說中,李叟提親,欲將義女慰娘嫁給書生豐玉貴,對話的場景表現出靜謐安詳的溫馨,符合人們對屋宅的想象與記憶。《續黃粱》中,則構筑了不同的敘事空間,有宮廷,有山野、有地獄、有屋宅等,在宮廷寫曾某發跡,在山野寫曾某遇盜,在地獄寫曾某受刑,在屋宅寫曾某蒙冤,敘事空間的轉移,核心事件也在變化,曾某在每個故事空間心理活動的變化,將一奸佞宰相刻畫出來。《王桂庵》中,夢境的空間則為江村,有竹有花的亭園空間,而王桂庵與蕓娘的相遇則發生在這一具詩情畫意的空間內,蕓娘的美麗多情、聰慧知禮也借江村的空間表征出來。
《聊齋志異》中夢境敘事在空間維度,將現實空間與虛幻空間融為一體,打破現實與非現實的界限,以此營造出朦朧神秘的意境。蒲松齡在創造夢境時,從小說敘事與審美目的出發,構建逼真的夢境空間,在此故事空間內,構思情節和人物關系,表現人物心理和揭示作品主題。從小說敘事來看,夢境敘事是插入的話語段落,它從屬于小說敘事,在時間、空間方面與小說敘事有密切的相關性;另一方面,夢境敘事又仿佛是獨立的敘事層次,它的敘事時間有著獨立的時序,敘事空間自由展開,獨立于小說的故事空間之外。在《蓮花公主》中,竇旭晝寢,夢中到桂府做客。竇旭醒后,再夢與公主成婚。后巨蟒入侵,竇生夢醒。小說結尾竇生為蜂筑巢,鄰翁殺蛇。小說中夢境空間與現實空間不斷轉換,而竇生與公主成婚一段,作者有意混淆,使人難分夢境與現實。巨蟒入侵一段,渲染巨妖威力,制造緊張氣氛,公主悲啼一段,夢境變為現實。竇生筑蜂巢,群蜂自來,以應夢中“遷都”“舉國相從”之事,捉蛇殺蛇一節又應夢中“千丈巨蟒盤踞宮外”描述,夢境與現實開始融合為一體,夢境的情節在現實中找到依托。《王桂庵》中,王桂庵夢入江村,遇見所思之人蕓娘,后在鎮江誤入小村,道途景象,仿佛平生所歷,夢境中景物與現實相符,王桂庵懷疑是夢,與蕓娘的相遇、問答使他從夢境走進現實。在《狐夢》篇中,畢怡庵夢中赴酒宴,狐女四姊妹斗口勸酒,夢境的故事空間為“大院落中堂”,小說描繪的是嬉笑歡宴的場景,栩栩如生,如同現實。畢怡庵夢醒后,方知為夢,而“鼻口醺醺,酒氣猶濃”又疑非夢,虛幻的夢境與真實的現實被作者有意聯結在一起,以夢的非理性打破時空界限和情節發展的固有邏輯,在敘事方面有特殊的審美意義。
《聊齋志異》中的夢境敘事在敘事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作者熟練地以預敘、倒敘編排情節,對故事時間進行精心的調整,形成“時間倒錯”敘事。另一方面,在夢境敘事中,以概述、場景、省略等不同的時距,構成了小說特有的敘事節奏。《聊齋志異》中的夢境敘事在小說中構建不同的主題空間,在不同的故事空間里,表現人物心理,塑造人物形象,推動敘事進程。夢境敘事融合現實空間與非現實空間,表現出神秘莫測的充滿詩意的審美風貌,《聊齋志異》中夢境敘事高妙的敘事手法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孫玉明.《聊齋志異》夢釋[J].蒲松齡研究,1994,(1).
[2]郭麗.《聊齋志異》記夢作品的敘事結構[J].蒲松齡研究,2006,(2).
[3]劉艷玲.《聊齋志異》夢創作類型及意蘊摭談[J].東方論壇,2009,(6).
[4]蒲松齡.全本新注聊齋志異[M].朱其鎧,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5]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 [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6]姜克濱.論《聊齋志異》預敘敘事[J].蒲松齡研究,2014,(2).
[7]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M].周寧,金元浦,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8]蒲松齡.蒲松齡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方立天.中國佛教的因果報應論[J].中國文化,1992,(7).
[10]許勁松.《聊齋志異》中因果報應思想論析[J].江淮論壇,1994,(6).
[11]譚君強.敘事學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2]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13]羅蘭·巴特.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M]?蛐?蛐敘述學研究.張寅德,編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14]M. M.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M].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15]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責任編輯: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