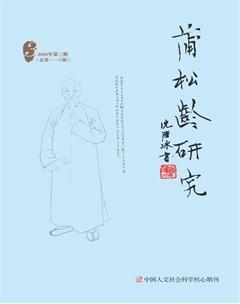《聊齋志異》中的“野人”蹤影
摘要:《聊齋志異·五通》篇所寫的“五通”,實際是一種被稱作山魈、山繅、獨腳鬼、“山鬼”、“野女”、“野婆”、“野人”等的一種人形動物,“五通”則是對這類動物被神化后的稱呼。它們是介乎人與世界上已搞清楚的四種類人猿之間的一種動物,后人泛稱其為“野人”。直至明清時期,這類動物在江浙某些地區還一直存在,而蒲松齡即根據民間傳說而筆之《聊齋》。如果說屈原《九歌·山鬼》所描寫的“山鬼”是生活化、藝術化的“野人”,所展現的是“野人”的美好面;那么蒲松齡筆下的“五通”則是被妖化和神化后的“野人”,所展現的是“野人”的邪惡面。但兩者同樣都通過文學作品為后人留下了“野人”活動的蹤影。
關鍵詞:五通;山鬼;野人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識碼:A
《聊齋志異》有《五通》二則。前一則說的是明季吳中“五通”為害,“民家美婦,輒被淫占”,幸有萬生剛猛善射,連殺三“通”,另一“通”亦被斷其一足,入于江中。后一則說的是剩余的一“通”被金龍大王之女遣婢“閹之”,而后遁去。故事最后,蒲松齡調侃道:“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為害也。”而“五通”究竟是什么東西呢?《五通》篇中僅云被萬生所殺的三“通”,一現形為馬,倆現形為豕,而后兩“通”,則未言其為何物。
《聊齋志異》中的《五通》應是蒲松齡根據其南游期間的所見所聞尤其是民間傳說而敷演成篇的。其時江浙一帶的“五通”崇祀之風甚盛。《清史稿·湯斌傳》記:
蘇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幾數百年,遠近奔走如騖。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婦病,巫輒言五通將娶為婦,往往瘵死。斌收其偶像,木者焚之,土者沉之,并飭諸州縣有類此者悉毀之,撤其材修學宮。教化大行,民皆悅服。
湯斌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間任江寧巡撫,其毀五通祠之事也就在這數年之內。此前,吳中崇祀“五通”之風則是“遠近奔走如鶩”。而蒲松齡南游并在寶應孫蕙府中作幕是在康熙九年(1670)秋天至康熙十年(1671)秋天,也就是在湯斌毀淫祠之前的十四年,其時吳中淫祭風氣之盛更是可以想見的。對此,蒲松齡不但親聞,也還會親見其祭祀場面。而蒲松齡對“五通”的認識,很可能也就停留在民間傳聞的基礎上。于是,他便本著“志異”的原則,將傳聞中一些怪異而有趣的事筆之于《聊齋》了。所謂淫占美婦,現形為馬、豕,以及閹其一“通”之說,就這樣被他采入《聊齋》故事之中。不過即此也可以看出,早在湯斌毀五通祠之前,蒲松齡已對“五通”之祭深惡而痛絕之,并借其志異之筆,首張誅伐之幟了。至于民間傳說蒲松齡是假《五通》篇以嘲笑南方人之“半通”,那只是后人的曲解而已,并非蒲老先生之本意。
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湯斌摧毀淫祠的一百五十余年之后,吳中祭祀“五通”的風俗又恢復了。《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淫祠”條記:
三吳風俗信祀淫祠。康熙間湯文正公撫吳,曾經奏毀。久而禁弛,僧人漸搭房屋,香火復盛,祈禱者又接踵于途矣。道光乙未,江蘇按察使裕謙復毀上方山五通祠,獲僧傅德、成鎰等,嚴加懲辦,并禁民間如有私奉五通、太母、馬公等像者,以左道論。由此始得稍息。
裕謙復毀五通祠之后,民間私奉“五通”者并未完全根絕,只是“始得稍息”而已。這又是為什么呢?事情便不得不從“五通”本身說起了。
“五通”實際上是一種動物,而不是五種神靈。明清時期,它在江浙某些地區一直是存在的。正如蒲松齡在《五通》篇開首所說,“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只不過狐常被“仙”化,而“五通”則被“妖”化,又進而被“神”化罷了。我們先看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一)對“五通”的記載:
諸說雖少有參差,大抵俱是怪類,今俗所謂獨腳鬼是也。邇來處處有之,能隱形入人家淫亂,致人成疾,放火竊物,大為家害。法術不能驅,醫藥不能治,呼為五通、七郎諸神而祀之。
原來此物即俗所謂“獨腳鬼”,而“五通”乃是人們對其“神”化之后的稱呼。獨腳鬼亦稱山魈。袁枚《子不語》卷六“縛山魈”條記:
門外有怪,頭戴紅緯帽,黑瘦如猴,頸下綠毛茸茸然,以一足跳躍而至。見諸客方飲,大笑去,聲如裂竹。人皆指為山魈,不敢近前。……地上遺緯帽一頂,乃書院生徒朱某之物,方知院中秀才往往失帽,皆此怪所竊。
《子不語》續卷五“山魈怕桑刀”條亦記:
常山璩紫庭貢士,有書塾在東門外山中。時有山魈出沒其間,土人習見亦不為怪,呼為獨腳鬼。皆反踵而行,其來必有風……山魈愛聽歌,有張某舘衢州山中,每夜山魈躑躅而來,強嬲唱曲。
又,俞樾(曲園)《右臺仙館筆記》卷一“趙姓”條還記:
宜興山中一趙姓者,每夕宿火于爐,加煤其上,以供明日之用。忽一夜,煤火皆發棄地上,連夕皆然。伺之,則一獨足鬼俯爐而窺,且笑且發,群起搏之,一跳即逝。或曰此山魈也,是畏爆竹。乃伺其至,燃爆竹投之。鬼驚仆,眾人執之,于其足旁得一鼗鼓。鬼雖黑丑,殊無所能,惟叩首作乞憐狀。或予之飲食,恐怖不敢多食。惟示以所棄鼗鼓,則喜而笑。姑與之,入手即大笑,奮足一躍,倏忽脫去。
袁子才與俞曲園所述之獨腳鬼亦即五通,是實實在在的一種山中動物,其神通并沒有蒲松齡所說的那樣大,僅是喜歡竊物而已(如竊秀才帽子及小孩撥浪鼓之類),而且還喜聽歌曲,“土人習見亦不為怪”。即使被人捉住了,也“殊無所能,惟叩首作乞憐狀”。而作為動物,其主要特征有三:一是“黑瘦如猴”,二是善笑,三是“以一足跳躍”,故被稱為“獨腳鬼”。
實際上,“獨腳鬼”并非只有一條腿,正如章太炎先生在《小學答問》中所說:
山鬼即夔。......山繅為物,今貴州、四川有之。聲如小兒,足跡似人,民呼為“山神子”,畏憚焉,誠所謂木石之怪者。古謂“夔一足”,或如鶴有兩脛,常縮其一,非真一足也。
太炎先生除謂“山繅為物”實即古人所說的“夔一足”外,還指出所謂“獨腳鬼”,并“非真一足”也,而是像仙鶴那樣“常縮其一”罷了。而關于“夔一足”的記載,古代文獻中也常能見到。如《國語·魯語下》引孔子之言“木石之怪夔、魍魎”,三國韋昭注:
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音騷,或作犭喿。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
《太平御覽》卷886“精”條引《白澤圖》亦云:
山之精,狀如鼓,色赤,一足而行,名曰夔。呼之,可使取虎豹。
這種人形動物在后世亦被稱作“山臊”、“山都”、“山鬼”、“野女”、“野婆”、“野人”、“毛人”等。請看相關的文獻記載: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丈余,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名曰山臊。
——《神異經·西荒經》
廬江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裸身,見人便走。有男女,可長四、五尺,能嘯相喚。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 ——干寶《搜神記》卷十二
南康有神曰山都,形如人,長兩尺余,黑色,赤目黃發。深山林中作窠,狀如鳥卵,高三尺余,內甚光彩。? ——任昉《述異記》
山都,形如昆侖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開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見蟹食之。……木客生南方山中,頭面語言不全異人,但手腳爪如鉤利。居絕巖間,死亦殯殮。能與人交易,而不見其形也。
——鄧德明《南康記》(《太平御覽》卷967引)
安國縣有山鬼,形如人而一腳,僅長一尺(丈)許,好盜伐木,入鹽炙石蟹食。人不敢犯之。能令人病及焚居也。
——《本草綱目》卷五十一引鄭輯之《永嘉記》
日南有野女,群行覓夫。其狀藠白,裸袒無衣襦。
——《后漢書·郡國志》五劉昭注引《博物記》
狒狒,西蜀及處州山中亦有之,呼為人熊。人亦食其掌,剝其皮。閩中沙縣幼山有之,長丈余,逢人則笑,呼為山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魈也。
——《本草綱目》卷五十一引《方輿志》
古之說猩猩者,如豕、如狗、如猴。今之說猩猩者,與狒狒不相遠,云如婦人被發袒足,無膝群行,遇人則手掩其形,謂之野人。
——羅愿《爾雅翼》
(丹州)有獸名野婆,黃發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以下有皮累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其群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所殺,至死以手護腰間。
——周密《齊東野語》卷七
房山高險幽遠,石洞如房,多毛人,長丈余,遍體生毛,時出嚙人雞犬,拒者必遭攫搏。? ? ——清代《房縣志》
以上諸說雖稍有不同,但所描寫的顯然不是今天動物園中尚能見到的猩猩、狒狒、山魈之類,而是一種人形動物。故有的文獻便徑稱此種動物為野人、野女、野婆。它們與今天盛傳的神農架中的“野人”是否屬于同一類型的生物呢?竊以為它們間的相似度應該是很高的。如直立行走(受驚或登坡時也能四肢并用),披發,多毛,多疑,善笑,體格靈巧,喜歡盜物,善攫婦女等。但它們雖具有人的一些特征,卻還不會勞動,沒有語言(只有一些發音符號),也沒有社會分工。它們是介乎人與世界上已搞清楚的四種類人猿之間的一種動物 [1]。
大約在明清時期,這種被稱為“獨腳鬼”或“野人”的動物,其分布還是很廣的,而蒲松齡南游的江蘇一帶也應是屢見不鮮的。當時的人們出于對此種動物的“畏憚”,先是把它們視為妖物,隨后又將其奉為“五通”之神而加以供奉。其間雖有湯斌及裕謙曾將五通祠摧毀,但這種動物并沒有滅絕,其危害也沒有停止,所以民間仍是奉之如故,只不過到了最后又演化為“五猖神”了。如魯迅在《朝花夕拾·五猖會》中所寫的“五猖神”,便是由“五通神”演變而來的。此后隨著環境的變遷及人類足跡的擴大,這些動物的活動領地逐漸縮小,其生存也越來越艱難,最后便只能留存于湖北的神農架一帶。這也就是今天的人們已很難在神農架以外地區發現“野人”的原因了 ① 。當然,關于神農架地區“野人”的有無,學術界至今還在爭論。不過從歷史上來看,僅1925年到1942年間,房縣就曾有活捉或打死“野人”的多次記載 [1]。1949年以來,神農架地區對“野人”的目擊者,總數已達240多人次 [2]。直至近年來,在神農架地區遭遇“野人”的事例也時見報道 [3]。目前,“野人”的實體雖然還沒有發現,但沒有發現不等于沒有,今天沒有更不等于過去也沒有。
至于在文學作品中描寫過“野人”的,則除蒲松齡的《五通》外,更早的還有屈原《九歌》中的《山鬼》。《山鬼》篇表面看寫的是一失戀少女的形象,實際上她的原型便是“野人”。篇首“若有人兮山之阿”一句,既已暗示了“山鬼”的真實身份。“若有人”,仿佛似人也。而仿佛似人又不是人的動物又是什么呢?實不免會令人聯想到“野人”。再看“山鬼”的日常裝束。她“被薜荔兮帶女蘿”,“被石蘭兮帶杜衡”,即身披薜荔和石蘭,并以女蘿和杜衡為帶。此四者皆為香草,而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女蘿”。女蘿即兔絲,是一種棕紅色的絲狀寄生植物。“山鬼”身系棕紅色的兔絲,與文獻記載(如湖北《房縣志》)及近人目睹的“紅毛野人”的形象便十分相似。再看“山鬼”的居住環境。篇中寫她居于“山之阿”,“處幽篁兮終不見天”,即居住在山坳的幽密竹林中;她“乘赤豹兮從文貍”,即出入與野獸為伍;她時而奔走于“石磊磊兮葛蔓蔓”的澗谷,時而又獨立于“風颯颯兮木蕭蕭”的山巔。這多么像文獻記載的“野人”的生存環境啊!至于篇中所寫“山鬼”的生活習性,如“既含睇兮又宜笑”,及“君思我兮然疑作”,更與文獻記載的“野人”“多疑”、“善笑”特征相符合。還有“山鬼”的“留靈修兮憺忘歸”,即渴望能遇上“公子”、“靈修”等迷于山中的“情郎”,也與“野女”“群行覓夫”的習性一致。甚至“山鬼”的“折芳馨兮遺所思”,也可由《永嘉記》所說的“山鬼”“好盜伐木”以得到印證。總之,人們透過屈原《山鬼》篇所描寫的那位天真爛漫而又幽怨多情的少女形象,實不難發現其原型即“野人”的種種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以“野人”作為描寫對象的偉大詩人。
最后再回到《聊齋志異》的《五通》篇。如果說屈原所寫的“山鬼”是生活化、藝術化的“野人”,那么蒲松齡所寫的“五通”則是妖化與神化后的“野人”;前者所展現的是“野人”的美好面,而后者所展現的則是“野人”的邪惡面。但兩者同樣都通過文學作品,為后人留下了“野人”活動的蹤影,這實在是很難得的。
參考文獻:
[1]劉民壯.沿著奇異的腳印-鄂西北山區“野人”考察[J].百科知識,1979,(2).
[2]張良.他們在尋找“野人”-訪神農架的科學考察者[N].甘肅日報,1980-09-05.
[3]張崇琛.“山鬼”考[J].寧波大學學報,1998,(4).
(責任編輯:譚? 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