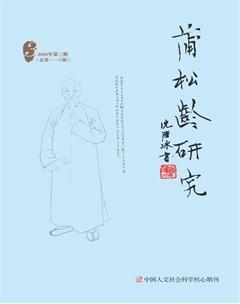聊齋詩文中的淄川景物考辨
邵祺昌 孫啟新
摘要:《聊齋詩集箋注》《聊齋詩文中的淄西景物考》有個別景物的箋注和考察不甚精準,甚至主觀臆斷。通過廣泛研讀相關史料、實地走訪眾多景點,認為“北山”不能單指長白山,而是長白山南麓群山的泛稱,應包括叉拉山(茶葉山)、臥牛山、玉清山和長白山等;“龍舟山”是沖山的別稱,并非豹山;“虎頭石”坐落在淄川區嶺子鎮小口村沖山大岬口之西的沖山西段,即蒲松齡所說的龍舟山上;“南山”當為今之沖山,即大史村的南山,并非豹山;東山不是黌山,而是蒲松齡所居村莊東邊群山的總稱。對張古村的玉皇閣,豹山的豹巖觀、清夢樓等建筑群的地理位置、建筑年代、建筑規模及毀壞過程進行了詳實考證。
關鍵詞:北山;龍舟山;虎頭石;南山;東山;玉皇閣;豹巖觀;清夢樓;考辨
中圖分類號:I207.22? ? 文獻標識碼:A
趙蔚芝先生《聊齋詩集箋注》對聊齋詩涉及的所有景物作了詳細箋注,張永政、王一千先生《聊齋詩文中的淄西景物考》就淄川西部蒲松齡詩文中的眾多名勝古跡、人文景觀作了實地考察,這些考證對于研究蒲松齡的生平和詩詞文章提供了可貴的第一手資料。近年來,筆者通過廣泛研讀相關史料、實地走訪眾多景點,發現《聊齋詩集箋注》《聊齋詩文中的淄西景物考》有個別景物的箋注和考察不甚精準,甚至主觀臆斷。現將相關資料梳理成文,以請教于從事聊齋學研究的專家學者。
一、北山
蒲松齡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寫作兩首七言律詩《重陽王次公從高少宰、唐太史游北山歸,夜中見訪,得讀兩先生佳制,次韻呈寄》。詩其一云:“午夜敲門貴客殘,登堂喧笑禮儀寬,未分勝友名山座,猶得奚囊妙句看。去就依人常似鳥,工夫化鶴不成丹。高齋蕭索惟秋樹,李郭仙舟望亦難。”詩其二云:“詞人車馬北山游,日暮攜歸詩句遒。爽氣常存黃葉下,逸思欲抱白云留。重陽無酒憐新菊,九月迎霜戀敝裘。兄弟茱萸應插遍,年年為客負清秋。” [1]181
詩題及詩其二中的“北山”,趙蔚芝先生注釋:“北山,西鋪北面的長白山。山北屬鄒平,折而西屬章丘,南接淄川,東北屬長山(今并入鄒平)。《抱樸子》稱為‘泰山之副岳。《太平御覽》以為‘山中云氣長白,故名。” [1]181詩其一第三句中的“名山”,也指北山。對于注釋中“北山,西鋪北面的長白山”的說法,筆者認為欠妥。
首先,“北山”不能單指長白山。蒲松齡在西鋪設館授徒三十年,入鄉隨俗,在其詩詞中時常使用當地的習慣用語。如蒲松齡的七言絕句《留別畢子帥》詩其三:“君昔送我在橋北,我昔送君在橋南。橋上依然南北路,千條楊柳盡鬖鬖。” [1]159詩中的“南北路”即為一例,因為畢氏族人習慣把西鋪稱作南莊,把萬家莊稱作北莊,所以詩中“南北路”是特指,即南莊(西鋪)和北莊(萬家莊)之間的道路,不是泛稱。與其相類似,詩題及詩其二中的“北山”亦是如此,“北山”不能單指長白山,而是王村地域(現淄博市周村區王村鎮一帶)的村民對長白山(俗稱白云山)南麓群山的統稱。詩中的“北山”應包括叉拉山(茶葉山,舊寫作嵖岈山)、臥牛山、玉清山和長白山等。其中叉拉山在蒲松齡《畢子光小閣落成,戲為長歌》中又稱為“少白山” [2]109,這是因為長白山為泰山副岳,叉拉山又為長白山系的一座小山,故名少白山,也就是小長白山的意思。
其二,以西鋪為基點來定義長白山的位置也不妥。因為長白山距離西鋪至少在二十里以外,而西鋪以北還有十幾個村莊都在長白山以南,西鋪和長白山根本不搭邊,因此不可以用西鋪作基點來定義長白山的位置。
其三,從行政區劃來辨別北山位置。乾隆八年(1743)淄川縣行政圖標示,“北山”的范圍在淄川縣西北鄉、正西鄉的北部以及章丘、淄川、長山三縣的交界處。西鋪與王村為鄰,在淄川正西四十里處,不在“北山”范圍之內。再從現在的行政區劃來看,鄒平市臨池鎮的北園、梁家莊、洞子頭、橋子上、殷家莊、王家莊、南南寺、北南寺、高莊、上源流、下源流、佛生莊、青冢、郭莊、臨池、望京等村;濟南市章丘區普集鎮的曹家村、池子頭村、博平村、楊官村、肖家村、孫家村、井泉村、蘇家村、傳李村、侯家村、小柏村、大柏村、西洼村等,都屬于蒲松齡詩中“北山”一帶,唯獨淄博市周村區王村鎮不在“北山”的范圍。所以,把“北山”定義為“西鋪北面的長白山”謬誤太大。
二、龍舟山和虎頭石
康熙三十七年(1698)秋天,蒲松齡與諸位同仁游覽龍舟山,寫有七言古詩《九日與同人登虎頭石》,詩小序:“石在龍舟山巔,絕類虎頭,唇齒畢具,相傳系大族興衰。畢有豪士,夜夢虎嚙,以為石之妖也。率士鑿之,石破髓流,類瑙色,煮而食之,甚甘。今惟頸存耳。”詩云:“龍舟山上綠云堆,登顛絕叫天門開。削壁石花大如席,坐映青山翠欲滴。細草芳潔抱石溫,野菊冷艷黃金色。老友筋力半衰殘,露頂脫帽爭援攀。亂披短發上空碧,行云直蕩胸懷間。居人指石以為虎,有人夢虎遷石怒。大招工匠繦屬來,遙環領項縱斤斧。虎頭墮地摧山岡,齒牙崩臥如群羊。石髓軟傾赤瑪瑙,煮啖脆膩雜膻香。山上生石幾千載,一旦石破山容改。壯士野死頸血青,山靈福報將無乃。” [1]584
對于詩題和詩中的“龍舟山”“虎頭石”,盡管趙蔚芝先生和張永政、王一千兩位先生已分別作出相應的注釋或說明,我們以為還有商榷之處。
(一)龍舟山的考證
趙先生對龍舟山注釋:“龍舟山,《淄川縣志·山川》未載。然‘豹山一條云:‘歷級而上,大似浮槎。絕巔兩石相對,一徑中通,呼曰天門。與此詩所言山勢相合:‘龍舟近于‘浮槎,山巔均有‘天門,意龍舟山乃豹山別名。” [1]585趙先生把龍舟山注釋為豹山有兩個證據,一是“浮槎”,二是“天門”,這是不對的。
乾隆《淄川縣志·輿地志·山川》記載:“豹山,縣西五十里。山巔建立宮觀,各依巨石,上筑高臺,梁柱闌楯皆石。歷級而上,大似浮槎。絕巔兩石相對,一徑中通,呼曰天門。從松柏雜樹中遙望,南山縹緲,若蓬萊三島。” [3]313豹山分為東、西豹山,兩端山勢較高,中間低矮且平坦,是人們南北過往豹山的大道。自遠處瞭望,豹山形如兩頭上翹的木船,即縣志所言“大似浮槎”。趙先生因為認為“龍舟”“近于浮槎”,于是就把豹山誤為龍舟山。再者,《淄川縣志》中的天門是“兩石相對,一徑中通,呼曰天門”,這樣的景況不僅豹山有,沖山虎頭石也有。筆者之一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帶領學生游覽虎頭石時,就稱其為“一線天”。趙先生不了解虎頭石實際景況,認為只有豹山才有“天門”,其結論失之偏頗。
嘉靖《淄川縣志·封域志·山川》記載:“沖山,在縣治西三十五里。其形突然上起。” [3]22縣志所說的沖山在王村鎮大史村南二里處,即沖山大岬口以西的一段山脈,大史村人稱之為“南山”。南山上有一景觀“虎頭石”,千百年來被大史村人視為風水寶地(下文另有考證)。這段山脈被稱為“龍舟山”,可追溯到隋唐時期。乾隆《淄川縣志·輿地志·古跡》記載:“土鼓城,漢縣,縣西五十里。高齊并土鼓入衛國縣,隋改衛國曰‘亭山。唐省亭山入章邱。今土鼓故城(注:今王村鎮沈古村),實在淄川境內,分為四村,土人通呼為‘鼓城,而以居者之姓氏別之,遺址門垣尚存。又按:《隋志》注:‘亭山,云有龍舟山、儒山。” [3]330《隋志》中所稱儒山在沈古城南五里處,龍舟山在沈古城東二里處,即沖山(大史南山)。至此,可以斷定“龍舟山”是沖山的別稱,并非豹山。當然,沖山還有其它的別稱。沖山山脈因自東而西綿延起伏且有九個山頂,又像一輪彎彎的月牙橫臥在淄西大地上,也稱“九頂月牙山”,亦簡稱“月山”。清初淄川名士趙金人取號月麓,即源于此。
(二)虎頭石的考證
張永政、王一千先生《聊齋詩文中的淄西景物考(一)·淄西奇觀虎頭石》,對蒲松齡詩文《九日與同人登虎頭石》涉及的“虎頭石”進行了考證,對虎頭石及周邊景物描寫極為詳盡,再現了虎頭石原貌,但對于虎頭石的準確位置以及歸屬權、景觀保護與毀壞過程等敘述卻有不當之處,如《淄西奇觀虎頭石》介紹:“虎頭石位于淄西王村鎮楊古城村(漢土鼓縣城)東里許的龍舟山北段上”。[4]112
1.虎頭石的位置
由《淄川縣志》所載沖山“在縣治西三十五里”可知,沖山坐落在淄川縣西部地區,具體地址是東起今淄川區商家鎮的楊家村境內,西至今周村區王村鎮的大史村。《周村區志·自然環境·周村區山丘一覽表》載:沖山,大史村南1.5公里,走向東西、西北,面積0.7平方公里,高程242米。[5]58經實地察看,沖山之“虎頭石”坐落在淄川區嶺子鎮小口村沖山大岬口以西的沖山西段,即蒲松齡所說的龍舟山上,具體地點是“蔓葫蘆頭頂”和“塔山頭”的中間地段。
2.虎頭石的歸屬權
蒲松齡在詩中提及的龍舟山,目前由現王村鎮的大史村、楊古村和現嶺子鎮的小口村、朱家村、王家村共同擁有;沖山虎頭石的具體位置在山脊北側,其歸屬權自古以來都屬于大史村,從未屬于楊古村,更與嶺子鎮不沾邊。
光緒元年(1875),為了保護虎頭石,大史村畢豐維、畢聿成等人請求淄川知縣徐大容專門發出《示嚴禁事》官文:據正西路史家莊監生畢豐濰(維)、生員畢聿城(成)等稱切,生等莊西南有塔子山一座,山巔有玉皇廟。迤南有山石突起,俗名“石虎”,系塔山來脈,直沖生等莊村。因系風脈攸關,莫敢損傷。相傳乾隆年間有附近居民在此“石虎”處鑿石使用,以致生等莊中老幼疾病死亡居多,曾懇示封禁,并未刊碑。迨至同治年間,附近居民又在此偷行開鑿石塊,生莊居民亦復因此疾病死亡,生等邀會莊民理阻,時止。生等竊思:“石虎”系生莊來脈,有關民生。一經開鑿,闔莊不安,屢試屢驗。忽于今年十月間,又有在此開鑿石塊使用,莊民驚慌,雖經生等勸阻,誠恐日后互相效尤,莊眾受害無底。為此,公懇施恩,格外賞準,出示禁止,則生等闔莊無即叩乞之情到縣。據此,除此呈批示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附近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爾等務各遵照,不許赴該山“石虎”開鑿石塊,有傷風脈。尚有無知之徒偷行開鑿,許該紳耆人等指名呈究,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由此可知,虎頭石的管理權確為大史村無誤。解放后,此告示碑流落于村民手中,碑文由大史村黨支部老書記畢坤德親筆抄錄。2013年大史村整體搬遷后,此碑不知所蹤。
3.虎頭石的毀壞
盡管虎頭石的所有權與楊古村無關,但虎頭石的毀壞卻與楊古村有關。蒲松齡《九日與同人登虎頭石》小序中的“畢有豪士”當為楊古村的畢偁。《淄西畢氏世譜》記載:“偁,賦性則鷙。沖山虎頭石為邑西偉觀。一旦,糾石工碎其首,石髓流出如腦然,是歲為崇禎戊寅。旋遇難去。” [6]31崇禎戊寅即崇禎十一年(1638),事件發生年份僅比蒲松齡出生年份早兩年。
在大史村人的傳說中,還有縱火燒毀虎頭石的說法,因為虎頭石極為宏壯,即使畢偁召集石匠破壞,也只能損其皮毛。至于張、王兩位先生“后來虎頭石被采石者放炮炸毀,現殘跡尚存” [4]112之說也是不正確的,因為虎頭石在“崩塌”之后,所有巨石都裸露在山坡上,采石者要想得到完整有用的石料,不會放炮崩石。現今虎頭石殘存的人工采石痕跡(褉窩)即是證明。虎頭石到底是怎么損毀的,現已成為歷史之謎。
三、南山
蒲松齡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所作七言律詩《九日贈王憲侯》云:“蠟屐行穿落葉堆,攀緣石磴上高臺。白云滿地群羊臥,衰草連天野菊開。一點青中人共坐,十年望處客初來。主人曳下南山路,爛醉華堂踏月回。” [1]292
趙蔚芝先生箋注:這首七言律詩,是在重陽節登高贈給王憲侯的。詩中寫出了登山的經過,在山上見到的晚秋景物以及游山歸來宴飲致醉的情況。“群羊臥”,形容亂石。蘇軾《登云龍山》:“醉中走上黃茆岡,滿岡亂石如群羊。”“南山”,或指豹山。[1]292-293對于趙先生箋注中的“群羊臥,形容亂石”和“南山,或指豹山”兩處,筆者與趙先生有著不同的認識。
蒲松齡筆下的“群羊臥”不是指散落山坡的“亂石”,而是布列緊湊、相對集中的巨石群。符合這一情景的只有大史村南山(即龍舟山)的“虎頭石”。上文《九日與同人登虎頭石》已有“虎頭墮地摧山岡,齒牙崩臥如群羊”的詳細描述。筆者之一是大史村人,無數次登臨虎頭石,并多次拍照,對“崩塌”之后的虎頭石深有感觸:這些巨石一塊緊挨著一塊,“有規則”地靜臥在南山“虎頭石”北側,有如人工巧布,與蘇詩“滿岡亂石如群羊”所述不盡相同;也正因為眾多巨石“排列有序”,蒲松齡才在詩中發出“白云滿地群羊臥”的感慨。筆者之一拙作《山村的記憶》以“群羊臥”的巨石作為封面配圖,看中的正是這些巨石獨一無二的排列特征,而反觀蒲松齡描寫豹山的諸多詩篇,沒有一處山石景點符合“群羊臥”的形態。
趙先生可能沒有訪過大史村南山的虎頭石,不知道實際狀況,因此用“南山,或指豹山”的模糊結論了之。凡文人對景物的描寫,大多以借景抒情為主,直接描寫實景的少之又少。明末淄西畢氏族人畢自寅《清明同友人游虎頭石》詩寫道:“風雨清明景倍新,鳴鳩花里喚游人。虎威仿佛生奇石,塔影依移轉法輪。興劇溪山泥不滑,盟堅詩酒味逾真。夭桃若為催芳節,可信儂行樂及春。” [3]833詩中真正展示虎頭石景觀的只有“虎威仿佛生奇石”一句,若非題目明確告知是游覽虎頭石,那些沒有親臨虎頭石的人還以為又在描寫豹山呢。蒲松齡《九日贈王憲侯》中“衰草連天野菊開”的詩句,當然是實景描寫,因為自虎頭石向東直至“蔓葫蘆頭”山峰處,是一片較為平坦的曠野,而且“蔓葫蘆頭”又成聳起之狀,深秋之際,荒草漫山遍野,金黃色的野菊點綴其間,登高遠眺,“衰草連天野菊開”之感慨油然而生。
綜上所述,蒲松齡《九日贈王憲侯》詩中的“南山”,當為今之沖山,即大史村的南山,并非豹山。
四、東山不是黌山
康熙五十三年(1714)重陽節,蒲松齡與本縣孫圣華、圣文兄弟,齊河許圣瑞以及本家兒孫等人游覽東山,寫有七言律詩《九日同孫圣華、圣文昆仲,齊河許圣瑞及兒孫登東山》,詩云:“登高童冠語紛紛,奇石滿山路不分。翳日豐林眠似鹿,連天翠黛亂如云。遙村堆綠煙千點,遠碧橫空雁一群。名教原非無樂地,何須載酒醉紅裙。” [1]501趙蔚芝先生注釋:“東山:黌山。在淄川縣城東北,故名。” [1]501趙先生認為詩中的東山便是黌山,這一觀點不準確。關于東山,《淄川縣志》對此有明確記載。
嘉靖《淄川縣志·封域志·山川》:“東山,在縣治東十里。一徑而入,漸行漸窎,有鵓鴿、狼虎諸崖,兔、懷諸峪,黃、路諸嶺,擦、石諸坡。轉折溪迥,時或流為小川,突出小泉。依岬傍巖有小莊,占高據勝有古寺,誠一佳境奧區也。雖天臺、桃源亦不是過,豈非淄川之鎖鑰也哉!” [3]23
萬歷《淄川縣志·山川》:“東山,在縣東十二里。每秋雨后,兔峪出泉,水勢湍急,西至馬家莊,南入般水。其山南北,盡縣之境。東折二十余里,至諸葛崖,始屬益都縣。” [3]129
乾隆《淄川縣志·輿地志·山川》:“東山,邑人遙望之總名也。縣東十二里,入谷有鵓鴣、狼虎諸崖,兔峪、槐峪、黃綠嶺、擦石坡、豆腐臺。夏秋雨后,兔峪輒出一泉,水勢湍急,西至馬家莊,南入般水,其山南北盡縣之境。正東轉折二十余里,至諸葛崖,始屬益都縣。中有狼虎崖,邑生宋遂曰:‘俗名,誤也,本名擒虎崖。予始祖鳴鐘者,兄弟七人曾擒虎于此,固名焉。識之。” [3]314
同時,乾隆《淄川縣志》也有黌山的記載:“黌山,縣東北十二里。山上有碧霞元君廟,山半有漢儒鄭康成祠,祠后有樓,為邑景之一。” [3]314
據此,蒲詩中的東山,一定不是黌山,而是蒲松齡所居村莊東邊群山的總稱。
再者,還有兩個例證。《九日同孫圣華、圣文昆仲,齊河許圣瑞及兒孫登東山》描述東山亂石堆積、山路難尋,登高遠望,群山如黛、村莊堆綠,一派蒼茫的景象。詩中的東山沒有廟宇等宏偉壯麗建筑,與黌山的景致大不相同。
七言絕句《聞淄東無雨》其一云:“霖雨不曾灑綠屏,黌山瞻祝總無靈。薄田拚少逢年望,賺得蕉窗一夜聽。” [1]369蒲松齡在詩中感嘆自己瞻拜黌山、祈求神靈降雨的愿望依然落空。趙先生在詩末注釋:“黌山,山名,在淄川城東北十里。據《太平寰宇記》:‘黌山,相傳鄭康成注《計》《書》,棲遲于此。今俗書為‘洪山。蒲氏故居在黌山下。” [1]369趙先生在此為黌山作了詳細注解,但他并沒有將黌山稱作東山,可見趙先生在此詩箋注中也不認為東山與黌山是同一座山。
五、張古玉皇閣
張永政、王一千先生《聊齋詩文中的淄西景物考(一)·玉皇閣秀入云端》在引用蒲松齡《登玉皇閣》詩后敘述:“蒲松齡《登玉皇閣》一詩,充分描述了古代廟宇‘玉皇閣這一古建筑群高大雄偉及周圍秀麗的自然景觀,表述了其登臨時的興奮心情。聊齋詩中還有與玉皇閣有關的《九日同邱行素兄弟、父子登豹山》之三,讀后,藍天白云,綠水青山赫然在目。” [4]109又描寫:“玉皇閣,位于城西五十里的王村鎮張古村東,距西鋪村東南里余,占地約十余畝,七進院落,建于明代,幾經擴建,規模頗大。” [4]109還敘述玉皇閣被毀壞過程:“1961年,嶺子煤礦修鐵路時占去該廟東北角,其它殿宇毀于‘文革,現僅存廟門三間,遺址瓦礫一片。” [4]110對于張、王二位先生的敘述,筆者并不完全贊成。
首先,不應把蒲松齡登臨豹山玉皇閣的內容引入此文。豹山玉皇閣與張古玉皇閣是兩處不同的廟宇。《玉皇閣秀入云端》全文圍繞張古玉皇閣的布局、規模、修建和毀壞過程等進行敘述,特別是對于殿宇、神像及周邊景物的描寫,具體生動,值得稱贊,但文中插入蒲松齡登臨豹山玉皇閣的感慨,容易使兩處玉皇閣混淆,讓不知兩處景點詳情的讀者不知所云,實為贅筆。
其次,張古“玉皇閣……建于明代”的說法也欠缺。宣統《淄川縣志·三續寺觀》載:“玉皇廟,在縣西五十里張家土鼓城東。規模宏敞,殿宇輝煌。舊有觀音殿、關帝廟。國初,添建玉皇閣。邑人唐夢賚有碑。后于閣西又建親王祠。” [3]943由此可知,明朝時此處僅有觀音廟和關帝廟,玉皇閣為清初增建。其實,張古玉皇閣為張古村庠生王之璠(字振鳧)等人在康熙十年(1671)開建,至康熙十七年(1678)因王之璠病重而停工(或竣工),至于后來增建曾王祠已經是光緒年間的事了,因此“玉皇閣建于明代”的說法不夠嚴謹。也就是說,張古玉皇閣在明朝只有觀音殿和關帝廟,至康熙年間增建玉皇閣、文昌閣、娃娃殿、土地廟、石大夫廟等殿宇,由此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玉皇閣建筑群。
再次,關于張古玉皇閣的毀壞過程。該文“1961年,嶺子煤礦修鐵路時占去該廟東北角,其它殿宇毀于‘文革”的說法很不準確。據張古村王樹恒老人回憶:玉皇閣的毀壞始于抗日戰爭,一是日本鬼子把廟內大樹幾乎伐光,二是1941年修筑王村到現王鋁礦(原址為糠山子)小鐵道,強行拆廟毀殿。新中國成立初期“破除迷信”,廟內神像多半毀壞,但是殿宇基本無損。50年代末,在廟內北部建有煉鐵爐,至今還有煉鐵時遺留的小坩堝碎片。修筑嶺子煤礦鐵路時,只是拆除了東院文昌閣的一部分。高級合作社至人民公社時期,張古村各社、隊修建辦公室、倉庫、豬圈、社場屋等所需石料、青磚、門窗、檁條等,大部分都從玉皇閣建筑群拆用。1963年張古大隊修建磚窯時,連地面上的鋪路石也全部起走,僅留下玉皇閣大門(當地老百姓稱呼“山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拆卸“山門”石料時,參與拆卸的人發生傷病事故,被村民訛傳為得罪神靈,此后就無人敢拆了。至1966年前,玉皇閣建筑群除山門外,其它建筑物均被徹底拆毀。現在玉皇閣這座大門已被列為淄博市周村區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記文物。
六、豹山之豹巖觀、清夢樓
豹山上的豹巖觀等建筑群是淄西的一大勝景。蒲松齡在西鋪期間,與鞏家塢邱氏、西鋪畢氏等父子兄弟多次游覽豹山,留下了《豹山》《九日登豹山》《三月十九日與同邱行素喬梓、畢萊仲兄弟等豹山看桃花》《九日同邱行素兄弟、父子登豹山》《九日贈九如昆仲》等優美詩篇。張、王二位先生《聊齋詩文中的淄西景物考(一)·吟詩會友話豹山》寫道:“山上建有魁星樓、文昌閣、九圣廟、豹巖道祠等,廟宇、道觀多處,頗具規模。明萬歷六年,里人王教、王政、王敬等捐資又修建了圣母殿、地藏王殿。”“廟南不遠處便是蒲松齡好友邱行素的花園別墅清夢樓”。[4]110-111此記述對豹巖觀等建筑的記載極為簡略,對修建人及景觀位置僅限于“記”而疏于“考”。筆者根據淄西邱氏后人、王村鎮尹家莊邱洪昌先生所藏《邱氏宗譜》和《魁星樓記》,對文中涉及的景物給予補證。
《邱氏宗譜》記載:“(八世)秉忠,字厚山。公長厚好善,傾資修豹山諸廟。” [7]138又據邱啟運(字振聲,歲貢生。十三世)所撰《魁星樓記》記載:“豹山玉皇宮,原吾太高祖厚山公創建,供香火處也。殿成,荊石先伯祖(邱璐,字荊石,乙未進士。十一世)遂以獲科名,登進士。”由此可知,豹山玉皇宮諸廟宇由鞏家塢人邱秉忠創修,是豹巖觀建筑群中最早建成的殿宇。邱璐是邱秉忠曾孫,生于萬歷四十八年(1620),三十六歲時中順治乙未(1655年)科進士,此時至修建玉皇宮應在百年左右,據此推斷玉皇宮應在隆慶年間(1567—1572)或許更早時間修建。
《吟詩會友話豹山》記載:“明萬歷六年,里人王教、王政、王敬等捐資又修建了圣母殿、地藏王殿。”據《王村鎮志》記載:“明萬歷十六年(1588),王政、王敬、王教三兄弟捐資修建圣母殿,萬歷二十二年(1594)又捐資修建地藏菩薩寶洞(即地藏王殿)。” [8]95《吟詩會友話豹山》所言“萬歷六年”,或為筆誤。圣母殿、地藏王殿先后分別建成是不爭之事,不能混為一談。
《邱氏宗譜》記載:“(十二世)希潛,字行素,號龍崖。己巳歲貢生。善引誘,樂裁成,構清夢樓于豹山之陽,作讀書處。疏泉鑿池,栽花植柳,時與同人并兄弟子侄輩飲賦其間。縣乘稱文學焉。” [7]139由此可知,清夢樓在豹山玉皇宮南面,即豹山南麓,不屬于豹巖觀建筑群。邱希潛所建清夢樓,成為他和蒲松齡等文人聚會最多的地方之一。
《魁星樓記》又載:“于是宜素先叔父重修諸殿時,特建文昌閣于山之極巔,蓋以此為文星聚會之區,而扶輿磅礴之氣,有以攝之而益厚。”文昌閣位于“山之極巔”,即豹山山脊上,位置在玉皇宮以南,清夢樓之北,由邱啟運的叔父邱緒圣(字宜素,十二世)在重修豹山諸殿時特建。
《魁星樓記》還載:“后愚兄弟從游于此,先叔(邱緒圣)每顧而謂曰:‘文昌、魁星,理以相配。余今既建此閣矣,汝輩異日有能增以魁星樓者乎?是吾志也。以故辛亥冬,舍弟啟萃(字協萬,號豹陽,十三世)不量己力之淺薄,奮然以建樓為己任。又幸附近眾君子樂與為善,各助資財,不兩月而樓成。于斯時也,登峰巒之聳萃,倍興云路之思;觀樓閣之凌霄,益奮鵬程之志,則接諸先人而發跡者。”由此可知,豹山魁星樓是應邱緒圣以“文昌、魁星,理應相配”的囑托,由邱啟萃在“附近眾君子”的鼎力支持下,于雍正九年辛亥(1731)興建,次年建成,并為之立碑紀念。
豹巖觀依山而建,自下而上,依次可分為下、中、上三院。下院內東有九圣廟,西為地藏王殿(萬歷十六年建),中間步行道兩側有鐘鼓樓。中院內西為圣母殿(萬歷二十八年建),東有關帝廟,中間為邱秉忠所建玉皇宮(或為隆慶年間建)。上院分東、西兩院,西院內北有王母殿,南為邱緒圣所建文昌閣;東院內主建筑為豹巖道祠,門楣匾額“豹巖道祠”今清晰可見。文昌閣位于“山之極巔”處,邱啟萃于雍正九年所建魁星樓,也在距此不遠的山脊處。另外,邱希潛所建花園別墅清夢樓,位于豹山之陽,即豹巖觀建筑群南面的山坡上,不屬于豹巖觀建筑群。至此,蒲松齡游歷過的豹山豹巖觀、清夢樓諸景物的大體位置和建筑排列順序基本明確。
參考文獻:
[1]蒲松齡.聊齋詩集箋注[M].趙蔚芝,箋注.北京:中國出版社,2005.
[2]孫啟新,邵祺昌.聊齋詩詞中的淄西畢氏(續)[J].蒲松齡研究,2019,(2).
[3]陳漣遠,白相房.淄川縣志匯編[G].淄博市新聞出版局,2010.
[4]張永政,王一千.聊齋詩文中的淄西景物考(一)[J].蒲松齡研究,2002,(2).
[5]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志編纂委員會.周村區志[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2.
[6]畢撫遠.淄西畢氏世譜(十世重修世譜)[M].1922.
[7]李漢舉,王一千.族譜所見邱氏家族資料[J].蒲松齡研究,2008,(2).
[8]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王村鎮志編纂委員會.王村鎮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8.
(責任編輯:李漢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