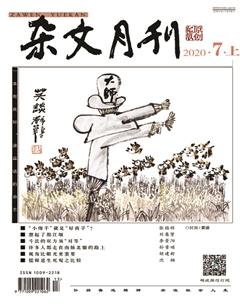清代嚴刑峻法的制度性缺陷
禾刀
《鐵齒銅牙紀曉嵐》中有這樣一個橋段:巡城御史海昇當街毀了權臣和珅家的馬車,和珅為圖報復,唆使海珅的妻舅貴寧指其殺妻。在紀曉嵐的保護周旋下,海昇被無罪釋放。
真相是,該案經刑部、都察院和戶部三次驗尸,最終坐實海昇殺妻事實,海昇按律被擬為絞監候。而那個銀屏上人見人愛的紀曉嵐,因暗中幫襯內閣和軍機兩個中樞的首席大臣阿桂被乾隆痛斥為“無用腐儒”。
專業研究清代制度史、政治史的北大博士鄭小悠,此前因推出《年羹堯之死》一書而頗受好評。本書中,鄭小悠重現了雍正末年麻城涂如松妻子失蹤案,道光年間遂寧諱良誣盜案,乾隆年間海昇殺妻案,嘉慶年間知縣李毓昌被殺案、徐文誥京控案和直隸遲孫氏京控案,道光年間宛平傅大唆使毆打他人致死案、德清名門徐氏案,光緒年間河南鎮平王樹文頂兇案等九件大案,探討了清代法律制度中刑訊逼供、諱盜誣良、辦人情案等弊病。
要說,九起大案一開始便漏洞百出,參與驗尸的仵作,審案的官員等諸多人士,無一不心知肚明。連皇帝這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局外人”閱完案卷后,也會因為這些案件太缺乏技術含量而勃然大怒。
然而,正如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所述,清代官場斷案向來有“四救四不救”之說,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一旦鍥入利益的考量,案情走勢就不再是真相。
“根據清代律例和處分條例,地方如果發生強盜案,地方大小官員又沒能在一定期限內將盜賊抓獲,就有‘疏防之罪,要省督撫題參,由吏部給予處分。”基層官員大都數年寒窗,好不容易才混了個功名,自然對頂戴花翎特別看重。避免處分的辦法就那么幾個,要么抓住強盜,要么逼報案者主動撤訴,更有甚者諱良誣盜。
諱良誣盜之所以屢成現實,這與當時過于看重口供不無關系。一些所謂的“能吏”,或者“自定供招,誘之伏法”;或者“故生枝節,刻意株連”,迫其接受;或者“以嚴刑”侍候,屈打成招……
需要指出一點的是,雖然大多數人情案的背后都有金錢交易,但也不盡然,比如前面所提到的海昇殺妻案。出于對位高權重阿桂大人的呵護,先后參與該案辦理的一干人士要么因為同阿桂熟絡,要么此前受其恩澤,要么畏其權勢,總之人未到案已定,早就在心底達成了某種默契,根本無須阿桂過問。“在許多驚天大案里,真正收受賄賂的官員并不多,大都是囿于親戚、同鄉、科舉同年、官場同僚等千絲萬縷的人情關系,而陷入其中。這是傳統中國人情社會的寫照”。
“在清代的法制體系中,一件地方的死刑案,其審轉必須要經縣、府、司、撫、刑部五個衙門”,實際在此之上還有終審,即皇帝。在道統與政統合一的清代,皇帝手執終審大權。只要控辯雙方未能達成一致,都有可能“申冤”至皇帝,這也是“京控”屢見不鮮的深層原因。“京控”的存在,表面上為百姓申冤提供了更多上訴可能,實則會大大加大社會成本,耗時耗力不說,對于社會的正面導向也極其有限。
雖然較明朝略有減輕,清朝依然推行嚴刑峻法,對審案作弊官員的處理也非常之重。盡管這樣,仍未能阻遏一些官員的鋌而走險,究其原因,不是他們不怕死,而是律法早就讓渡于“四救四不救”這樣的潛規則。潛規則的背后,本質上還是對權力合法運行缺乏合理的制度設計,比如對“疏防”之罪的認定明顯過于機械。另一方面,在上訴問題上,案件一旦被“上控”或者“京控”,原來審理的地方官員因此可能背上“失察”之罪一同被告,這必定會加大案件審判的阻力。至于仵作、禁卒、書吏等底層腐敗,根本原因在于編制人員過少、薪酬過低,以及監管不力。
制度性缺陷,實際就是違法犯罪的沃土,鄭小悠筆下的這些冤案錯案,本質上是這片“沃土”上結的果,雖然昭雪,但無法根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