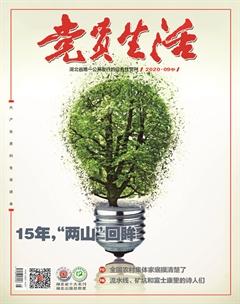“延安五老”的崇高風范
孟蘭英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駐于延安時,中央領導和全體機關干部將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黨員尊稱為“延安五老”,他們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畢生精力,新中國成立后又投身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之中。
“延安五老”是當之無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會活動家,他們以其各自獨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豐碑。
徐特立:“你們應該繼承的不是財產”
1927年夏秋之際,當中國革命陷入低潮時,徐特立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4年10月,徐老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紅軍中最年長的人。
1949年進城后,組織為徐老配備了專車,可他卻不大乘坐,經常是步行外出,有時還乘坐公共汽車。為這事,警衛員有些意見,牢騷很快就傳到他耳朵里。有次晚飯后,他問警衛員:“你知道這汽油是從哪兒來的?進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錢?”警衛員無以對答。
徐老耐心地告訴他:“我們國家剛解放不久,汽油要靠外國進口,我們進一次城來回的汽油錢,就等于你家一個月的收入。現在群眾生活還很困難,我們怎能隨便增加國家開支,加重人民負擔呢?要是我們干部與群眾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眾是會有意見的!”徐老又接著說:“少坐車,多走路,既可以鍛煉身體,又能為國家節約開支,同時還能密切聯系群眾。”警衛員心中豁然開朗。
1968年11月,在彌留之際,徐老把多年的積蓄交給了組織。他對孩子們說:“你們應該繼承的不是我的財產,而要繼承老一輩的革命精神。”
吳玉章:“我們共產黨人沒有私有財產”
“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這段毛主席語錄,出自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為吳老補辦的60壽辰慶祝會。毛澤東當時特別指出:“我們的吳玉章老同志就是這樣一個幾十年如一日的人。”
1947年2月27日深夜,國民黨軍警百余人包圍了中共駐重慶聯絡處,吳老聞訊披衣急起,正氣凜然地對國民黨軍警說:“你們半夜三更來此胡鬧,簡直無理至極,你們絕對不能捕走我們一個同志!”之后幾天,吳老給同志們講革命故事,激勵大家斗志。他表示,只要他活著,一定要使每一個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
3月8日,國民黨重慶警備司令和一個連長同吳老坐在一輛小汽車里,“護送”他到飛機場,乘飛機撤回延安。當吳老看到只備有2架飛機時表示堅決不走。后了解到另外幾架飛機確系氣候原因延遲一日可達,他才放心地上了飛機,第二天其余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1958年3月,吳老回家鄉四川榮縣視察工作時,聽說當時榮縣的教育還很落后,適齡兒童入學率很低,便指著自己家的住宅對陪同的縣委書記說:“我們共產黨人沒有私有財產,我這些房子就交給你們辦一所師范吧。”
謝覺哉:“蘭州地下黨不是反革命組織”
謝覺哉,1884年4月出生于湖南寧鄉。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時,已經50多歲的謝老,憑著頑強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輕人更多的困難,勝利到達陜北。長征中,謝老有一塊毛毯,露營時,他總是與徐特立一同蓋上。有時,由于雙方都想讓對方多蓋點兒,結果誰也沒有蓋好。這件事深深地感動了周圍的同志。
謝老晚年時,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權力,找理由想把蘭州地下黨組織打成“紅旗黨”的特務組織,欲將全體蘭州地下黨同志打成特務,逼著曾任蘭州辦事處黨代表的謝老寫材料。當時謝老已80多歲高齡,又重病在身。謝老對來者說:“我癱瘓了,寫不了材料。你們硬逼我寫,那我說,你們記,記完我左手簽字。”對方以為目的即將得逞,趕緊找來紙筆做記錄。只聽謝老斬釘截鐵地說:“蘭州地下黨不是反革命組織。那批地下黨員不是特務,而是好黨員。”來者得不到符合他們意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就這樣,謝老不顧個人安危保護了一大批同志。
董必武:“爭取當個好農民”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黨校校長,身為校長的他將自己的待遇定得很低,和教務主任共用一張桌子、一條板凳,合用一張硬板床。抗戰爆發后,為方便在武漢做統戰工作,他“奢侈”一把買了一塊懷表。這塊表又大又響,走得也不準,大家都叫它“火車表”,可董老卻樂觀地說:“反正快慢不超過半小時就行了。有會議時,表快了,我晚點去;慢了,我早點去,這樣不就調對了嗎?”
董老曾三次出國訪問,訪問期間,他精打細算,把節約下來的外匯都上交給了國家。這三筆錢共計2600多美元,在當時堪稱一筆巨款。
董老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性習于儉,儉以養廉”自勉,對子女也嚴格要求。1969年春,為響應黨的號召,董老堅決把自己的小兒子董良翮送到河北晉縣農村去鍛煉。在良翮下鄉前,董老題詞諄諄囑咐他:“到晉縣農村去,要好好學習毛澤東著作,努力勞動,爭取當個好農民。”良翮入黨后又擔任了村黨支部書記。董老馬上寫信告誡兒子:“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淺嘗輒止。”董老去世前對夫人何連芝說:“良翮是晉縣的人了,由晉縣組織上去安排,我們不必多操心了。”
林伯渠:“傷病員比我更需要它”
紅軍長征時,林伯渠任紅軍總供給部長,主要任務是負責籌糧籌款。
一天深夜,林老從衛生隊回來,見警衛員小黃正往暖瓶里灌開水。他道:“灌滿水后把它送到衛生隊,傷病員比我更需要它,別再把暖瓶拿回來了。”小黃知道這暖瓶的來歷,那是紅軍打遵義時繳獲的,小黃一直小心翼翼地保護著,長征途中,首長泡干糧、吃藥都得靠它。小黃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從命令,將暖瓶送到了衛生隊。
1944年春節,時任延安邊區主席的林伯渠發表了《我的生產節約計劃》一文,林老的生產節約計劃使大家贊嘆不已,一位外國記者也深受感動,懷著好奇、敬仰的心情來采訪林老。記者來到林老的住處,只見窯洞里只有一張炕,炕上的被子打滿了補丁,一張破舊的小方桌,桌邊放著幾把半舊的椅子。此時,林老坐在椅子上,埋頭縫補著一條舊褲子。他笑著對記者說:“中國有句俗話,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我這條褲子,才穿了三年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