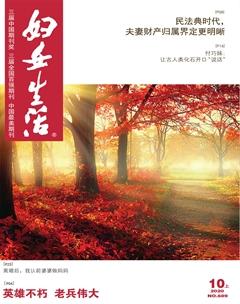科學家也可以是懂生活情趣的時尚女性
一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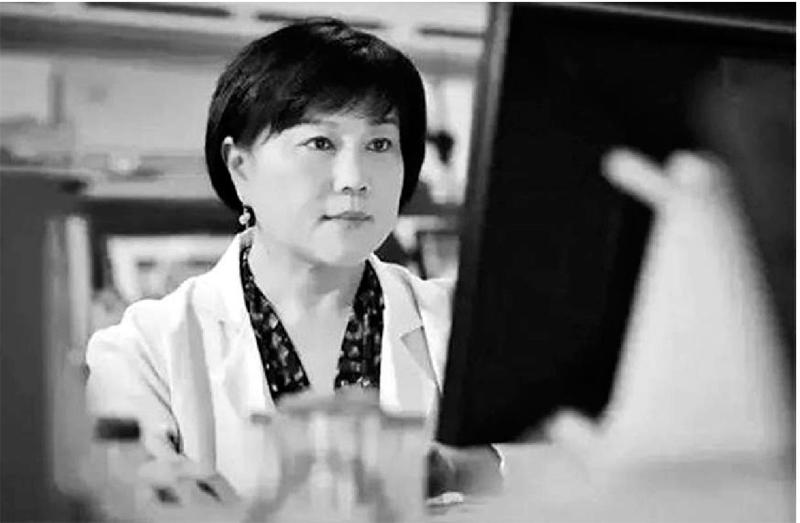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科研人員尤其是科學家,都是刻板、教條、固執、不修邊幅、不顧生活的。而我,希望破除外界對科學家的這種偏見——
從汽車修配廠的翻砂工半路出家進入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做科研
筆者:能談談您是怎么從事科研工作的嗎?
閻錫蘊(以下簡稱閻):我1958年生于河南開封,進入基礎生物學領域完全是半路出家。16歲那年,我到河南一家汽車配件廠當翻砂工,干的是很多人難以承受的重體力活。因吃苦耐勞,我年年獲得“勞模”稱號,短短4年就升為三級工。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入河南醫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中日友好醫院工作。為了提高我的科研能力,單位派我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實習。在那里,我遇到了時任所長貝時璋,人生從此改變。起初,我對理論完全不在行,只好從消毒、準備器械這些與醫學沾點邊的事情干起。不久,實驗室一位老師生病休假,貝時璋提議:“能不能讓閻錫蘊接棒?”就這樣,我戰戰兢兢地接下了這個任務。為了不把實驗做砸,我在老師們的鼓勵下,埋頭工作,有不懂的就向他們討教。最終,實驗達到了預期目標,我和老師們都很高興。
筆者:那后來是貝老勸您留在所里做研究的?
閻:是的。就是那一次做實驗,讓我發現做科研很有趣。這么多年過去了,現在我對那次實驗仍記憶猶新。我在生物物理所的實習期是一年,期滿后我對留在所里做研究還是回到醫院當醫生猶豫不決。最終讓我決定改行做科研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貝老對我說的一番話:“我看你是塊搞科研的料兒。你年齡還小,專業知識可以去補,況且醫學對生物物理研究也有幫助……”事實證明,我日后在科研上的幾次突破,都得益于醫學與生物物理學的交叉優勢。
筆者:留在生物物理所后,為強化專業知識,您下過不少功夫吧?
閻:留所后,我從基礎理論學起,從最簡單的實驗做起。后來,我先到北京大學進修,學了一年高級生化課程,又前往日本名古屋大學深造,學習分子生物學。與此同時,在生物物理所前輩的悉心指導下,我又系統地學習了細胞生物學。1989年,在貝老的實驗室中工作6年之后,我被公派赴德國海德堡大學、德國馬普細胞生物研究所做訪問學者,也算是出國留學吧。那時我女兒剛剛2歲,我在國外很想她,再加上語言不通和學術上的巨大差距,我經常難受得想哭。
科學設想被證實當然好,可有時實驗結果出乎意料,也會帶來意外發現,納米酶的發現就是這樣一個意外
筆者:您是納米酶的發現者,能說說發現的經過嗎?
閻:納米酶是我和團隊深耕10多年的新領域。對我而言,探索未知盡管困難重重,但有一種神奇的魅力,特別是當你的科學設想被證實的時候,那種窺破自然奧秘的喜悅感真的太好了;即使有時候實驗結果出乎意料,也會帶來意外發現,那種喜悅更加難以言說。納米酶的發現就是這樣一個意外。當年,我帶領團隊發現了一個腫瘤新靶點,在探索腫瘤診斷新方法時,遇到了一個奇怪的問題:磁納米粒子竟然與過氧化物酶底物發生了反應。起初,我們認為這可能是某種污染所致。可經過多次重復實驗,這種情況仍然無法避免。當時,我大膽設想:難道這個惰性的氧化鐵具有過氧化物酶的催化活性?隨后,我與團隊用一系列嚴謹的實驗證明了這個假說,接著將成果發表在《自然納米技術》上。很快,此文在全球業內引起轟動,英國皇家化學會刊發表綜述,認為這是酶學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此之前,沒人相信,作為惰性物質的無機納米材料會發生和酶一樣的反應。而這一項發現,可以說顛覆了科學界傳統意義上對“無機”與“有機”的認識。
筆者:“納米酶”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呢?
閻:納米酶是一種既有納米材料的獨特性能又有催化功能的模擬酶,具有催化效率高、穩定、經濟和可規模化制備的特點。我當時作為納米酶的發現者,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原始論文自2007年發表后已被引用1800余次,成為開拓納米酶研究新領域的奠基之作。在發現納米酶后,我和團隊成員并沒有發完文章就了事,而是將納米酶引入腫瘤生物學研究,將其用于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效果驚人。我還絞盡腦汁建立了納米酶活性檢測的標準體系,使納米酶應用研究標準化、可質控、可量化。目前,已有超過100種不同納米酶相繼被發現,納米酶研究已在30多個國家的300多個實驗室開展,在生物、醫學、農業、環境治理等多個領域展現出可喜的應用前景。不久的將來,納米酶將會為人類健康、能源再生及環境保護等做出更多貢獻。國際專家普遍認為,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中國納米酶研究引領全球。
筆者:您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就,肯定獲得了不少榮譽吧?
閻:是的。我在生物物理學領域已探索了30多年,成就頗豐,也收獲了很多榮譽:2012年,納米酶研究入選年度中國十大科學進展。2015年,納米酶的應用研究獲Atlas國際獎,同年我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接著,亞洲生物物理聯盟換屆,我有幸被推選為亞洲生物物理聯盟主席,成為該組織有史以來首位女主席。2017年,我獲得首屆全國創新爭先獎。還相繼當選全國第十二屆、第十三屆政協委員。2019年,我榮膺“全國三八紅旗手標兵”稱號……其實,我是生活在了一個好時代,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得到了國家如此多的榮譽。以后,我唯有更加努力,才能不辜負這些榮譽。
工作和生活從來都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女性科學家既可以很優秀,也可以很優雅
筆者:聽說您跳起舞來很瘋,可一旦工作起來,認真得讓學生們都感到有些可怕,是這樣嗎?
閻:確實是這樣。在生物物理所的新年聯歡會上,我們實驗室的保留節目是歡樂群舞。身為主任的我每次都不落下,無論是《江南style》《小蘋果》,還是《燃燒我的卡路里》,我都跳得激情四射,絲毫不輸年輕人。學生們都說:“閻老師跳起舞來很瘋!”可回到工作中,我的認真卻讓學生們有些害怕。平時開組會,從圖表的展示方式到單位的大小寫,我都嚴格按照發表文章的標準要求學生。學生的畢業論文,修改十幾遍是常事,多的甚至達到20遍。有一位博士生很努力,但4年間換了5個課題仍一無所獲。有人勸我降低一下標準,我總是搖頭:博士的標準不能降低。只有嚴格要求,才是真正對學生負責,這是貝老留給我的優良學風。至今我仍然感激貝老當年對我的指引,也一直保持著他所塑造的研究所的學術基調。由于我嚴格要求,我的學生在國內外科技界頻頻獲得各種學術獎項。
筆者:您常說當科學家并不意味著要放棄生活中的美好,是這樣嗎?
閻:不錯。人人都愛美,當科學家并不意味著要放棄生活中的美好。我過去不注重服飾,對生活也比較馬虎。2003年,我參加一次全國女科學家大會,看到不少同行不僅工作出色,而且著裝得體,光彩照人,我眼睛為之一亮,才意識到,原來女科學家也能如此美麗。從那以后,我開始認真打理自己。有一次,一個著名媒體人采訪我,說我“一絲不亂的淺褐色短發,合體的中式服裝,精致的耳墜,淡淡的妝容,舉止優雅,年近六旬與常人想象中的女科學家有些不同”,我很高興。
說到這里我非常感謝我的愛人和女兒,他們給了我一個溫暖的家。愛人經常夸我不僅是一位優秀的女科學家,還是一位賢惠、懂得生活情趣的時尚女性。每當換季時,我都會擠出時間和愛人、女兒一起逛商場挑衣服。在男裝柜臺,我和女兒爭著替愛人挑選衣服;在女裝柜臺,愛人又會忙著為我和女兒挑選服裝。搭配服飾也成了我們一家三口的幸福時光。我時常感慨:“工作和生活從來都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女性科學家既可以很優秀,也可以很優雅。”為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我還專門在中科院組織了“女性與生物物理之美”系列講座,為女科技工作者營造家一樣的互助氛圍,讓大家共同出彩。
筆者:都說您是一位“三熱愛”科學家,能具體說說嗎?
閻:在我的辦公室里,獎狀、獎杯數不勝數,但我覺得,中科院“五好家庭”紀念杯和全國婦聯頒發的“最美家庭”獎杯,才是最珍貴的。愛科學、愛生活、愛美麗,是我心中的“三熱愛”。在中國,人們一直認為,科研人員尤其是科學家,都是刻板、教條、固執、呆板、不修邊幅、不顧生活的。我希望破除外界對科學家的這種偏見。所以,在公眾面前,我著淡妝,戴耳飾,妝容得體,身姿優雅。我喜歡明亮的服飾,說話直爽,感染力十足;我還會和學生一起跳舞,為愛人做生日蛋糕……在學生眼中,我愛美麗、有智慧又懂生活情趣。其實,我也想告訴他們,搞科研固然有枯燥、艱辛的一面,但不要忘記,科學研究也是快樂的旅程,是一項有趣的工作。像大多數科研人員一樣,我也非常忙。為此,我練就了一套高效的時間管理法。在家中,我雙手很少閑著,看到家務順手就做了;沒時間去健身,我就見縫插針,在灶臺旁、辦公室,用自創的健身操放松身心、鍛煉身體……下廚烹飪,甚至掃地、擦桌子在我看來都是健身。我還有讓家務活變得有趣的小竅門——創造性勞動。比如切西瓜,我把它切成西瓜船,這樣干起來有趣,看起來賞心悅目,吃起來也感覺更爽口。
2019年6月9日和9月17日,我應邀赴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演講,一些老教授看到我都很驚訝:“閻老師,你也六十多歲的人了,怎么保養得這么好?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呀!作為一名科研人員,真難得!”我說我平時雖然忙,可對生活還是蠻講究的。咱搞科研、做學問的也要講生活情趣,追求生活品位。老教授們聽了頻頻點頭。我以《在科學中尋找人生意蘊》為題,圍繞從零開始、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極致、探索科學奧秘、做“三熱愛”科學家等,講述了自己的工作體驗、科研經歷和人生感悟,臺下數千名師生不停地鼓掌……
〔編輯: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