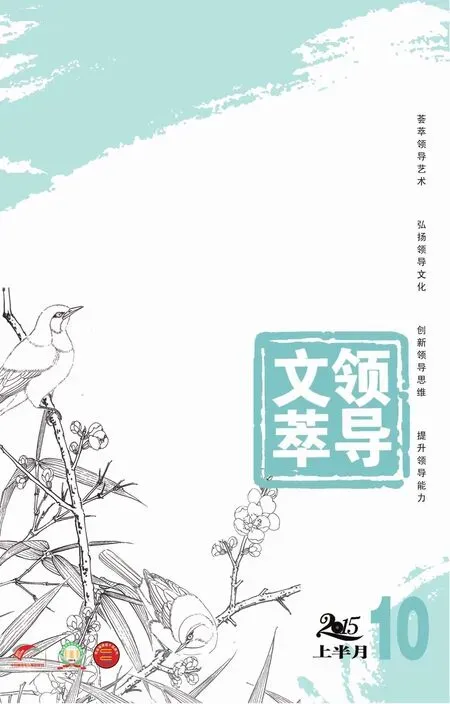外媒:中國在紅海地區不斷加強軍事存在
喬爾·伍思諾 劉洋 畢忠安
2017年,中國在吉布提正式建立了軍事基地。對于從未在外國領土建立過基地的中國軍隊來說,這不僅是重要的“第一步”,而且還是中國在紅海地區逐漸擴大軍事存在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中國的目標
中國在紅海地區不斷擴大的軍事規模推進了三大目標:支持中國在特定國家實現更大經濟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標;通過打擊海盜活動和監視美國的軍事行動,確保對中國貿易至關重要地區的海岸線安全;獲得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應用的實施遠征地面和海上作戰方面的經驗。
支持實現更廣泛的經濟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標? 北京的優先目標之一是保持原油供應。2017年,5個紅海地區國家為中國提供了大約22%的石油進口量,位居榜首的是沙特(銷售額為205億美元)和阿曼(銷售額為124億美元)。因此,該地區已經成為中國在許多不同合作伙伴中實現石油進口多元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中國在多個國家也有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利益,最明顯的是沙特、埃塞俄比亞和埃及。2017年,中國對這3個國家的出口總額超過300億美元,這3個國家都與中國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中國軍隊的一些活動提升了中國在東道國的公共外交能力。盡管與中國的石油利益沒有直接關系,但通過駐扎蘇丹和南蘇丹的維和人員對東道國基礎設施進行建設和修復,以及提供醫療服務,中國軍隊對中國的“軟實力”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類活動不僅可以消除人們對中國在該地區的負面印象,而且還提供了一個論據,說明北京方面可以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從而減輕人們對中國崛起的擔憂。
維護海上安全利益? 在保護穿越紅海的海上交通安全方面,北京有兩個基本利益。較小的利益是確保原油通過蘇伊士運河和曼德海峽順暢運輸。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石油進口“要沖”被關閉,都將使中國石油進口面臨風險,從而可能需要尋求其他“渠道”進行替代。然而,與霍爾木茲海峽或馬六甲海峽的中斷相比,這種影響微不足道,原因是全球石油供應和中國進口的大部分石油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運輸。中國更大的利益在于保護進出歐洲海上貿易通道的安全。2018年,中國與歐盟的貨物貿易總額超過5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通過紅海運輸。因此,紅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環也就不足為奇了。
盡管海盜一直是中國海運最常見的威脅,但更嚴重(可能性較小)的威脅是,在未來的沖突中,美國可能封鎖中國的補給線。中國分析人士對美國海軍在包括紅海在內的多個地區封鎖中國貿易的能力表示擔憂。中國國防大學教授、海軍大校梁芳將蘇伊士運河和曼德海峽列為“美國想要控制的”16個全球海上“要沖”之一,這對中國的軍事和經濟活動構成了巨大威脅。此外,中國在吉布提建立基地的目的之一是,監視美國海軍在曼德海峽附近的軍事活動,這可能為中國軍隊提供機會,以考慮可能挫敗美國針對中國海運采取行動的方式。
獲得遠征作戰經驗? 中國軍隊在吉布提的經驗使中國對管理前沿基地的機制有了深刻的認識。這包括與東道國政府就部隊地位協定進行談判,與當地居民保持富有成效的相互關系,從當地公司獲得承包服務,并在現行法律和文化規范的范圍內進行運作等。要想在這些領域取得成功,中國軍隊內部就必須具備足夠的涉及外國領域的專業知識,并在軍隊與包括外交部和中國大使館在內的其他有關行為體之間進行有效協調。
吉布提的經驗還需要中國軍隊學習如何安全管理與外國軍隊之間的關系,比如消除空中軍事交通管制沖突。由于美軍駐扎的萊蒙尼爾基地與其他軍事基地相距不到16千米,因此吉布提也為中國軍隊提供了一個觀察了解其他國家軍隊如何計劃和執行前沿作戰行動的“有利位置”。
對美國的影響
有許多理由不能夸大中國當前和未來在紅海周邊部署軍隊的重要性。中國軍隊仍然是外圍安全軍事力量。就規模而言,與美國第五艦隊在巴林部署的十幾艘或更多水面艦艇和潛艇相比,中國派遣的3~4艘海軍艦艇相形見絀,更不用說沙特或埃及等規模更大的地區海軍的能力了。此外,對中國軍隊來說,吉布提的軍事基地雖然是一個重要的“第一”,但也只是吉布提境內的幾個外國軍事基地之一。
中國軍隊是否會陷入地區沖突也值得懷疑。其中一個原因是,當核心領土利益沒有受到威脅時,中國不愿訴諸武力。即使有聯合國的授權,也很難想象中國軍隊會被部署在索馬里那樣高度動蕩的環境中。更重要的是,由于需要與各方保持積極關系,北京在地區爭端中采取了中立立場。中國希望置身于地區沖突之外,這意味著北京方面可能會避免大量出售武器裝備,以免天平向某一方傾斜。
盡管中國軍隊在該地區的作用不應被夸大,但美國官員仍需要應對三個不斷演變的挑戰。首先是作戰安全問題。其中一些活動可能是為了保衛中國的基地(比如,試圖阻礙美國在其基地上空的軍事飛行),這些自衛行為若美方處理不當,可能導致事故升級為直接沖突。第二個挑戰是避免無意中對中國軍隊作戰能力的提升做出貢獻。毫無疑問,中國軍隊也在從觀察美國在吉布提及其周邊的行動中吸取教訓。雖然其中一些技能可能與非戰爭軍事行動最相關,但另外一些技能可能有助于進一步提升中國軍隊在其本土周邊的作戰能力。第三個問題是,作為安全伙伴,中國與該地區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在美中全球競爭不斷演變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影響力主要來自于其作為許多國家的頂級貿易和投資伙伴的地位,而作為軍事盟友和安全援助行動的“貢獻者”,美國仍然擁有重要的戰略優勢。然而,北京建立和發展更強大的戰略伙伴關系,可能削弱美國在安全領域的優勢。
盡管存在這些挑戰,但中美軍事合作在該地區的潛在價值不應被完全低估。正如美國負責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安全事務的前助理國防部長蘭德爾·施里弗在2017年與別人合著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與中國軍隊在亞洲以外的合作機會通常多于在亞洲內部的合作機會。與印度洋-太平洋地區不同的是,中國并不尋求消除美國在紅海地區的聯盟,也不存在與美國盟友產生沖突的領土或資源爭端,主要專注于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而非執行作戰或威懾等任務。北京和華盛頓在該地區也有一系列的共同利益,包括打擊非傳統安全威脅,避免可能威脅全球石油供應、危及紅海商業交通緊張局勢的大范圍升級等。雖然中國軍隊對地區安全所做的貢獻有限,但應予以鼓勵,并確定富有成效的合作途徑。
目前,中國軍隊在紅海地區的活動是獨一無二的:在其鄰國以外的其他地區,中國僅象征性地保留軍力而已。盡管軍力將繼續集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但隨著考慮加強在其他地區的軍事存在,中國軍隊在紅海地區獲得的經驗將非常實用。該研究表明,中國的這種軍事行為將涉及某些權衡。一方面,中國軍隊對非戰爭軍事行動的貢獻可能會增強地區穩定,并減輕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負擔。然而,對美方而言,不利的方面包括:中國軍隊有機會提高其戰備水平,有能力利用部署的部隊對美軍的行動進行監視或“制造麻煩”,以及地區國家對其與華盛頓的安全伙伴關系的重視程度可能降低。美國國防部在紅海地區處理這些權衡的方式包括降低風險和尋求合作,這可能會為美中兩國在其他戰區的軍事互動定下基調。
(摘自《裝甲坦克車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