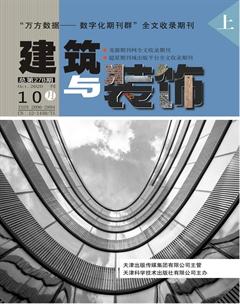論藏式碉樓的意向性現象學分析
周宏偉 趙建華
摘 要 “建筑現象學”的概念由來已久,其中以諾伯格-舒爾茨的理論著述為主要核心,但其理論從建筑學的角度來說較為晦澀、模糊,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是超越的、實項的。本文試圖回到現象學本身,從對藏式碉樓的體驗行為的角度入手,分析其意識行為的意向本質,從而分析藏式碉樓觀念的形成,進而為藏式建筑設計提供觀念上的設計指引。
關鍵詞 質性與質料;充盈;立義形式
建筑學與現象學的淵源頗深,其理論發源于現象學哲學家們的著作,其中最直接的理論來源如海德格爾(Heidegger)原載于《演講與論文集》中的《筑·居·思》和《人,詩意地棲居》、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知覺現象學》等,這些哲學理論的探討已經是在哲學研究的邊界徘徊,再往前邁出一步,便是對意識超越的,或者說是對非實項內容超越的深淵,而對這種超越之物的“懸擱”正是現象學的根基。挪威建筑理論家諾伯格-舒爾茨(C.Norberg-Schulz)的基本思想正是從海德格爾這個短篇(《筑·居·思》)中獲得的,在《場所精神》(其稱之為走向建筑現象學的第一步)中,舒爾茨對場所及其本質的定義卻是超越的、實項的——我們所指的是由具有物質的本質、形態、質感及顏色的具體的物所組成的一個整體[1]。若以此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建筑現象學”必然與現象學相去甚遠,也就是說建筑現象學的理論根基不穩。本文將這些超越之物“懸擱”起來,從現象學的源頭,從意識的意向性的視域,來反思藏式碉樓的建筑設計和思考的過程。
1質性(Qualitaet)與質料(Materie)
現象學哲學的創始人胡塞爾(Husserl)認為行為的意向本質由質性和質料組成,質性是指那種使表象成為表象,使意愿成為意愿的東西;質料是指使具有相同質性而區分得開的東西[2]。而對于藏式碉樓的體驗行為來說,在整體外觀的配色上,墻面運用的紅色、白色,窗戶運用的黑色和綠色;在裝飾上,窗戶上的彩繪和雕刻、柱頭和橫梁以及大門的結構裝飾;在室內布置上,運用紅藍白的條形狀幔等等這些具體的客觀之物、具體的質料,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體驗行為的發生,人們通過對這些質料的把握,逐漸形成了關于藏式碉樓的意識,隨著時間的流逝,具體的質料慢慢地從意識中消退了。而摒棄了客觀表象的意識便是質性,質性在其內在本質中不具有與一個對象的聯系。我們不難發現,質料表現的具體方式可以隨時代的需求的不同而不同,而在質性得以表達出來之前,需要質料來作為載體[3]。這就為我們對藏式碉樓設計的演進提供了學理上的進路,在保證質性不變的前提下,我們對碉樓的色彩、裝飾等質料運用現代的設計手法進行演變甚至是局部刪減,我們得到的依然是具有藏式特色的建筑作品,甚至使得藏族人民具有歸屬感的建筑作品。
2充盈(Fuelle)
質性特質不具有補充的“質料”就無法存在,只是隨著質料的補充,與對象的聯系才得以進入到完整的意向體驗之中,并因此而進入到具體的意向體驗本身之中去[4]。這種運用現代設計手法進行設計的建筑,到目前為止還只能說是類似于一般藏式碉樓的現代建筑作品,或者說是新藏式碉樓。對這種現代建筑作品的行為體驗,所把握到的質料還不能讓人們形成認識上的更新。或是說,不同質料的一般藏式碉樓與新藏式碉樓,要想產生認識上的關聯,就需要充盈來實現。只有當一個意向在足夠的充盈中被直觀所證實時,真正的認識才成為可能[2]。也就是說,人們在體驗新藏式碉樓時,通過新質料把握到了新藏式碉樓的質性,再將新質性直觀為一般藏式碉樓的質性,如此反復直觀的過程,使得展示性的內容(充盈)與被展示的內容(質料)得到認同,人們對新藏式碉樓的認識真正成為對一般藏式碉樓的認識。如此這般,“不僅所以被展示的東西都已被意指,而且所有被意指的東西都得到了展示”[5],便得到了一個最完滿的充實的意向。
3立義形式
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認為,質料代表的是意識活動的內容,而意識活動的形式便是立義形式。立義形式分為符號性的、直觀性的、混雜性的。也就是說,人們對“藏式碉樓”這個意向的把握,可以是意識中的一種符號,比如人們在談論它的時候;也可以是一種直觀的把握,比如正在體驗它的時候;也可以是一邊體驗一邊回憶或認識的時候。但,無論是哪種形式,意向的質性是不會改變的,如若質性發生改變了,那么意向的質性也就改變了。這也為我們檢驗一棟“新藏式碉樓”是否是具有藏式特色的建筑作品,是否是使得藏族人民具有歸屬感的建筑作品,提供了意識上的方法。即無論是正在體驗的,還是回憶中的對這棟建筑的意識和認識,都是“藏式碉樓”這個意向的質性。否則,這棟“新藏式碉樓”便失去了它的靈魂,出現了失實的問題。
4結束語
今日的中國建筑是以何種程度喪失了與環境和歷史的關聯,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三流國際風格建筑的“翻版”[6]。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本文依托“藏式碉樓”這個意向,摒棄傳統“建筑現象學”超越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懸擱實項內容。以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對意向性的現象學分析為方法,從質性與質料、充盈、立義形式三個方面,來剖析人們在建筑更新中,對新舊藏式碉樓的重新認識的過程。試圖為日后的建筑設計提供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做一些理論上的探討。盡管本文所做這些探討的內容是受限的:限制在胡塞爾對客體化行為的研究范圍內;限制在胡塞爾對稱謂行為(表象)的分析上。如有所紕漏之處,還請各位前輩不吝指教。
參考文獻
[1] 諾伯格-舒爾茨.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7.
[2] 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41,50.
[3] 林雨萌.南京地區漢傳佛教寺院神圣與非均質空間營造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7.
[4] 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485.
[5] 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79.
[6] 托馬斯·史密特.建筑形式的邏輯概念[M].北京:北京科技大學出版社,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