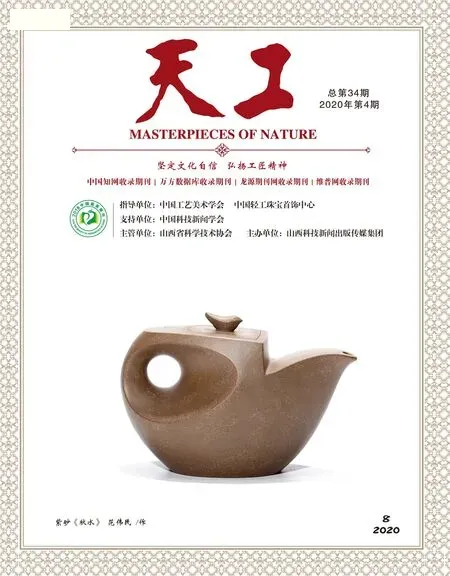淺談地域文化視野下壽山石雕藝術形式美
文 林 城
一件具有強烈藝術感染力的優秀作品,一定是在某種強烈情感的支撐下而產生的。而這情感大多數源于創作者所處的地域環境、文化以及當下的時代背景。
一、福州地域文化與壽山石雕刻藝術產生的背景
福州隸屬福建省,別稱“榕城”, 具有獨特的古城風貌,歷史上長期作為福建的政治中心,1986 年獲批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福州地區延續著開放博大、兼容并蓄等海洋文明顯著特征的地域人文底蘊,孕育出了閩都四大文化品牌:曇石山文化、船政文化、三坊七巷文化以及壽山石文化。三坊七巷被稱為半部中國近現代史,是福州的歷史之源、文化之根。曇石山文化遺址出土了福州早期的陶器,將福州歷史文化推進了近千年。船政文化孕育了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進思想,展現了近代中國先進科技、工業制造及西方經典文化翻譯傳播等豐碩成果。此外還有上下杭、朱紫坊等底蘊深厚的歷史文化街巷,以及林則徐、沈葆楨、嚴復、林旭、林覺民等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歷史名人。正是這樣深厚的文化積淀,為壽山石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和精神支撐,造就了歷代壽山石雕刻創作者們勇于創新、虛心好學、博采眾長的匠心精神。他們將美學思想與時代特征相結合,創作出了無數藝術佳作,彰顯了閩都獨特的地域文化魅力。
作為閩都四大文化品牌之一,壽山石雕刻藝術發展至今已有1500 多年的歷史,福州桃花山南朝墓中出土的“石豬甬”,是現今所發現的最早的壽山石雕刻作品,而藏于福州市博物館中一件壽山石雕作品《翁仲》,其雕刻形制與漢代玉雕翁仲風格一致,曾有專家推測為漢代之物。元明之際,王冕創造性地以軟石入印,柔而易攻、色質斑斕的壽山石理所當然地成為文人制印的首選材料。在數百年的發展中,壽山石雕刻藝人在傳統印璽的基礎上,融合了玉雕、石雕、木雕、竹雕等百家之長,充分發揮了壽山石自身的紋理、色質特性,創造了獨具特色的壽山石雕刻藝術。清代,高兆的《觀石錄》、毛奇齡的《后觀石錄》將壽山石推向了當時文化、藝術審美的浪尖,文人雅士、達官貴人爭相收藏。而壽山田黃石更因其有“福、壽、田”之名受到乾隆皇帝的青睞,進而把壽山石雕刻藝術推向了時代頂峰,由此也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壽山石雕刻藝術創作者,他們為當代壽山石雕刻藝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當代壽山石雕刻藝術的發展
壽山石雕刻藝術源于南朝,興于唐宋,盛于明清,復興于當代。在鼎盛時期形成了各種藝術流派爭奇斗艷的繁榮景象,或淳樸深厚、或精巧玲瓏,精品多被宮廷所收藏。
傳統壽山石雕刻藝術流派主要分為東門派與西門派兩大流派。東門派以圓雕見長, 鼻祖為清同治、光緒年間的林謙培。圓雕作品觀賞性極強,觀者可從不同角度看到工藝品的各個側面。它要求雕刻者從前、后、左、右、上、中、下全方位對石材進行雕刻。而西門派則以典雅著稱,其中又以“薄意”為其代表,鼻祖為西門外鳳尾村的潘玉茂,其弟子多集中在西門外鳳尾村一帶,故稱為“西門派”。壽山石“薄意”雕刻技法,是壽山石獨有的一門雕刻形式,其融書法、篆刻、繪畫于一體,以“重典雅、工精微、近畫理”深受世人喜愛。
在傳統“東門派”“西門派”之外,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壽山石界出現了一門“新興”創作流派——“學院派”。彼時中國文化藝術百業待興,恢復高考后一大批接受了當代美學教育的創作者從各類大中專美術院校畢業后,把自身所學融入傳統壽山石雕刻藝術中,在形式感與創作技法上都與傳統東、西門派有所區別。“學院派”中,王則堅是其中代表之一,他將現代美術理論和雕塑繪畫要素與壽山石雕藝術相結合,使長期以來以具象為主的壽山石雕藝術沖破傳統技法,體現了創新的理念。
而無論是“東門派” “西門派”還是“學院派”,隨著時代文化的發展,各流派之間的相互交流也日益密切和頻繁,在藝術表現上兼收并蓄。現如今壽山石雕已成為中國文化藝術中高雅文化的代表,以其獨特魅力吸引了國內外眾多愛石、玩石、賞石、藏石人士,在玩石界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
作為傳統壽山石雕刻藝術傳承中的一員,筆者自幼跟隨祖父林發述大師學習壽山石雕刻技藝,繼承家學,而后又得陳益晶大師悉心指導,專攻壽山石圓雕與浮雕技藝。林發述、陳益晶兩位均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也是當代“東門派”雕刻派系的代表人物,授徒多人,他們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經驗傳授于徒,為壽山石“東門派”的延續與壽山石雕文化的傳承和發揚做出了諸多貢獻,也成為筆者藝術生涯中影響最深的人。

《道法自然》

《酒中仙》

《航登彼岸》

《納福》
三、壽山石雕刻藝術的形式美
壽山石雕刻藝術成為福州的特色,因其獨特的內涵和藝術價值而聞名。創作者思想觀念的融入與創作題材的不斷變化,使藝術作品成為形式美的載體。例如,吉祥意識的出現,孕育出人們對美好幸福、吉祥平安的追求與向往,以至于此后的創作“圖必有意,意必吉祥”。例如,龍與鳳凰常用來象征祥瑞;鶴則象征長壽;竹子象征正直、堅韌挺拔,同時賦予節節高升的寓意;荷花象征堅韌不屈、潔身自好的品質。這便是壽山石雕藝術形式美的內在意蘊。
發展至今的壽山石雕刻技法成熟、多樣,主要包括圓雕、印紐雕、薄意雕、高浮雕、鑲嵌雕等技法,在創作形式的表現上也是多種多樣。作品整體講求布局端莊穩重、和諧統一,巧妙利用石材色彩的差異進行“巧色”處理,以增強作品藝術性,彰顯高雅情操。豐富多樣的雕刻技法,造就了壽山石雕藝術的形式,促使其精妙絕倫。
受林發述大師與陳益晶大師影響,筆者尤喜圓雕人物的創作。林發述大師對人物的神態、動作特點,甚至是發絲飄動的方位都十分注重,有極高的要求。也正因此,為筆者在此后的壽山石雕刻藝術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如何因材施藝,因色取巧,沒有足夠的藝術功底是很難駕馭的。作品《道法自然》將石材紅色部分處理為老者裸露在外的臉部、手部與玩耍中的孩童,使作品呈現出除裸露在外的部分外,里面還裹藏著更多與裸露部分相同材質的幻覺。在人物面部的表現上注重以目傳神,眉毛、眼睛等細節部分則多用點刻或短沖刀。處理須發與人物衣紋時,線條多以輕捷流暢為主,寥寥幾刀以表現人物衣飾的褶紋與須發飄動的自然之感。
作品《航登彼岸》將中國畫的寫意畫理融入雕刻中,在人物服飾上鐫刻裝飾花紋, 使作品出現禪、藝結合的美學格局,映襯出空靈靜幽、安寧悠遠的意境,令觀者如置身于山水林間,有高山行云流水下任遠隨緣、尋覓真我的超脫之感, 呈現“禪”的意境。
作為新時代的壽山石雕藝術工作者,我們肩負著時代的見證者與建設者的使命,任重道遠,應努力實現地域文化特色價值內涵的全面傳承與深度融入,抒寫壽山石藝術發展的新征程、繪制新畫卷,創作出更多技藝精湛、制作精良的新時代優秀作品,為壽山石雕藝術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