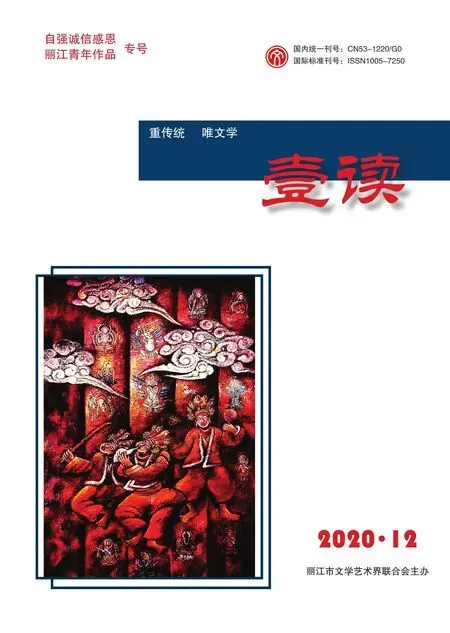又是一枕秋涼(組詩)
◆馬海
香格里拉
卓瑪轉身的時候,草綠了
植物長出一寸寸陽光
大地飲著露水浸泡的早茶
風是一把梳子,高原開始柔順
咀嚼時光的牦牛,目光
穿過古樸的木柵欄
靜立的馬匹,傾聽
昨夜星辰遺落路旁的一盞情歌
荒原的獨樹上,誰種下第一粒鳥鳴
佛陀雙手合十的縫隙里
烏鴉穿過吉祥的陽光
指尖,一朵凈界的云緩緩滑過
薄薄的流水,把村莊洗了又洗
山寨一角,顫音的野蜂
寫著一行袖珍的詩
高懸蜂巢的崖壁,巖畫斑斕
霧散,霧散
綠野上一只鷹馱著家園飛翔
巖壁上的鳴蟬
走進虎跳峽的人突變為千年啞巴,他們清楚
在翻卷的巨浪中,說什么都是多余。唯有
絕壁上數萬的蟬,那些小蟲,不肯罷休
伏身險境,一刻不息地嘶聲高叫
于是在巨大的洪水轟鳴聲中,始終
有另一種尖銳的聲音不絕于耳。仿佛
一群民間歌手,在與十萬鐵甲的吶喊對峙
游人忘情山水的同時
無法忽略那些蟬的鳴叫
我被浪花打濕睫毛,卻被鳴蟬打濕內心
在回程的路上,虎跳峽洪水的轟鳴漸漸停息
那些蟬,還在虎跳峽深處叫綠一個夏天
牦牛背上的風
藏地。香格里拉。秋日草甸。
陽光和雨水,同時到達。高地啊,
不是歲歲可以登臨。
臉龐,歲月的攀爬,步履,如胡須樣密。
虔誠,有如僧侶。掌上,有花,靜放如佛。
來了,不戴墨鏡,不著風衣和帽。任亂發,
隨風曳動。
走過濕地,有一份野馬的心情。
哦,牦牛。一個個高原的標點。沉默,隱忍,彪悍,
大地的斷章,在此鋪開。
牦牛就是不須吶喊的斗士,
一對尖銳的角,在呼嘯的高海拔上屹立。
逝去的青春,就要返程。我喝了一口雄心。
牦牛背上的風,來自藍天。從月亮那邊吹來。
我只有用赤裸的胸膛來裝,裝一壺風。
不佩戴藏刀,不喝烈酒,已經是男人。
狼毒花,在腳下。伸展腰,到天涯。
今晚,我不宿店,
等一個少女,騎著牦牛過來。
又是一枕秋涼
秋天,說來就來了
回老家的路被稻子的熟黃包裹
涼意梳理著我步入中年的心情
何時,這條路漸漸荒蕪
幾枚文字,怎么也碼不出故鄉的樣子
凌亂的草垛,堵住回鄉的路口
一年年在土地上尋求榮光的爸媽
蓄滿歲月之鏵的犁痕,笑容里
點著如月的豆和晚景的瓜
我用歉意編織的籃,無法裝下
因為有爸爸在,故園還是園
因為有媽媽在,老家還是家
只是爸媽給我一生的愛
我卻給他們孤獨的晚景
在我背離的這片故土上
面對說來就來的秋天
一生忙于收割的爸媽,毫無還手之力
午夜,一輛入城的馬車
月光在午夜慘白,如水流瀉
一地銀色河流。樹影,那水草
等待魚的貫入。工業的犬子
紛紛睡去,金屬的鼾聲漸起
農業的蟲鳴,仿佛失憶的人
在月光下苦苦尋找精神故鄉
這是午夜兩點,一輛馬車
一個十九世紀的闖入者
倉惶駛進城堡。踢踏之聲
濺在我腦上,夢被踏碎
我想到馬背的汗味,和車上的
一兩個酒甕,破落貴族的后裔
龜裂的油畫,他們隨著馬車
駛入一個不安的城市。我推窗
一陣蹄聲和轱轆,已遠去
滿地碾碎的影子,在如水的月光下
慘白,如一個失憶者的記憶
陳家院子
陳家院子,是民國遺留到今天的舊物
居住著鎮上的鰥寡孤獨
我在院外度過半饑半寒的童年
每天收集嵌進墻體的銅錢和瓷片
王謝堂前燕子,在百姓頭頂做窩
深宅不深曲巷太曲,拴著的老犬
吠一片草根的天空。防火墻的流線
舉起衰草,落些瑣碎的雀,念著民謠
我家四口從陳家院子遷出
已是三十多年,總有一些民國書聲
傳進我耳里,像是陳家院子遛出來的
一聲雀唱。我的文字,染指了那些舊
舊的鄉人,舊的燈,舊的院落
我的味蕾,徒增了一步荒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