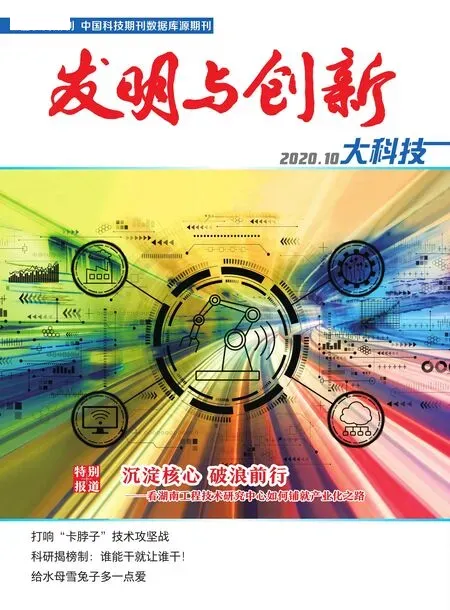王光義:長五、長七“雙料01指揮員”
文/溫才妃 徐斌如

王光義在和分系統指揮員討論(圖/新華社)
7月23日12時41分,長征五號遙四運載火箭點火發射,將我國第一顆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送入太空,中國由此邁出了行星探測的第一步。這是我國運載火箭首次沖出地球、飛向火星,也是首次真正意義上的多彈道宇航發射。
文昌航天發射場再次成為萬眾焦點。緊隨“五、四、三、二、一、點火”口令的,是巨大的轟隆聲、空氣的撕裂聲和觀眾的歡呼聲,火箭發動機噴出的尾焰在天空劃出了優美曲線。
這次任務的“01”指揮員王光義坐在測試發射大廳正中央,盡管一夜未眠,臉上帶著倦色的他還是難掩興奮之情。
王光義,我國第一名也是唯一的長征五號和長征七號兩型火箭的雙料“01”指揮員。1999年,他從北京理工大學自動控制系畢業后,20年如一日,扎根航天事業,書寫了精彩的人生華章。
和時間賽跑,搶回第一發射窗口
火箭專家、宇宙航行之父齊奧爾科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類不可能永遠被束縛在搖籃里。” 探測火星必須飛出地球,這是中國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突破口之一。
長征五號火箭已經具備將火星探測器送到地火轉移軌道的能力,但這樣的機會每26個月才有一回。因此,在發射窗口前沿實現“零窗口”發射將為“天問一號”節省更多燃料,可用于后續的探測工作。
“這是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第一次應用發射,一開始我們就是奔著發射窗口前沿和‘零窗口’發射目標去的。”王光義說道。
這是王光義第二次擔任新型火箭的首次應用型發射“01”指揮員。早在2017年4月20日的長征七號火箭首次應用發射——“天舟一號”任務中,他就成功實現了“零窗口”發射。而這次火星探測任務則遇到了更多挑戰——由于前續任務的調整,留給火箭活動發射平臺的恢復時間也跟著縮短,從48天直接壓縮至35天,在此基礎上還必須再壓縮出4天時間才能在第一窗口發射。
盡管要和時間賽跑,但王光義仍然堅持所有工作都要“穩”字當先,要搶回失去的時間,關鍵在于找出短線、制約因素和系統間的耦合關系。所有環節他都在一線全程跟進,因為他所需要在保證質量、不減流程的情況下,通過優化流程安排,實現再壓縮4天的目標。
“前期在研究長征五號活動發射平臺恢復計劃時,我們針對串行工作安排不合理、室外射后恢復工作時間偏長、應對惡劣天氣裕度不足這些問題,找到優化和解決方法。”王光義說。
擊破層層挑戰,見證白日焰火
本次火星探測任務,火箭于7月23日正午發射升空。
7月22日晚上11點,發射場的參試人員在短暫休息后進入各自崗位。0點26分,大多數分系統已經進入工作狀態。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新的一天,在夜色中開始了。
通宵工作是中午發射帶來的一個小挑戰,有部分崗位甚至需要連續36小時“作戰”。“我相信大家即使在夜里也會有很好的精神狀態,因為所有人都明白,自己在參與的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王光義說。事實上,他已經習慣在晚上工作,這次任務期間有接近80%的天數里,他都會在廠房或測試大廳加班。
整流罩內溫度上升過快則是中午發射帶來的又一個挑戰。塔架的回轉平臺打開后,火箭頂端的整流罩將完全暴露在直射的陽光下,特別是在射前整流罩空調斷開后,整流罩內的溫度將迅速上升,而對溫濕度非常敏感的火星探測器將面臨嚴峻考驗。
通過數學建模理論分析、梳理歷次任務空調保障情況,王光義帶領團隊提出3項措施:推遲整流罩內停止空調送風的時間;增大進風面積,提高換熱效率;采取雙機組空調保障,盡量降低空調停止送風前的初始溫度。經過模擬發射演練的驗證后,措施效果良好,團隊后續順利完成探測器環境保障的信心也得到了增強。
披星戴月之后,才能乘風破浪

7月23日,長征五號遙四運載火箭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升空( 新華社 郭程 攝)
王光義語速總是不自覺放快,他認為,這是因為每天要在不同的試驗現場奔走,也因為長時間的高負荷工作狀態讓腦袋始終保持著高速運轉。每天發射場的十幾個分系統都有大量的工作數據需要他進行判斷、決策,工作進展、問題隱患和處理方法在他電腦里9萬余字的記錄中清晰可查。這是他第一次擔任“01”指揮員時就有的習慣。
2016年6月25日,王光義在長征七號火箭測試發射大廳的正中央,下達了他人生中也是這座發射場里的第一個“點火”口令。他常說航天人的工作只有兩種狀態:執行任務和準備執行任務。在長征五號遙二火箭發射失利后,他和發射場都進入了漫長的“準備執行任務”狀態,這一準備,就是908天。
在成為“雙料01”之前,王光義面臨著從“長七”到“長五”指揮員的跨越轉型,這一挑戰是巨大的。不同的火箭設計思路、發動機類型、地面設備設施、崗位培訓方案,都是他的必修課。
為了把長征五號火箭的“脾性”摸得更準更透,王光義索性當起了“小學生”,先后三次奔赴火箭研制生產廠家,把零件部件、設備原理、應急處置從頭學了一遍。作為發射場系統的牽頭人,他需要讓自己知識和經驗的庫存富足,才夠格當其他人的“老師”。
長征五號遙四運載火箭點火發射,伴隨著倒數的口令,王光義意識到還沒到高興的時刻,他依然緊盯指揮大屏上火箭飛行的速度高度曲線,仔細辨聽調度傳來的測控跟蹤聲音。30多分鐘過去,跟蹤結果表明器箭分離正常,大廳內頃刻間掌聲如雷,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所有人都早已忘了一夜未眠。
此時,王光義向后靠上椅背,腦中緊繃了兩個多月的弦終于慢慢舒展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