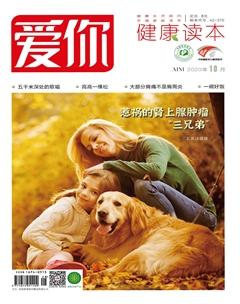螞蟻“拌飯”
【專欄作者簡介】
龔維忠,筆名璞石,湖南長沙人,湖南師范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曾任湖南師范大學(xué)出版科學(xué)研究所所長、湖南省期刊協(xié)會副會長、湖南省科技期刊編輯學(xué)會理事長、《科學(xué)啟蒙》雜志總編輯。
20世紀(jì)60年代初,連續(xù)幾年巨大的自然災(zāi)害,加之大國逼還外債,全國所有物質(zhì)實行憑票計劃供應(yīng)。為支持國家建設(shè),全民縮衣節(jié)食過上了苦日子。
此時期,剛過五十的父親積勞中風(fēng),只能在家自療,母親上班早出晚歸,兩位姐姐先后從衛(wèi)校畢業(yè)且都分到了外地工作。于是,正讀小學(xué)四年級的我與父親有一段長達近三年難以釋懷的密切生活交集。
那時,家中“常住人口”就是父母親與我。全家基本生活軌跡單調(diào)、重復(fù)。通常是每天傍晚母親下班買菜回來,急忙搞晚餐,同時把第二天三個人的中餐飯菜準(zhǔn)備妥當(dāng)。第二天清早,母親就帶著自己的那份中餐去上班了。中風(fēng)癱瘓、行動不便的父親只能眼巴巴地等著我,午時放學(xué)回家把飯菜加熱后,一起進餐。
那時的家用煤爐不僅天天需要干柴重新生火,而且時間稍長一點,煤炭燒盡就自然熄滅了,必須有人適時打理,疏通添加新煤才能保持爐火延續(xù)。
為了確保家中的煤爐中午與傍晚都能盡快達到煮飯炒菜的火候,盡管當(dāng)時父親坐臥活動的范圍僅在方“尺”之間,但是父親在上下午“盡心盡職”燒完兩壺開水后,還須及時通爐出灰,換上新炭,保證家中煤爐用時可旺。
白天時段,我要事先把煤爐、攪和好的濕煤以及燒水壺、熱水瓶等物,放置在父親的病榻旁。床邊的煤爐三九嚴(yán)寒尚可取暖,春暖花開還能勉強應(yīng)對,酷暑秋燥高溫?zé)荆P爐旁實際比在戶外烈日暴曬還難受難熬,猶如身在釜甑中。
當(dāng)時,中午一放學(xué),自己必須盡快拔腿跑回家,所以總是眼饞小伙伴們在放學(xué)途中能磨磨蹭蹭地玩耍,并還傻乎乎地以為自己是家中最“累”的人。現(xiàn)在回想起來,確實年少太幼稚懵懂了。無論是精力與體力,每天母親的付出是最大的,而時處中年的父親病中只能臥床和坐立,他內(nèi)心所承受的痛苦與壓力遠遠超過常人。
然說到物質(zhì)匱乏的60年代,就像講“天方夜譚”。當(dāng)時根本無從知曉冰箱為何物,夏秋兩季,家中隔天預(yù)留或剩余的飯菜,都裝在瓷碗內(nèi),放在竹籃中,設(shè)法置于陰涼通風(fēng)之處,有條件的則懸吊于清涼的水井里,一般大多吊掛在房屋中空氣流通的高處。
我們家通常是將飯菜籃掛于過道晾衣的竹竿上。有時天氣實在太熱,在吃過數(shù)次餿飯菜后,索性把剩飯仍留在煮飯鍋內(nèi),放在緊依水缸底邊的潮濕地面上。這樣,盡管天熱,第二天吃餿飯的次數(shù)倒還略有減少,但沒隔多長時間,又出現(xiàn)了意想不到的狀況。
記得在夏末秋初的一個中午放學(xué)后,我急忙跑回家中已是滿頭大汗,熟練完成的第一件事,就是從父親床邊將煤爐移至房外,接著火急火燎地?zé)岷酶粢共耍俚剿走叾孙堝仯l知打開鍋蓋,竟看到鍋內(nèi)黑壓壓地擠滿了“興奮異常”、不停爬動的大小螞蟻,我?guī)缀跬瑫r感覺到端鍋持蓋的兩手癢癢的,原來瞬間螞蟻就爬了上來。我這才注意到,就連黑黑的飯鍋外殼也早被密密麻麻的螞蟻大軍包圍占領(lǐng)了。
當(dāng)時,自己頭腦中的第一反應(yīng)是:“飯還能吃嗎?”父親看了后,立馬面帶焦慮地說:“能吃,能吃!倒入冷水,螞蟻就會爬出來的。”反復(fù)幾次實施父親傳授的“水攻”浸泡,蟻口奪食“戰(zhàn)術(shù)”,仍有不少“置生死于度外”的頑固分子硬是“與陣地共存亡”。
看來鍋內(nèi)米飯中的螞蟻用水是不可能“全殲”的,加之下午還要上課,時間不允許。于是,仍在父親的指導(dǎo)下,我只好把還黏附著不少螞蟻、被水浸泡得濕漉漉的米飯倒入炒菜鍋中加熱。
在不時地翻炒的過程中,米飯內(nèi)不斷地爬出一些殘余的螞蟻,可還沒有爬到鍋邊,很快又原路撤回了。在翻動米飯的同時,自己也不停地捻掉了不少“不知所措”的螞蟻。實在覺得根本無法清理干凈了,饑腸轆轆的父子倆也顧不了那么多,最后連同米飯和螞蟻一并吃了個精光。至今還依稀地記得,剛開始父親看到我皺著眉頭,極不情愿地扒著飯時,開朗地調(diào)侃說:“螞蟻‘拌飯比餿飯的味道好多了哦!”聽到父親的開導(dǎo),我也狼吞虎咽地很快就吃完了。
后來我們倆似乎都感覺到有點腹脹。當(dāng)然,也搞不清是蟻毒的“功效”,還是米飯被水泡發(fā)了的緣故。
自從有了第一次速吞螞蟻“拌飯”后,不知是螞蟻有記憶功能,或是螞蟻飯至少比餿飯容易咽下,接下來大凡高溫的日子,全家三口都有多次吃螞蟻“拌飯”的經(jīng)歷。其實,在那個年代,說出來也沒有人笑話,絕大多數(shù)家庭為填飽肚子都有這樣類似的心酸“囧”事。
璞石有話說
從前的苦日子早已離我們遠去。當(dāng)下全國人民邊抗疫情,邊加快建設(shè)祖國,我們是伴隨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一代老人,也是往事的見證者,對今天來之不易的生活感慨萬千,有責(zé)任訴說與告知年輕一代,且行且珍惜,為更強、更富、更美的祖國明天活出民族本真,干出強國真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