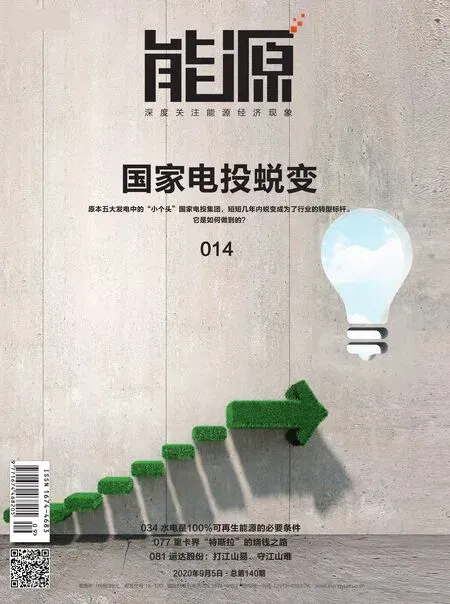找到油氣上游發展的內生動力,比盲目轉型更重要
文 | 秦峰
油氣勘探和開發依然有強勁的發展動力。個體行為永遠代表不了整個行業。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及蔓延之后,交通管制、人員出行及商業行為限制成為各國防控疫情的主要做法。這些措施的實施在有效控制病毒傳播的同時,對經濟運行及增長產也生了廣泛而深遠的負面影響,表現在各行各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具體到油氣勘探開發行業也是如此。
負面影響的路徑應該是商業行為及交通管制導致成品油需求銳減,使得煉廠開工率下降,終端和煉化市場的疲弱表現迅速通過市場和產業傳導機制反饋至上游油氣開采環節,使得油氣勘探開發表現出了蕭條。
勘探投資及油氣發現創歷史新低
咨詢公司雷斯塔的預計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疫情爆發期間全球上游油氣勘探開發投資被大幅度削減,整個年度投資同比降幅接近30%。2019年上游油氣開采投資在5000-6000億美元水平,維持了2018年以來的平穩增長態勢。
在立足未穩之際,2020年的疫情終止了這一良好局面。從演變的路徑看,近年全球油氣開采的重點正在向陸上深層、海洋油氣以及非常規油氣轉移。
2020年疫情的出現使得上述三個領域的發展均遭受重創,投資大幅下降。雷斯塔預計2020年全球海洋油氣投資下降15%,非常規油氣投資下降50%,油砂投資下降44%,陸上油氣投資下降23%。
由于投資不足,油氣發現自然差強人意。在此依然引用雷斯塔公司數據,2020年上半年全球油氣發現創近十年新低,其中常規油氣發現僅有49個,發現規模不及50億桶油當量,同比下降近50%。
上游拐點可能在1-2年后出現
鑒于油氣依然是全球主體能源,其需求尚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空間,因此當前的油氣投資萎縮現象肯定不會長期持續下去,出現投資增長拐點應該只是時間上的問題。這其中的關鍵點在于疫情何時得到有效防控。
上游復蘇拐點的最深層次影響因素應該是經濟形勢,這是基本面因素,是終極影響力量。具體的機理是:經濟形勢回暖拉動能源需求,終端市場能源需求增長通過傳導機制反饋至上游油氣開采領域,促使投資開始活躍。

目前關于近中期經濟形勢的判斷,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綜合分析上述兩家機構的預測結果可以發現,2020年世界經濟出現負增長幾成定局,IMF預測的2020全球經濟增長率為-4.9%,其中美國、歐盟、日韓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均出現負增長,僅有中國能夠保持1%的正增長。但是到了2021年,全球經濟形勢將明顯好轉,經濟增速大幅回彈,其中中國的GDP增速可能達到8.2%。
若按照這一預測判斷,油氣勘探開發行業回暖應該需要一到兩年的周期。持此觀點的主要理由是成品油以及化工產品需求在經濟回暖大形勢下肯定出現反彈和增長,煉廠開工率增長繼而拉動上游產業。
終端產品需求增長起初會消化掉之前經濟低迷時期市場過剩的庫存能源產品,這一時期油價可能還會保持相對低位。但當庫存產品被消化之后市場則會產生新的增量需求,而2020年投資下降導致的儲產量不足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原油供應短缺,繼而拉動油價上漲并刺激勘探開發投資增長。
考慮到國際原油價格變化對油氣開采行業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時滯”,油氣勘探開發投資復蘇拐點不會與油價的反彈同時出現,而是略有延后,理論上看可能發生的區間是2021-2022年。
部分公司弱化上游不代表行業衰落
疫情爆發以來,有歐洲背景的大型石油公司轉型發展理念非常引人注目。比較有代表性的公司非BP公司莫屬。
BP提出了2020年發展新戰略,計劃10年內每年在低碳領域投資約50億美元,10倍于現今的年度低碳投資數額,構建低碳技術的一體化業務組合。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能源,以及氫能和碳捕捉、利用與封存(CCUS)的早期市場地位。BP還宣布未來10年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氣日產量計劃將至少減少100萬桶油當量,相當于在2019年的水平上減少40%。
BP公司由一個地道的油氣公司向“去油氣化”公司轉型,力度可謂空前之大。同屬超大石油公司陣營的殼牌則要穩健許多。
殼牌的戰略重心依舊聚焦油氣,其戰略三大主題包括核心上游、領先轉型和新興電力,油氣依然是排在第一位的。通過這些戰略,殼牌旨在對其資產組合進行重整,其中核心上游業務包括深水、頁巖和常規油氣。
殼牌新興電力將著力打造滿足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的業務模式,以適應社會電氣化水平的提升,這是其傳統優勢項目。較之BP公司,殼牌的發展戰略似乎要相對穩健一些。
BP、殼牌等傳統油氣公司加大新能源業務發展力度的事實并不能作為油氣行業整體衰退的證據,從世界經濟形勢和能源行業自身發展規律看,油氣在人類的能源需求中主體地位還將長期保持。這兩家公司僅是行業中的少數,且其過去的發展戰略也曾出現過失誤,并非完美的戰略制定者化身,不能將其視為圣賢。
BP公司曾依靠激進的發展戰略攻城拔寨發展上游油氣業務,一度躍居世界跨國石油公司三甲之列,但多年前的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則讓其不堪重負。漏油事件看似偶然,實質是其激進投資擴張與股東回報雙重約束下的過度成本控制策略所致。
殼牌也曾出現過因為不重視油氣業務導致儲量捉襟見肘而靠儲量造假蒙蔽股東的丑聞。因此,評判公司的發展戰略時需要客觀冷靜和系統全面。疫情之后BP和殼牌新戰略一出臺就非常吸引眼球,看起來BP的戰略轉型似乎是其激進戰略轉型傳統的再現,其效果如何尚需時間檢驗。
什么支撐了油氣長期發展?
做好油氣業務依然是多數石油公司的首選。支撐油氣中長期需求的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
首先,發達國家的油氣需求會呈現兩極分化狀態,美國將長期維持油氣消費大國地位。美國號稱車輪上的國家,千人汽車擁有量在800輛水平,國內成品油價格低廉。美國擁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和下游加工產業,低廉的油氣供應成本會降低美國發展油氣替代能源的愿望。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國內就曾有發展電動汽車替代燃油汽車的呼聲和發展規劃。此種呼聲出現的背景更多的是出于保障美國的能源安全,當時美國的原油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但是隨著頁巖革命的興起,國內油氣供應充分,發展電動汽車的呼聲逐漸被弱化。
歐洲、日韓發展核能、可再生能源愿望迫切,表面上看是落實綠色低碳發展戰略,其背后與自身油氣資源供應不足有很大關系。日韓國內基本沒有油氣產量,全部依賴進口。近十年的歐洲油氣產量在不斷下降。
其次,油氣資源國本地消費是支撐油氣消費的重要力量。美國就是重要資源國之一。除了美國之外,中東、非洲、俄羅斯等地區是現在、乃至未來的油氣主產區,也一定是未來的重要油氣消費區。在資源富集區推廣油氣替代空間不能說沒有,但也不能說空間無限化。
再次,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還遠未結束,工業生產和城市建設的現實需要使得這些國家脫離不了為其提供基礎原料的石化工業的存在。交通方面最大的替代路徑就是發展電動汽車,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往往需要以本國發達的電力基礎設施做后盾。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并不具備支持其電氣化水平全面提升的條件。一系列數據顯示電氣化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經濟條件未達到相應的發達程度,推進電氣化未必能夠行得通。

最后,天然氣作為低碳化石能源,其潛力還遠未到達發揮殆盡的地步,甚或說剛剛開始。全球天然氣資源豐富,其開發程度落后于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遠距離輸送以及應用加工技術成熟,產業運行商業化程度高,不會輕易被替代。目前的非化石能源雖具有排放方面的優勢,但其在資源穩定性、儲能技術方面還有不少短板,產業鏈的完善和成熟程度較天然氣產業還有一定的差距。凡此種種事實說明,油氣需求在較長時期內依然有巨大的市場空間。只要有油氣需求,油氣勘探開發的發展空間就會存在。
油氣行業供給側改革至關重要
油氣需求長期存在是支撐油氣行業長期發展的終極動力,但并不等于說油氣行業就可以高枕無憂及無所作為。相反,在能源多元化的時代,只有時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心態,努力做好供給側改革,油氣行業方有可能保住自己的市場份額。
油氣行業如此,煤炭等行業也不例外。基于此判斷,后疫情時期油氣行業內生發展動力的培育至關重要。培育油氣行業自身內生發展動力,堅持“兩個必須”的發展理念是前提條件。
一是必須要有長期面對低油價的思想準備。接下來的幾年油價隨經濟形勢好轉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對油價的上漲空間不要抱有太高期望,這主要是因為非化石能源的能源替代效應的存在使得油價的漲幅不能隨心所欲。
二是必須時刻保持競爭的心態去應對能源轉型,做好應對新能源挑戰的思想準備。當前新能源發展的一大特點是技術進步的速度超出想象,太陽能、風能發電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已經出現大幅下降,甚至接近煤電。新能源發電主要設備生產成本因為規模經濟的出現而顯著下降,競爭力空前提升。再加上歐盟、日韓以及中國等新興大國的政策扶持,新能源競爭力還將表現出顯著的提升空間。
石油天然氣產業雖然技術成熟,商業化程度高,但面對新能源等后起之秀的競爭,沒有理由不居安思危。只有持續提升行業運行效率,依靠技術經濟性的提升方有可能穩定份額與市場。
面對低油價以及競爭的日益激烈,油氣行業保持競爭優勢的唯一出路就是變革自身傳統的發展模式以謀求更高的效率。油氣作為主體能源已持續多年,其產業運行模式在其參與者和決策者心目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優越性,繼而導致可能的惰性思維。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現實是發展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從發展趨勢看,打破企業之間的界限壁壘,推動生產要素之間強強聯合,通過共享、協作與聯合是實現油氣勘探開發行業儲產量增長,成本下降與效率提升的唯一的理論上的有效途徑。
目前這種實踐在全球多地已有不同形式的嘗試,比如在美國頁巖油氣和中國的勘探開發領域都有體現。由于全球的范圍內的油氣勘探開發在資源、政策和管理方式方面存在諸多差異性,實踐當中可能會有多種模式的合作形式,但其共享發展的核心理念應該是一致的。
全球能源轉型目標的實現,路徑的選擇取決于政策導向和行業自身的努力,轉型不會剝奪每一個能源行業發展的權利。具體到油氣勘探開發行業,面對后疫情時代的政策推動的電氣化競爭,面對政策鐘愛的可再生能源的迅猛發展,同時面對低油價的約束,內生發展動力的培育的的確確成當務之急,供給側改革成為生存發展大計,這是全球石油公司所共同面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