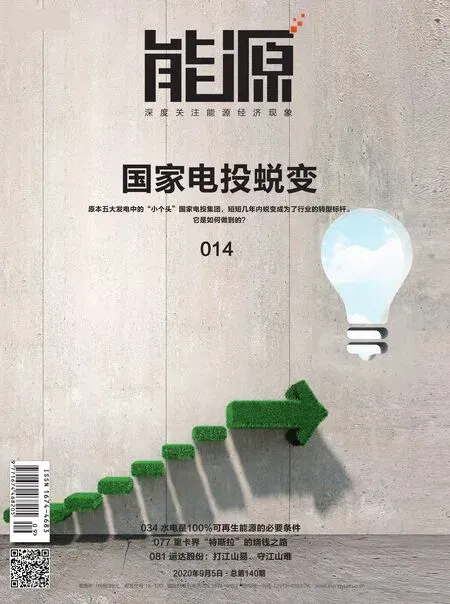國際能源通道恩仇錄石油王國沙特的序幕
文 | 陳湘球
誰也不會想到,沙特曾經是一個坐在“金礦”上的窮國家。
海灣石油公司的后臺老板安德魯·威廉·梅隆是一個天才商人。1882年他接過父親手中的銀行,在隨后30年里向匹茲堡各公司提供資金,開發鋁、鋼、石油、煤、焦炭、合成磨粉等各種工業產品,由此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金融和實業帝國,200年來長盛不衰。這個帝國的財富甚至超過了洛克菲勒和肯尼迪家族財富的總和。
安德魯·威廉·梅隆就是這個龐大金融和實業帝國的掌門人,他是梅隆家族的族長。雖然他沒有直接經營海灣石油公司,但他一直在資助海灣公司并使它成為一家綜合石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被他視作梅隆家族的家族企業,并對它表示直接的關心。在海灣石油公司進軍中東的事情上,梅隆是個關鍵人物。
安德魯·威廉·梅隆不僅僅是一個天才的商人,還是一個政治家。他是美國共和黨成員,1921年開始涉足政界,出任美國財政部長。一直到1932年,十一年間他擔任了三任總統的財務主管。
獨特的政治地位,讓他毫不費力就在委內瑞拉獲得了石油租借地。海灣石油公司在馬拉開波湖盆地的租借地很快就開發出了梅尼格蘭德油田,油田的石油產量上升很快。到1929年,海灣石油公司已是委內瑞拉第三大石油公司,它的石油產量占委內瑞拉總產量的27%。為了提煉委內瑞拉所產的比重較大的原油,它在荷屬西印度群島的庫拉索島上建了一座煉油廠,煉油產品向美國國內和中南美洲銷售。
已經沒有人知道,安德魯·威廉·梅隆是否早就預料到1931年的美國經濟危機和其國內嚴重的石油生產過剩,會讓油價狂跌,甚至預料到美國政府會對國內油田實行配額限制生產,并對委內瑞拉進口石油征收高額的進口稅。
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他買下了霍姆斯手中科威特和巴林的石油開采權,一定是將視野轉向了中東,旨在規避委內瑞拉石油風險。
巴林出油:打破中東石油平衡
顯然海灣石油公司不愿意放棄到手的生意,巴林島只不過是一個小島,霍姆斯手中還有沙特阿拉伯王國和科威特的石油開采權,這片無邊無際的疆土才是海灣石油公司構筑夢想的地方。
巴林的確落在紅線區域之內,而海灣石油公司作為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成員公司,也受“紅線協定”的約束。梅隆力圖勸說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其他幾位股東,和自己合伙干。但是在伊拉克石油公司中影響最大的是英國波斯石油公司,而其總地質師認為:巴林缺乏波斯和伊拉克這樣的地質構造,不會有油,因此英波公司反對去巴林。
在他沒能說服英國波斯石油公司主導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共同開發巴林油田之后,他把巴林特許權轉讓給了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收回了5萬美元。因為后者不是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成員公司,不受“紅線協定”的約束。但是,他留下了科威特的特許權,科威特不在“紅線協定”范圍內,梅隆還聘請霍姆斯作為他在科威特的代表,夯實了自己在這個地區的人脈。
加州標準石油公司帶著特立獨行的氣質進軍中東,1930年派遣地質學家弗雷德·A·戴維斯到島上考察。根據美國作家埃倫·沃爾德所著的《沙特公司——沙特阿拉伯與沙特阿美石油的上市之路》一書記載,戴維斯從明尼蘇達大學采礦工程專業畢業,一戰期間在美國陸軍的化學戰爭部門服役,1922年加入加州標準石油公司。
來到巴林,戴維斯首先選擇在巴林最高點開始鉆探,那是一座被阿拉伯人稱為煙霧山的橢圓形山峰。1931年10月16日,第一口井開鉆,八個月后,戴維斯打到了石油,每天1400桶的產量。盡管在所有人看來,這個產量過于平淡,但是巴林“煙霧山”山頂冒出的石油,似乎改變了形勢和整個阿拉伯沿海的前景。
科威特埃米爾·阿赫默德酋長為此心煩意亂,他對霍姆斯少校說,“當我注意到巴林的石油工程,而這里卻一無所有時,我心如刀割”。此時的科威特正處在嚴重的經濟艱難時期,大蕭條使科威特和其他酋長國的經濟陷于癱瘓。科威特作為隸屬于英國統治的海灣控制區中一個很小的國家,阿赫默德酋長當然知道英國皇家海軍的厲害。
此時的英波石油公司,正在波斯王國身陷痛苦的現實之中,世界正在改變,而且改變得很快。通過石油收入累積起來的大筆財富都集中在國王及其親信手中,而英國政府作為英波石油公司的大股東,無疑助長了波斯王國內部堅定的反英情緒和高昂的民族主義精神。
讓波斯人愈發不滿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難以把控油田的利潤。擁有特許權的英波石油公司在支付授權費時顯得相當狡猾而富于創造力。這些企業組建了一個由子公司構成的網絡,其目的是通過內部借貸形成“虧損”,以削減甚至完全抵消運營公司的賬面利潤,從而最終降低根據特許權協議的規定本應支付給波斯的授權費。
當地報紙憤怒地說道:“那些獲得準許開采波斯石油的外國人通過非法和不必要的關稅免除故意壓榨我國的財政收入”。1932年11月,在遭受授權費繳納數額劇減,以及一系列幫助英國人向德黑蘭隱瞞詳細財務數據的財務騙局之后,波斯國王宣布取消英波石油公司的特許權。波斯地區石油特許權的動搖,讓英波石油更加看重其在中東其他地區石油特許權的爭奪。
英美爭奪科威特開采權
巴林“煙霧山”山頂冒出的石油,更加堅定了英波石油公司對取得科威特石油開采權的信念。他們急忙給英國外交部寫信,表達了對科威特石油開采的濃厚興趣。而英國政府也想盡力維持它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和地位,它要保證英波石油公司擁有該地區內獨一無二的石油開采權。

英國政府向阿赫默德酋長轉達了英波石油公司的意愿,對英波公司的態度轉變沒有人比酋長本人更高興的了。他說:“是的,我現在有兩個投標人,從一個售主的觀點看來,這完全是有利的”。
丹尼爾·耶金的《石油風云》詳細描述了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圍繞著科威特石油開采權的博弈過程。根據這個全球知名的石油作家記錄,英國政府讓石油部去科威特調查海灣公司的出價,同時了解英波公司的新報價,基于此向埃米爾提供“意見”。
實際上英國政府是想完全主導科威特的石油開采。但因為兩份投標的檢查在倫敦拖而不決,霍姆斯和海灣公司——以及美國政府——開始懷疑起來,認為拖延是一個幫助英波公司勝出投標競爭的詭計。
沒有人知道,是歷史的選擇還是本人有意而為,曾經的財政部長,安德魯·威廉·梅隆,此時又成為了美國駐英國大使。在為海灣公司取得科威特石油開采權的問題上,他緊追不舍,雖然國務院不愿意顯得僅僅為了梅隆先生的個人利益而行動,但是美國政府確實在行動。到了1932年秋天,投標推薦的結果仍然遲遲未見分曉,梅隆失去了耐心,他決定置禮儀于不顧,直接向外交部追問這件事,這畢竟是家族的生意。
無論是英波公司還是海灣公司,他們深知對方堅強的決心和背后的強大力量。一方面英波公司看到美國的財富和其潛在的巨大政治影響,另一方面海灣公司看到英國在這個地區牢固樹立的地位與盤根錯節的關系。
英波公司董事長約翰·卡德曼感到詫異和苦惱,現在他完全相信必須同海灣公司訂立協定,他認為阿赫默德酋長的“兩個買主”無論如何要減少到一個。如果不這樣,酋長就能繼續從一個集團和另一個集團的爭斗中抬高價格,漁翁得利。所以英波公司保證它在投標競賽中絕對不致失敗的唯一辦法,就是同海灣公司建立合營企業。接著在兩個公司之間開始了緊張的談判和討論。到1933年12月協議最終達成,雙方同意建立一個新的合營企業,各占一半股權,取名科威特石油公司。
“王子復仇記”
在中東的石油歷史上,有一個人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他就是現代沙特阿拉伯國家的締造者,沙特阿拉伯王國的第一任國王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特。這位曾經的內志(現在的沙特阿拉伯納季德地區)王子,11歲開始流亡生活,親眼見證北部地區的拉希德家族奪取了他和他的臣民們賴以生存的利雅得。12歲經歷了一次伏擊,他躲在衛士身后親眼目睹了雙方短兵相接的血腥場面,手起刀落的人頭濺了他一臉鮮血,似乎這些鮮血一直在澆灌他心中的仇恨。
每每想到拉希德正統治著他的故土,他就疼痛難忍,他經常向父親懇求:“戰斗吧!趕走拉希德,沒有人比你更適合做利雅得的國王”。但是他的父親阿卜杜·拉赫曼總是在提醒他,穆罕默德·本·拉希德是阿拉伯地區最有勢力的人,他控制著北起敘利亞沙漠、南至阿布扎比空曠之地的聯合王國,所有的貝都因人部落在他的鐵拳面前都會顫抖。
但那場殘酷的戰斗和曾經一臉的鮮血卻一直在激勵著年輕的伊本·沙特承擔起收復失地、奪取權利的責任,甚至為此不計后果。
阿薩德在《通往麥加之路》一書中寫到:伊本·沙特召集了一些勇敢的貝都因人,組成了一個40人的敢死小分隊,他們像俠士一樣悄無聲息地沖出科威特,沒有旗幟,也沒有戰鼓和戰歌。這群人不走大路,晝伏夜行,終于在1902年1月14日深夜,來到利雅得城下隱蔽的山谷里扎營。
伊本·沙特從這40個人中挑出5個人,加上他自己,總共6人穿過城墻的裂隙,進入利雅得城中。他們把武器藏在斗篷下面,其他的人則留在城外接應。第二天,城堡的大門打開,拉希德走出來,被攜帶武器的保鏢和奴隸層層簇擁。一片歡呼聲中,潛伏的6個人從人群中一躍而起,猛地掏出匕首刺向敵人,伊本·沙特舉起標槍,投向了拉希德… …
短短一個小時之后,伊本·沙特成為了利雅得的領袖。這是現代阿拉伯半島上最富傳奇色彩的故事,被寫成長詩廣為傳頌。他翻越城墻和發起進攻的地方,今天已經成為沙特王國的著名旅游勝地。
在以后幾年中,一次出征接著一次出征,伊本·沙特把自己變成了阿拉伯中部公認的統治者。他還使自己成為易赫旺或兄弟會——非常熱誠的宗教戰士新運動——的領袖。這個運動在阿拉伯的迅速擴展,為伊本·沙特培養了一批忠誠的士兵和將領。在1913到1914年期間,他把阿拉伯東部,包括廣大而有人居住的哈薩綠洲在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此時的阿拉伯半島已經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西部漢志(現在的沙特阿拉伯希賈茲)地區被哈希姆家族統治著,北部地區則仍然是拉希德家族的疆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向奧斯曼土耳其宣戰。為了牽制奧斯曼帝國的軍隊,英國支持哈希姆家族,同時它也支持伊本·沙特以牽制奧斯曼帝國支持的拉希德家族。
1915年,伊本·沙特與英國簽訂《烏凱爾條約》,他統治的內志處于英國的保護之下。一戰結束后,失勢的拉希德家族試圖與哈希姆家族結盟,伊本·沙特決定出兵再次攻打拉希德家族。經過多年的戰爭,1924年9月,內志的軍隊向漢志發動進攻,10月攻克麥加。1925年12月,漢志最后一個據點吉達陷落。
麥加和麥地那兩地的宗教學者與達官顯貴推舉伊本·沙特為漢志國王。1926年,世界穆斯林大會在麥加召開,伊本·沙特作為圣地監護者的地位得到廣泛認可。1927年5月,伊本·沙特與英國簽訂《吉達條約》。新條約廢除了英國的特權,宣布伊本·沙特領導的國家獲得“完全和絕對的獨立”。
缺錢的國王
多年的征戰,高昂的軍費,伊本·沙特明顯感到囊中羞澀,他的錢很快就要花光了。眼看勝利就要來了,大蕭條卻突然開始,往日前往麥加朝圣的涌動如潮的人流,慢慢變得稀稀落落,而這些人流正是剛剛獨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一直以來,伊本·沙特都通過給部落發放補助金的方式,把一個很不一致和不安寧的王國團結在一起,這是一種最主要的粘合劑,但是現在王國的財政陷入極端窘迫之中,他完全沒有能力繼續支付這筆維穩的費用了,更糟的是,他正在開發和建設的吉達城市供水系統,又該去哪里找到資金來源?
一次偶然的旅程似乎讓伊本·沙特看到了財富的機會。1930年秋天,伊本·沙特國王乘汽車與人同行時,一位同伴“無意之中”告訴他,也許有價值的資源都蘊藏在他王國的土地之下。這位同伴是英國人,名叫哈里·圣約翰·布里杰·菲爾比。
實際上他是英國軍隊的情報官員,而其公開身份是外交官。1917年他被派往阿拉伯中部地區專門收集伊本·沙特的情報。英國當時已經卷入一戰,正想方設法打擊他們在中東的敵人奧斯曼帝國。
菲爾比的任務就是判斷伊本·沙特是否有能力在中東領導一場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革命。這位劍橋大學圣三一學院的畢業生是一位語言的天才。他天資聰穎,對阿拉伯歷史具有濃厚的興趣,他對阿拉伯各個部落的歷史和統治者家族關系的正確理解成為了他敲開伊本·沙特心扉的鑰匙。
菲爾比在利雅得執行第一次使命時,就讓伊本·沙特迷戀上他的才識,那次三十四小時的私人會晤,定下了菲爾比以后一生的進程。
當然他也被伊本·沙特的魅力所折服,利雅得的外交生涯讓他和伊本·沙特成為了一生的朋友。他一直在向英國政府證明伊本·沙特才是真正能夠控制這個地區的領袖人物,但是英國政府并沒有采納他的建議,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哈希姆家族首領謝里夫·侯賽因身上。
當英國政府決定與侯賽因結盟的時候,菲爾比決定不再回到英國,他辭去了外交部的職位(也有人說他是被迫離開的)。他離開了英國,但始終沒有離開伊本·沙特。他一直保持著與伊本·沙特的通信聯系,不時地透露一些機密信息。正如沃爾德在《沙特公司——沙特阿拉伯與沙特阿美石油的上市之路》一書中對他的評價一樣,“從技術上,這屬于間諜行為”。

也許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菲爾比的兒子哈羅德·金·菲爾比成為了真實世界中的“007”——一個蘇聯在冷戰時期潛伏在英國軍情六處高層之中的雙重間諜,暗中替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克格勃效力,根據他的事跡改編的電影《忠誠與背叛》曾經風靡一時。
歷史證明英國政府的決定是錯誤的,當伊本·沙特成功地擊敗侯賽因并且宣布成為沙特阿拉伯國王的時候,菲爾比與這位領導人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成為了國王身邊舉足輕重的人物。
菲爾比非常了解伊本·沙特嚴重的財政問題和這些困難所加于王國的威脅。在1930年秋天共乘汽車的那一段旅程中,菲爾比注意到伊本·沙特非常沮喪。為了讓國王高興,他讓國王意識到自己和政府像是睡在埋藏著財寶上的人。菲爾比向伊本·沙特解釋說,開發這些礦藏需要勘探,需要外國的專業技術、知識和資本。
伊本·沙特順口回復菲爾比說,“如果有人提供我一百萬英鎊,我會把他所需要的開采權全給他”。他當時的心思確實不在這些毫無蹤影的地下礦藏上面,他一直在想著吉達的城市供水系統,并希望菲爾比能幫他找來一個打水井和做管道的人。
一年之后,科威特埃米爾·阿赫默德酋長的來訪似乎印證了菲爾比的想法,此時美國和英國在科威特爭奪石油開采權的斗爭正陷入膠著。1932年5月31日,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在巴林發現了石油的消息對埃米爾·阿赫默德酋長以及伊本·沙特國王都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他們都感覺到自己國家延綿橫亙的沙漠下面一定“躺著大量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