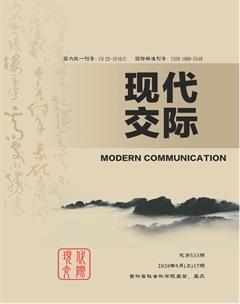試析五十年代作家行列對馬來現代文學的影響
王慧中 鄭雅然
摘要: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是興起于1950年的馬來文學團體,由著名文學家克里斯·瑪斯(Keris Mas)等十九位優秀青年作家建立。它所秉持的“為社會而藝術”的觀念,以及對馬來文學、語言的熱愛與推崇,使得該團體在二戰后的馬來文壇中脫穎而出,對推進馬來文學革新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其影響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馬來文學發展呈現出全新態勢,走上了以“為社會而藝術”為核心、以現代詩歌和小說體裁為創作主流道路,同時推進了馬來語革新的進程。
關鍵詞:五十年代作家行列 馬來現代文學 為社會而藝術 馬來語發展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17-0254-04
1950年8月6日,馬斯(Mas,真名為Arif Ahmad)、克里斯·馬斯(Keris Mas)、哈姆扎(Hamzah Hussin)等十九位青年作家于新加坡創立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即Angkatan Sasterawan 50,下文簡稱作家行列)。它是二戰后首個馬來西亞文學組織,以文學和語言喚醒民眾為宗旨,其成員的文學創作為馬來文學輸入了新鮮血液,也推進了馬來社會各方面的變化。作家行列從創立之初就一直不斷探索馬來文學新的發展方向,更多新成員的加入使得相關探究更加火熱及具象化。群英薈萃,各抒己見,團體內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意見分歧,從而衍生出了兩方辯駁的僵持局面。辯論就會有結果,必定會有一方勝利,而后走向繁榮。
一、新的文學發展方向出現
1.“為藝術而藝術”道路遇阻
以哈姆扎(Hamzah Hussin)為代表的“為藝術而藝術”一派,強調藝術的純粹性,也就是藝術即藝術,并非達成目的的手段。其不主張把文學藝術與政治和社會掛鉤,是理想狀態下的藝術發展狀態。這種脫離現實的文學藝術表達形式,放在當時依然被殖民壓迫、對獨立充滿向往的馬來社會,大概率是要被割棄的。不是因為這種文學形式不具有文學性與藝術性,而是因為那個時代的社會需要鼓舞人心的力量注入。大環境下不太能允許該種“文藝青年”逃離現實,只追求觀感的享受與滿足。雖哈姆扎一派竭力辯說,在期刊上發表文章反復強調不贊同將筆桿子當作政治斗爭的槍桿的觀點,但依舊不敵另一派的論辯,最終離開團隊,另尋去路[1]104。
早在19世紀30年代,法國文學界就誕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傾向,而其在19世紀末的繁榮則受到了英國藝術和文學領域發生的一場唯美主義運動影響。該流派能在當時的法國文壇掀起一陣不小的浪潮,歸功于浪漫主義思潮的持續繁盛和對充滿庸俗習氣的資本主義現實社會的反抗。這與20世紀50年代的馬來社會大相徑庭,前者是對現實的失望而企圖逃離以文學藝術作為心靈的慰藉,后者是現實需要眾人參與斗爭以實現國家獨立、社會公正、社會安寧及國家繁榮卻試圖不管不顧沉溺藝術美夢。純粹藝術的道路被攔腰折斷,是大環境所致,這也就意味著文學會朝著與其相斥的另一方向前行。
2.“為社會而藝術”道路堅定
相比起哈姆扎一派的命運多舛,阿斯拉夫(Mohd Asraf Abdul Wahab)為代表的“為社會而藝術”道路就堅實得多。作家行列建立初始,多數作家就是懷揣為下層民眾發聲、揭露丑惡現實的心情加入的,受到印度尼西亞文學組織“45年代派”(Angkatan 45)的啟發,這也為而后的文學藝術方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和哈姆扎辯論過程中,阿斯拉夫據理力爭,接連在當時著名的馬來刊物《時代先鋒》(Utusan Zaman)上發表多篇論文,擺事實講道理,把“為社會而藝術”的優點講得明明白白,把其受到另一方質疑的要點解釋得清清楚楚,同時還直接挑明了純粹藝術道路的缺陷[1]104-106。如此說服力極強且符合事實根據的論調,自然就增加了走“為社會而藝術”道路的可能性。
團隊中的一眾青年作家都是下層知識分子,他們愿用作品為被壓迫的勞苦大眾發聲,其實也可算作“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自然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文學的受眾者不止局限于懂行的文學家們,文學所面對的群體是所有群眾。作者與讀者能產生共鳴與共情,就極易受到追捧,而抓住眾多讀者的心,就能抓住文學主流。
“為社會而藝術”的文學道路是順勢而為的結果,更是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依靠不凡的眼界和不斷的努力所促成的。
二、文學形式多樣化發展
1.現代詩歌創作漸入佳境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時,詩歌市場仍被強調韻律和工整的古典詩歌所占領,自由詩體被知識分子嗤之以鼻,現代詩歌無從發展,只有極少數作家愿意冒著被譏笑的風險小試牛刀。馬來現代詩歌在二戰時還只是初現雛形,待五十年代作家行列建立起來,眾多青年作家投身到詩歌創作行列中,用現實的語言借詩歌的形式抒發真實的情感[1]119。曾被授予國家文學獎的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和共計發表過超1000首詩歌,同為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核心成員的瑪蘇里(Masuri S.N.)在詩歌方面也頗有建樹。
烏斯曼·阿旺于1955年所作的《罌粟花》(Bunga Popi),在當時社會引起巨大反響,他也因此名聲大振,躋身優秀作家行列。該詩沒有被韻腳、音節等規則束縛,以大眾熟知的罌粟花作為意象,用樸實又優美的語言描繪了經歷過戰爭后的國家、社會、人民都處于無盡的悲傷與難熬的苦難之中的景象:經濟蕭條、文化倒退、家破人亡、受到身心雙重創傷……這些血淋淋的事實都被烏斯曼·阿旺一一呈現:
血液膿漿遍布大地,
人類的靈魂被掠奪,
瘋狂地戰爭毀滅了和睦,
罌粟花美麗綻放期盼著敬拜。
僅剩的年歲,被痛苦補全,
體弱,佝僂,殘疾,失明,
映在記憶中的戰爭充滿恐懼,
現實中的戰爭卻讓人痛苦、孤獨。
人們痛失至親,
生無所依,
饑餓難耐,
成千的寡婦、失望與苦難,
上萬的孤兒乞討為生。
瘋狂的戰爭毀滅了和睦!
戰爭掠奪財富占領土地!
戰爭虐殺襁褓中的嬰兒!
戰爭摧毀了文明!
罌粟花就是倒地橫臥的戰士,
血色飛濺,充滿恐懼。
我們痛恨滿是殺戮的戰爭!
我們想念永久的和平![2]
瑪蘇里少年時期所在的新加坡曾被日本殘暴占領,而這一生活背景直接促成了瑪蘇里詩集《白云》(Awan Putih)的問世,但瑪蘇里年齡尚小導致其對占領一事持盲目樂觀的態度。從詩集《白云》中可看出,詩歌還未完全脫離傳統馬來詩歌班頓的詩體結構,但與班頓不同,其詩歌前兩句與后兩句已有了上下關聯:
功績
不會再出現的
只有真實的功績
成為塵土的
只有人類的忠誠[3]
在瑪蘇里受到作家行列的氛圍鼓舞,對戰爭有了新的領悟,詩歌也就發生了很大轉變[4]。詩體自由,內容緊靠“為社會而藝術”的發展道路,圍繞民族、社會和歷史主題而展開,呼吁民族獨立,呼吁國家自由,如長詩《我們是時代之子》(Kami Anak Zaman ini)[5]:
我們是時代之子
繼承了數代
在我們的血液里流淌著
舊時祖先的遺產
我們繼承了交替的傳統
血肉里印刻著原生文明
一脈相承,血肉相連
我們毫無拘泥,快樂生活著
我們繼承了過去的歷史
政府建立又沒落
留下的只有骸骨
腐朽壓迫下的殘灰
可以看出,傳統的詩體結構被打破,主題內容變化無窮,這樣的詩歌能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和認可,意味著現代詩歌已經成功走進大眾視野,不再是以前的“小眾文學”,打破了傳統詩歌一家獨大的局面。民眾思想觀念也在進步,新創作與新思潮的契合證明了曾經對現代詩歌冷嘲熱諷的時代已翻篇,同時更能說明作家行列憑借其巨大的影響力成就了馬來現代詩歌飛速發展,成了馬來文學領域重要歷史轉折點。
2.短篇小說、現實主義長篇小說持續升溫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同時也推動了小說創作不斷向前發展。除了文學團體內耳熟能詳的著名文學家克里斯·馬斯、沙馬德·賽義德(Abdul Samad Said)、吉米·阿斯馬拉(Jimi Asmara)之外,新晉青年作家維加亞·瑪拉(Wijaya Mala)等也貢獻了頗多的精良小說。
克里斯·馬斯在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期間,在報刊上發表了60篇短篇小說,而這些小說多以反對殖民統治和封建主義為主題,揭露了廣大農民漁民的困苦生活,后被收錄于4部小說集《鮮花盛放(1959)》(Mekar dan Segar)、《兩個時代(1963)》(Dua zaman)、《折斷生長(1963)》(Patah Tumbuh)、《反抗(1968)》(Pertentangan)當中。維加亞·瑪拉對于小說的創作熱情絲毫不輸別的著名作家,在此期間,他創作發表了上百篇短篇小說,其中還包含了不少獲獎佳作。主題寫實,有數量和質量的雙重保障,使得短篇小說的道路被擴寬,路基也被夯實[1]133-134。
而沙馬德·賽義德于1958年創作的長篇小說《莎麗娜》(Salina)也享譽全球,是具有國際水準的一部優秀長篇小說[7]2。該小說圍繞一位二戰后家破人亡痛失愛人的女子莎麗娜展開,從多角度呈現出了她的不幸人生,但她卻仍舊自食其力努力生存還心存善意。小說除了體現對戰爭的憎惡及對勞苦人民的同情之外,作者對主人翁的塑造包含了其對女性新的解讀,在當時看來,這種主題在文學界是鮮有的,甚至是違背世俗規則的,小說擺脫了傳統文學原有的條條框框,每個角色都鮮活無比,結局也并非是圓滿結局,可被算作現實主義的新嘗試,使得戰后馬來小說又朝前邁進了一大步。
三、文學和語言革新
馬來文學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經呈現出了繁榮的態勢。而該團體中的文學成員都是從小接受馬來語教育的下層知識分子,并非接受英文教育的貴族文學家,因此他們的作品都是馬來語作品。隨著他們的文學逐漸興起并被社會和世界所接受,自然也就拉動了源語言的發展,提高了馬來語的地位。以沙馬德·賽義德的小說《莎麗娜》為例,作品被翻譯成英語、法語、俄語、漢語等多語言版本向外輸出[7]3。這不僅是文學的輸出,更是馬來語的輸出。
作家行列同由一批老作家所成立的馬來語言協會(Lembaga Bahasa Melayu)達成共識:殖民地奴化教育不能達到爭取民族獨立的目的,改革和發展馬來語勢在必行。基于這一背景,作家行列確定其宗旨應該側重于改革馬來語和馬來語教育[1]114。作家協會在作家行列的協助下做了許多工作,例如推動了馬來語拉丁化,規范了馬來語語法規則,引進并改造了大量外來詞編入馬來語詞匯,編纂馬來語詞典等。這些努力都使得馬來語詞匯匱乏、語法不規范等問題得到改善,使馬來語在短期內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和提高。而后兩個組織又聯合舉辦了馬來語言文學大會(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商議決定推行馬來文字母拉丁化、發展馬來語教育等。馬來語能夠持續穩步發展,雙方的友好協作功不可沒。
語言是文學的基礎,文學是語言的集合,二者相輔相成,無法分割。作家行列就在語言和文學之間,充當起了協調員的角色,讓二者互相磨合、互相促進。可以說,沒有作家行列的進步青年所做的努力,馬來語言和文學革新的運動無法獲得社會各階層的參與和支持。因此在馬來西亞獨立后,馬來語能順利替代英語成為國語和教學的媒介語。
四、結語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可謂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馬來文學發展的大功臣,1950至1962年的文學發展成就幾乎都離不開該團體的貢獻。它影響了戰后馬來文學的方方面面,使得馬來現代文學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走上了出新且出彩的道路。全新的發展方向、不斷涌入的新人作家、體裁和內容的創新和語言的革新,以“為社會而藝術”為心照不宣的既定目標,直接引導了現實主義文學層出不窮蓬勃發展,還突破了傳統文學的各種限制。這種出新是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應當被看作有積極作用的“換血”機制,因為只有出新才能保障文學的活力,才能擁有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在這十二年間,馬來文學之路精彩紛呈,這些新動態、新成就也深刻影響了之后的馬來文學發展。
參考文獻:
[1]王青.馬來文學[M].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04.
[2]Usman Awang.Jiwa Hamba[M].Kuala Lumpur:Institut Terjemahan Negara Malaysia Berhad,2009:46-48.
[3]Masuri S.N.Awan Putih:Kumpulan Sajak-sajak[M].Singapore:Pustaka Nasional,1975:31.
[4]Tengku Intan Marlina,Muhammad Jailani.From Awan Putih to Suasana Senja:A Textdealism Approach Towards Masuri S.N.'s Poetry[D].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2010.
[5]Masuri S.N.Bunga Pahit[M].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20.
[6]A.沙馬德·賽義德.莎麗娜[M].郁郁,譯.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5:2-3.
責任編輯: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