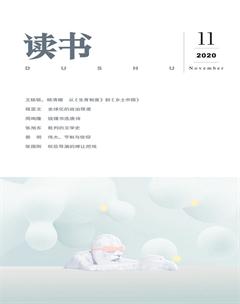全球化的政治限度
程亞文
在談論全球化時,人們往往會把它說成是一種經濟過程,即所謂“經濟全球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則如此定義:“經濟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市場、技術與通訊形式都越來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減少。”在這些描述中,全球化是中性的,僅僅是一種經濟過程,與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好像沒有多大關系。相當長時間內,全球化在西方政治家的演講和談話中,也一直是一個飽含積極、正面意義的詞語,被說成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代表著人類文明走向。
然而,對全球化的顯著不滿,近些年來出人意料地來自發達國家,這在提醒人們,以往對全球化的一些美好想象,可能是對全球化的性質缺乏足夠了解,而它主要又緣于對全球化從何起始及其本原體認不足。《讀書》二0二0年第二期汪毅霖先生的文章《“逆全球化”的歷史與邏輯》認為,“逆全球化”現象主要來源于自由貿易與國家利益兩種訴求之間存在內在緊張。這個解讀是說得通的,但意猶未盡之處在于,將全球化過多與“自由貿易”掛鉤,仍有把全球化等同于經濟全球化且從結果和過程來理解全球化造成的“內在緊張”之嫌。我們還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的視野,深入探析全球化的初始發心與動力機制,以及從資本與政治的國際國內互動和相關權力結構的變遷中,更好理解全球化所帶來的諸多乖張。英國歷史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是對此有精致思考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全球化“僅僅是社會權力資源擴張的結果”,而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則“意味著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的傳播,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展,意味著軍事打擊范圍的延伸,意味著民族一國家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開始具有兩個帝國,后來則只剩下一個”。也就是說,全球化是曼所說的意識形態、經濟、政治和軍事四種權力運動的結果,在后者的驅動下,資本主義、民族一國家和帝國這三種宏觀制度的建構與展開,是為了進一步拓展這四種權力。全球化在其展開時,是有主從關系的,由于四種權力的優勢方主要是在少數大國手中,它們也就成為主動方,在一九四五年之際是美國和蘇聯,而在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后唯有美國。全球化遠不只是在商業動機驅動下市場的全球整合,而是各種社會群體謀求擴張其集體權力和分配權力以實現其目標的結果。美國在“二戰”結束后主動幫助歐洲原殖民國家重建工業基礎、向冷戰前沿戰略要地的盟友單方面開放市場,以及后來接受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都是同一邏輯在不同時期的類似演繹,這也是過去一些年間“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這一話語的由來,以及全球化和“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實質所在。
此輪全球化的起始條件是“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啟程于冷戰期間、服務于霸權競爭目標的全球化,在其展開過程中,也在強勢政治力量的塑造下,構建了資本與國家的有機互動和回饋,即霸權國家為資本的跨境流動提供政治支持,而資本在帶動技術擴散、獲取利潤的同時,也為霸權國家鞏固優勢地位、化解國內問題創造更好的物質與技術條件。在此期間,人們見證了蘇聯的崩潰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也在新世紀來臨之際驚呼一個“新羅馬帝國”正在誕生。全球化其實是戰后國際規則制定者的一次超大規模對外投資,其預期回報是為霸權做出加持和優化國家治理。同時,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但在全球化剛剛展開之際,資本是有國家屬性的,受到了霸權國家政治意志的有力節制,使之與母國及其公民構成了“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資本與政治在戰后相當長時間內的互進關系,是建構起來的,相當程度上是對十九世紀中期英國主導的全球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終結的回應和反思,在那一輪全球化的后期,資本的無度擴張,不僅帶來了很多國家內部的貧富分化、階層差別和政治撕裂,還帶來了國際關系的緊張。作為撥亂反正,自“羅斯福新政”起至戰后一段時間,美國在其政治制度上建立起了對資本的制約機制,使資本運動有利于促進國內和諧。
然而,隨著冷戰結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動力弱化,資本與國家的關系在二十世紀晚期以來的演變中,出現了一些與以往大為不同的新的現實,它們開始突破曾經有過的政治對資本的規制。表現在:在技術隨資本力量的全球擴散中,一些非西方國家因其具有“后發優勢”,也逐步儲積起不可小視的技術能力和發展潛力;資本的全球擴張,改變了全球化起始之際的資本空間配置格局,新的超大規模市場也在以往的發達國家市場之外被創造生成,這個市場所支撐的新的資本積累與技術生長空間,并不完全受到來自外部的支配性力量的控制;與此同時,隨共同敵人的消失或不再明朗,在全球化初始期霸權國家利用全球化來壓制對手的動機和控制盟友的合法性均遭遇缺失,這使得美國不再有動力繼續“幫助”中國“融入人類文明主流”,也使得歐洲國家不再愿意忍受美國利用資本和技術擴張而對其進行政治控制。在這一輪全球化的前半段,強勢國家的政治意志主導了資本應用和技術擴展的進程,規制了全球化的路線和強度,但當全球化的范圍不斷加大、程度不斷加深時,進入這一輪全球化的后半程,資本應用和技術發展相對政治意志的獨立性空前增強,由某一個霸權國家來獨享絕對性的技術及其他方面優勢的局面不再可以維持。本是政治權力延伸手臂的全球化,反過來卻成為斷其臂膀的砍刀,這是全球化的動力提供者始料不及的。
“二戰”結束后,美國牽頭建立了多個國際組織,倡導多邊主義下的合作,表示出一定的共同分享世界權力和權利的姿態。這使國際體系進入了近代以來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即強勢國家意圖構建一個可共享的世界,而不再是少數擁有、多數被剝奪。在此之前,歐洲列強所構造的是一個絕對性的“有差別的世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說,維也納體系具有雙重特征,“在核心區域維護和平,而在殖民地等邊緣地區實行暴力”,就反映了這種事實。但這種意愿實際上還是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在這個分享體系中,美國和西方國家仍應占有優勢地位,即在表態“共同”的同時仍潛規則堅守“差別”;所主張的是一種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但美國擁有規則制定權。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一票否決權”,工業化國家“七國集團”的設置及其意圖主導國際經濟事務,都是這種現實的具體體現。它在理論上的表達,是以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為代表的霸權秩序觀,即認為國際秩序的建構和維持主要靠霸權,有實力的霸權國家提供了更多國際公共品,因此也應享有更多的國際權力和權利,即對世界事務的主導權。
按理說,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會鞏固全球化初始時刻在權力資源上占據優勢方的優勢地位,然而,實際的進程事與愿違。曾經作為全球化發起者的國家,因此轉而向自己竭力倡導的全球化皺起了眉頭,這也在向人們提出以下問題:人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夠接受一個“主權國家一律平等”的世界的出現?這樣的政治世界又是否真有可能?千百年來,平等一直是人類的夢想,但世界各國在近世以來,從未真正實現過主權平等,有等級的國際秩序、存在著支配與被支配關系是長久以來的事實。一個共同分享的全球化,是人類過去從未有過的經歷和經驗。美國對“共同而無差別”的世界的不能適應,也暴露了當今世界究竟在面臨什么樣的挑戰。
從對全球化的“不滿”和“新的不滿”中,需要認識到“全球化”在其起始時不過是霸權國家的一種投資品,它的出身中就已包含了政治上的選擇性,這決定了它的擴展有兩個基本政治限度,一是就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關系來說,存在著國際政治的平等限度;另一個是從廣義的政商關系來說,存在著資本與政治的互進限度。一九四五年之后相當長時間內,主導“二戰”結局的勝利者在制定戰后游戲規則和重建國內政治時,所建構起的政治現實,乃是霸權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和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在此前提下的國家間的主權平等,其實仍然有差別;與此同時,政治對資本建立起有效規制及兩者在共進中完善民族國家的制度建設,在此前提下為資本擴張提供保障。就前者來說,這意味著戰后以來的所謂平等的國家間關系,只是形式上或某些局部的平等,并以不言自明的不平等為前提,強勢國家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被視為是“二戰”的勝利果實之一,是不能允許別人拿走的;就后者來說,對資本建立起一定的約束機制,是對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前期國際國內政治失敗的應對,資本的自由要以能夠促進國家內部的共同福利為前提。這兩個限度今天都已被打破。國際政治的平等限度的被打破,相當程度上是在不平等的國際權力結構的保障下,全球化破解了資本與政治的互進限度的結果,也即資本在突破政治的規制、獲得前所未見的行動自由后,反過來瓦解了曾在國際體系中擁有主導權國家的權力優勢,此一過程可謂是反噬。這兩個限度的存在,也提醒人們要去回應和解答這兩個問題:全球化處于起點時的權力優勢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容忍其優勢地位的弱化和接受更加平等的國際關系?以及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國家政治可以多大程度上容忍資本的擴張?
在二0二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嚴重阻滯了全球物流和人員往來之后,對全球化的心灰意冷,已經成為一種另類“全球化”;全球化進程中的政治限度,也更加顯露無遺。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二0二0年五月份的一期封面上,赫然加黑印著“Goodbye globalization”(再見全球化)幾個大字,副題是“The dangerous lure of self-sufficiency”(危險的自給自足誘惑),底下是一幅螺旋狀裂開的地球圖片。新冠疫情進一步凸顯了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和階層差別,據有關統計分析,在密歇根州,只占當地居民14%的非裔美國人患病人數占總數40%;在居民46%是黑人的華盛頓,死于新冠病毒的人員中有76%是黑人,相比之下,盡管該市人口的37%是白人,但白人只占死亡人數的11%;在紐約昆斯區一條公交線路沿途的兩個社區中,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窮人區是富人區的八倍。新冠疫情還嚴重激發了建立自足性國家供給體系的沖動。英國歷史學家大衛·艾杰頓(David Edgerton)在六月十日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志發文《“自給自足”的新時代》,提出英國在“二戰”結束后曾將自給自足視為國家權力和安全的核心,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轉向強調全球化的經濟利益,然而,再到今天,危機和動蕩正在使英國脫離全球化而轉向民族資本主義。全球化在建構全球性的生產鏈條和貿易體系的同時,也瓦解了不少國家的生產自立和生活用品自助能力,對全球經濟體系高度依賴,所出現的“全球化內化”現象,普遍加大了各個國家在應對某些突發危機時的難度。當全球供給體系因抗疫帶來的“閉關鎖國”而突然發生斷裂時,一些國家的無力感明顯比往日未加入全球經濟體系時強烈得多,要想重新組織本國資源或利用全球資源來化解危機,短時間也難做到,欠發達國家尤其如此。
新冠疫情還在持續中,衛生專家普遍預測將會持續一年以上時間,在“全球經濟”突然遭受“隔離”的情況下,在抗疫行動中行動有力和經濟、社會恢復得越快的國家,在全球競爭中也會越有優勢。中國正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但這不是全球政治的幸運,而是“不幸”,會加劇全球化初始時的動力提供者對從全球化中獲得的收益少于成本的認知,轉而杯弓蛇影、疑心加重,更加激烈地尋求維護曾經擁有的權勢。在三月中國抗疫初步取得成功,相反美國深陷疫情困擾后,美國對中國的指責增多、“報復”措施尺度全失,已使人聯想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大國關系和國際政治狀況。
“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或“全球化終結”成為當前的流行語,關鍵性成因就在于,“全球化”這種投資品的收益或回報已顯著偏出預期。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其著述中,多次批評當代世界已陷入“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的窠臼,與之相對的乃是“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國家的經濟形態、思想和制度發生了由后者向前者的演變,資本與國家曾經形成的相互扶助關系在此過程中也逐漸消失,轉變為資本對國家的利用、誘迫和駕馭。這也使得如曼所說,全球化具有回龍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即人類行動擴張至全球,然后又返回到自身,而在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分析中,全球化乃“是一個同時包含整合和碎片化的不平衡發展過程”,在全球化的前半段,人們更多看到了全球化的整合作用,而到全球化的終結時刻,它對社會和政治的碎片化效應則大量顯現。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在失去規制時所產生的回龍鏢和碎片化效應,并非僅僅以貧富分化為特征,在以往產業資本占據主導地位、全球化程度還不太高的時代,國家內部雖然也有貧富之別,但富人與窮人還是在同一片空間形成利益關聯,進而產生政治上的連帶感;而在全球化條件下,不僅有貧富分化,更重要的是,看起來生活在同一片天空的人,在與外部世界產生了不同的利益聯系的同時,他們之間可能已經沒有利益粘連,這也使得民族國家的政治,失去了必要的利益前提和情感憑借,由此進一步演變為政治撕裂,也就難以避免。
當代形態的全球化已突破了其啟程之初的政治限度,由此在國際和很多國家帶來嚴重的政治失序,使全球化不再可能沿原有軌道繼續下去。新冠疫情則加快了全球化的“終結”速度。回應上文所說的兩個限度,未來全球化的開新,應從這兩處破題:從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國際關系角度來說,構造更加平等的全球化;從國家內部的階層關系來說,構建政治可以節制資本、福利共享的全球化。全球化如果還要繼續下去,就必須受到改造,而其要害又是重建政商關系,使資本在重新受到政治的規制的同時保持其活力。在構建公平而有責任感的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必然不可或缺,也應該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但在如何進一步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問題上,中國需要好好總結十九世紀中期以英國為主要動力提供者、二十世紀后半期以美國為主要動力提供者的兩次全球化歷程的經驗教訓,要深切理解全球化的限度,避免陷入因全球化失度而產生的陷阱,一方面,在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的過程中,要防止自身被全球化所反噬;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因沒有適當推進一些全球化議程而傷及其他國家、引起他人反感。
在當年英國開始工業革命并行將推動全球化之際,亞當·斯密、杰里米·邊沁、J.S.密爾等處于全球化中心地帶的思想者,在對自由貿易樂觀對待的同時,又對全球化的負面政治影響有所警惕,曾警告“少數人”會為其海外投資之便而推動國家政策有利于己,并損害“多數人”的利益;并認為資源輸出可能不是件好事。斯密、邊沁曾認為自由貿易比殖民占有更為有利,因為殖民地是“戰爭的主要來源”,它們吸走了母國的勞動力和資源,這些資源原本投在母國會更為有利。密爾對殖民的解釋也緊隨著斯密和邊沁:少數強大的投資者能夠使那些對于整體利益有害的政策在歐洲國家強制執行。“絕不應該被遺忘的是,在任何國家總有‘少數人,以及‘多數人;在那些政府不夠好的國家里,‘少數人的利益勝過‘多數人的利益,并以多數人為代價,促進自身的利益。正是按照‘少數人的利益,殖民地才應該被開發。”德國是當時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其工業化如火如荼之際,馬克斯·韋伯卻說出了這樣一番令人意外的話:“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民族之間相互斗爭的另一種形式……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沖突,并使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來反對本民族的未來!”他提醒當年的德國人要注意“一個重要問題:經濟權力與民族的政治領導權并不總是一致”。對全球化的這些幽暗論調,不是要我們在今天還去一味反對全球化,而是在對全球化懷有期待的同時,也要高度警惕其消極一面,以使全球化真正助益于國家之間消除隔閡,普羅大眾也共享利好。
《薩盧斯特》
[新西蘭]羅納德·塞姆著荊騰譯
定價:88.00元
二十世紀最優秀的古羅馬歷史學家,《羅馬革命》作者羅納德·塞姆另一代表作,更為集中地展現了塞姆本人的學術旨趣、治史方式和史學理念。憑借這部經典著作。對于研究羅馬歷史和羅馬編史學的研究者來說,這是一部無法繞開的作品。
生活·讀書·新知書三聯書店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