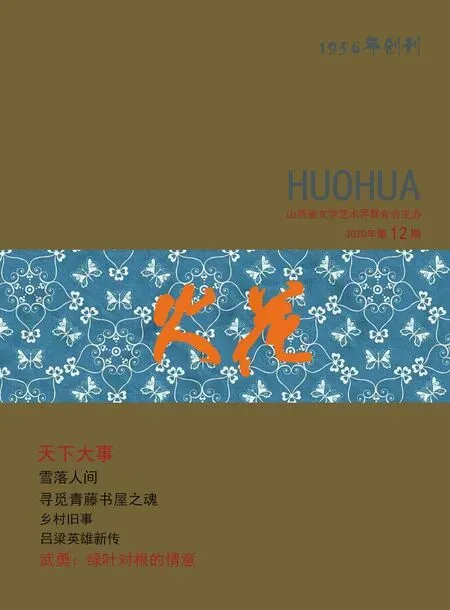尋覓青藤書屋之魂
邢增堯
一
實話實說,在我見識過的許多城市中,若論傳統文化的承續,文物古跡的留存,紹興就是走在前列的一個。不說別的,單言青藤書屋,就不同凡俗。
青藤書屋是一處具有明代文人園林味道的院落。之所以以書屋命名,主人自是讀書人。他出身官宦之家,卻一生窮愁潦倒;他才華蓋世,仕途卻一蹶不振。不過,歷史老人在他履歷表上填寫的,除了十六世紀杰出的文學家、書法家、戲曲家外,更有潑墨大寫意畫派開山鼻祖的身份。
他名徐渭,初字文清,后為文長,號有田水月、山陰布衣、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父親徐鏓,以貴州軍籍在云南中舉后,歷任縣官州官,直至四川夔州同知,卸任后還鄉。徐渭生母苗君本是陪嫁媵女,故生徐渭時只能居住在那座院落的舊式平屋里。讓人痛惜的是,徐渭出生剛滿百日,徐鏓便與世長逝,屋漏偏逢連夜雨,行船又遇頂頭風。從此,滿懷剪不斷理還亂思緒的徐渭遂躲在那靜如山谷的平屋中,用心血凝成的筆墨營造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
這是一所怎樣的院落,竟能成為一代宗師靈魂的棲息地?這又是怎樣的雜花、黃甲、墨葡萄、玉竹……竟能深蘊大師心田里郁積的痛苦、偏激、悲憤和孤寂?我揣著問號前去青藤書屋,走近徐渭,走近這位大師生活過的、能夠觸摸到體溫和心跳的空間。
細密似煙的春雨從天上從容飄灑,一所空曠的院落展示著古典的靜穆。高大的香樟、搖曳的翠竹,萌發的柳絲、綻開的草花,還有嵌著鵝卵石的小徑,精巧的亭閣,無不披上了提籠不起的輕紗。瀟瀟春霖將整個院落幻成了一幅雨意空濛的大寫意畫。
推開平屋大門,即是外室,正中懸掛著徐渭畫像,“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的對聯氤氳著濃郁的悲情。徐渭離世半個世紀,書屋招引著畫家陳洪綬專程前來,生活兩年之久,以體味徐渭那敏感的心,并將對他的崇敬化作幅幅生機盎然的墨寶。置于畫像上方的“青藤書屋”匾額即是其一。南首是一排方格長窗,臨窗安放著黑漆長桌、靠背椅和文房四寶。想當年,徐渭就在這里,在香煙裊裊中,邊望著窗外黃鸝、翠柳的倩影,邊將手中的筆墨揮灑得酣暢淋漓浩浩蕩蕩。
書屋的長窗外,是個小天井。我忽然瞥見,在青磚砌就的花壇上,有青藤瘋長。它青得鮮活,青得纏綿,青得深沉;在一串串珍珠綠般的細葉的護衛下,似一長溜令人心醉的音符從修竹、古樹間扶搖直上,靜謐的園林驀然有了動人的意境。我不由思忖:徐渭之所以對青藤情有獨鐘,將此屋取名為青藤書屋,將自己的別號命名為青藤道士,是特別喜愛那悅目的青色呢,還是欽慕那韌長的心力;是為了在孤寂中和它對話呢,還是用大自然的生命雕塑反觀自身,尋找失落的生機;抑或想到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語,將“青藤”作為自身在藝術的長河中乘風破浪的原動力!
此時此際,有兩位狀若父子的人走了進來,在徐渭的畫像前徐徐站定。長者口中念念有詞,念罷讓孩子握好畫筆,抱拳于胸,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禮畢,父親瘦削的臉上漾起了笑容,孩子胖嘟嘟的臉上漾起了笑容,我也不由自主地漾起了笑容。素聞,對徐渭推崇備至的鄭板橋曾刻過一枚專用的印章,名曰“青藤門下走狗”。難道這父子倆也有此心意?
書屋的內室原是徐渭住房,現作文物陳列室。整潔的櫥窗內陳列著徐渭的《白燕詩》書法手卷,多種版本的《徐文長文集》,戲曲名著《四聲猿》和戲曲研究《南詞敘錄》,供人瞻望,供人追憶。我發現,僅有的三二觀者,都流水般一淌而過。在名動古今的水墨寫意花鳥畫前,亦是如此,他們似乎并不明白,“入目三分景,七分在內涵”;似乎并不明白,這隨意涂抹的東西怎么就成了中國傳統藝術的瑰寶了呢?似乎并不明白,國畫大師黃賓虹怎么也把這些粗曠而簡略的東西推崇為“三百年來,沒有人能趕上他”呢?
二
縱觀我國的繪畫史,明、清是個群雄奮起、大家輩出的時代。徐渭就是這個時代超群絕倫的代表人物。
當然,這并非說,此前,我國畫壇卓有成效的名家就鳳毛麟角,事實上卻是大師濟濟,杰作滿眼。不同凡俗的創意也不鮮見。只是,要說到畫家筆墨創新的勇氣,特定的生命歷程和思想歷程的表露,心靈感應和人格氣場的契合,遙遙領先的就只有徐渭、朱耷和揚州八怪了。盡管回應在歷史晚云中的,不乏沉沉暮靄。
說到這里,人們也許會問:你說的不都是關于“人性”的東西嗎?那首當其沖的理該是人物畫家呀,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的,我國歷史上有不少當時出色的人物畫家,如東晉的顧愷之,唐朝的閻立本、吳道子,五代的曹仲玄、周文鉅、顧閎中等,他們的作品,或刻畫工細,或洗煉縱逸,或著色豐富,或形神兼備,都是秀出班行、可圈可點。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畫中人物與畫家本身的生性似乎疏遠得很。他們雖主張“助教化,成人倫,窮神變,測幽微”,事實上也在這樣努力。但其強調的卻是客體,少有融入自己靈魂和血液的東西。在這種態勢下,花鳥畫、山水畫卻反而別具匠心地傳輸出畫家自己一種生命的脈息,如宋代翰林圖畫院的花鳥畫,在提供給社會各階層人士賞心悅目的審美享受中就融入了畫家自己粉飾大化、文明天下的意旨,又如倪云林的山水畫,以“形”為表現手段,“神”為表達目的,清如泉水,潔如晨露,蘊含著對世俗煩惱的解脫和精神世界寬適的渴望。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些花鳥、山水畫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表露了畫家的心靈影調。但畢竟是曲折的隱晦的,能不能有一種更率直、更熱烈、更奔放的東西,像屈原的詩作“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鄭燮的詩作“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包拯的名聯“直干終為棟,真剛不作鉤”那樣,使畫家的心聲在畫作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釋放,使畫作成為其精神的載體。人們可以從畫作的線條、設色、筆意、神韻中洞明畫家本象,就像法國人洞明塞尚,西班牙人洞明畢加索,意大利人洞明米開朗基羅那樣……
我十分欣賞徐渭。他的水墨花卉、山水人物,在構圖和筆墨中,都屬奇峰突起,他樹立了一個讓人眼目為之一亮的典范。徐渭好像天生就是書畫的料,他的筆墨和同時代的“明四家”,和陳淳、張宏、藍瑛等相比,跟他之前的人相比,都是首屈一指的。徐渭信手揮灑,全無敗筆,他的諸多書畫作品,雖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榮寶齋、臺北故宮博物院等地,但就陳列在內室的復制品來看,亦是神韻獨具美不勝收。來此前夜,我因趕寫稿件,過了子夜方睡,今又早起,因而,步入院落時,不時有絲絲倦意襲來,但一見那幅葡萄圖,仿佛服下了清醒劑,每一根神經都被呼喚起來,舞動起來,連縷縷墨香也有了清涼的滋味。此圖純以水墨畫成,紛披錯落的藤條,倒掛枝頭的葡萄就像懸在觸手可及的頭頂一般。畫中自題詩發出的嘶啞嘆息:“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尤將藤條、葡萄與身世感慨融匯一體,一種飽經憂患、壯志難酬的椎心之痛與淬過火的不屈性格躍然于物象之上,成為不可磨滅的見證,成為青藤書屋之魂。北宋文學家蘇軾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評語,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用在徐渭的繪畫藝術上也是恰切的。就像人們在溫文爾雅的話語中,也能常常感覺到某種錚錚傲骨,某種執著強調,某種堅定信念一樣,《黃甲》《雜花》《玉竹》《驢背吟詩圖》等,亦使人在高雅和崢嶸、靜穆和靈動中,感悟到徐渭的百結衷腸,良苦用心。
在越地,徐渭的大名婦孺皆知。他擁有的才華難有人及,經受的苦難也難有人比。家庭的劇變、仕途的碰壁,性格的孤傲、政治的干系,血淋淋的現實使他九次自殺,有次,他干脆將鐵釘從耳道釘入,原以為必死無疑,誰知又命不該絕。七年牢獄之災還是靠了友人的保釋始獲新生。他嫌憎虛偽丑陋的官僚階層,嫌憎等級森嚴的封建家庭,甚至嫌憎時乖運蹇的自己。因而,當官員上門來訪,“忍饑月下獨徘徊”的他會用背脊頂住大門,狂呼:“徐渭不在!”用自己的獨特方式應對人世的蕪雜和炎涼。他一生凄清,一孓孤影,但失意不矢志,畢生在墨色和線條中放飛自己,收獲豐沛創意。明末大家公安派魁首袁宏道譽徐為“明代第一才人”。數百年來,江浙一帶特別是越地一直傳頌著他嫉惡如仇、不畏權勢、為民請命、智慧過人的故事,且不絕如縷。“山陰勿管,會稽勿收”就是個中一則。
那時,紹興分山陰、會稽兩縣。其間有一界河,名官河,上架一橋,名利濟橋。一年夏日,利濟橋上忽倒臥一無名尸體。百姓報到官府。兩知縣均說不屬本縣治所。幾天過去,尸臭薰天,人們敢怒不敢言。徐渭遂寫了一大張“出賣界河”的啟事貼于橋畔。消息一出,兩知縣齊齊趕至,著人拿徐渭問罪。徐渭見狀,當眾將手一招,議論紛紛的百姓剎時蜂擁而上。徐渭見自己和知縣被圍核心,遂稟告說:“該尸在橋上暴曬多日,無奈兩位大人均說此地非自己治所,既然‘山陰勿管,會稽勿收’,那么,此橋此河自與官府無關,今代為賣之,只為死者籌措喪葬之費,別無他意。”說罷面向眾人問道:“鄉親們,對嗎?”“對!”回應炸雷般響起。兩知縣見眾怒難犯,只得氣往屁眼出,喝令地保快快收斂了事。至今,若遇當事雙方互相推諉、搪塞敷衍,人們仍愛用“山陰勿管,會稽勿收”來揶揄。
在中國畫的天地中,沉浸于悲劇中的大家,除了徐渭,便數朱耷,他雖沒有徐渭那樣凄凄慘慘戚戚,但也好不到哪。1593年,七十二歲的徐渭與世長逝。三十三年后,便有了朱耷。朱耷,又稱八大山人,雪個,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的后代。面對朱家王朝的全軍覆沒,有苦難言的朱耷只能用形影相隨的畫筆勾勒出一個孤寂冷落的天地,以遠離政治上風刀霜劍的襲擊和威逼。那些孤零零的、躲在殘山剩水中的悲涼的鳥,凄清的魚,冷寂的竹,通體發散著勾魂攝魄的魅力;諸多畫作既是改朝換代國破家亡后個體生命痛楚的寫照,也是當時腥風血雨中文人學士朝不慮夕的凄慘生活象征。
水墨寫意花鳥畫,在一代宗師徐渭的營養下,朱耷、原濟登上了峰頂。那沉郁蒼茫、橫空出世的逸筆,那不求形似、豪放而又簡潔的醉墨,那情動于中又自然天成的神韻,似一股清流驅散了繪畫史上因循守舊,保守、精致卻又空洞的陋習。于是,這一注重主觀情緒,抒發性靈,充盈東方文化精神的畫種遂在中國繪畫史上大放異彩;于是,中國畫沿著文人、水墨的業余、寫意的軌跡前行,由徐渭到朱耷、原濟,再到遠離世俗的揚州八怪……至清末民初,中國畫,尤其是文人畫的發展,又高峰迭起,那就是以海派齊白石、吳昌碩為代表的大寫意花鳥畫,既別具只眼地繼承明清以來與時俱新的寫意畫傳統,又將金石中那種溫潤、厚重的特色融溶于中,從此,一個全新的涌動著強大生命力的傳承系列遂光耀于中國的繪畫史冊,成為世界畫壇一朵清香四溢的奇葩。
自古以來,我國文壇就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說,對水墨寫意花鳥畫的鑒賞也不例外。有一種說法是,水墨寫意花鳥畫的發展弊大于利,說它不講專業的基本功,不少既無高深學養又乏專業水平的文人,都像南郭先生一樣,擠將進去,究其根本,不過是濫竽充數而已;又說,就像西方的抽象畫派,在藝術史上,雖然是一大發展,但卻導致泛濫成災。對此,愚以為,未免太過武斷。試看中國傳統繪畫,以晉唐為絕頂的人物畫,以宋元為峰巔的山水畫,都屬嚴謹、規范的一脈,雖大匠迭出,佳作如林,但亦有不少畫作屬于忝列門墻之列。所以,我們不能因水墨寫意花鳥畫強調“無法而法”“我用我法”而認定其“不謂之畫”,認定其“絕大多數中小名頭的成就則基本上不入鑒賞”之列。英年早逝的民國畫壇巨匠陳師曾對文人寫意畫的主流作出公允評價說:“形式雖有所欠缺,而精神優美。”所謂“精神優美”,人品、學問、才情、思想也就囊括于中了。
三
我在青藤書屋里靜靜瞻望,在綠草如茵的院落里悠悠徘徊。那所見所聞所獲足可抵十年塵夢。然面對疏疏朗朗的參觀者,面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旅游者,心里又不免生發了些許遺憾。據悉,在不少發達國家,文化場所中,最為履舄交錯、車馬盈門的并非是綜合性的大商場、歌舞廳、影劇院,而是名人故居、紀念館、博物館。
在俄羅斯,名人故居、紀念館之多,舉世聞名。一幢幢滿是歲月滄桑的居所,門庭若市;一個個古色古香的房間,盡是參觀者,所有的沉思、懷想都顯現在人們的目光中,連年代久遠的木質樓板發出的“吱吱”輕響也成了一種引人尋思的蠹惑。
在法國,參觀實施分批入場制,門口排著長龍,館內人頭攢動。我沒有去過美國,友人說也是一派興旺景象,到晚上八九點鐘,參觀者還是不絕如縷。
文化名人故居、紀念館,猶似充滿智慧的伊甸園,個中陳列的罕籍墨寶,既是名人生平思想、工作和生活歷程的記錄,也是他所處時代風云跌宕變幻,學術消長傳揚,流派盛亡興衰的縮影。所以,這些國家都把名人故居、紀念館作為一個城市的文化圣地,都把參觀、瞻仰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列入學校的教學大綱。眾多中小學生常在老師帶領下,到名人故居、紀念館接受歷史和人文知識的再教育,讓先賢作為自己精神建構中的棟梁,讓名人故居、紀念館和大眾文化融匯一體,從而堅定文化自信,實現當代價值。實可借鑒。由此,我又想到,古之伯牙乃操琴高手,子期為識音行家,金風玉露一相逢,便有了精神上的通感,心靈上的共鳴,便有了“高山流水遇知音”之說。這就需要我們的藝術家,在置身于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潮流中,自覺升騰起對廣大讀者的“愛”,通過筆墨特征,將“愛”注入到表現的題材里,創造出洋溢時代審美感的杰作,來震撼讀者。而讀者亦能緊隨時代步伐,學會在美學中散步,那么,雙方就會在互動中達成默契,在交流中心心相印;那么,不僅藝術家的精神寄托會閃耀于人們的精神家園,名人故居、紀念館也會走出深閨、走出寂寞;那么,中國的傳統文化遂會“思接千載,視通萬里”,遂會“芳草年年綠,風物歲歲新”。屆時,縱然你只是個匆匆過客,但你帶走的,也會是個賞心悅目甜入骨髓的美夢。